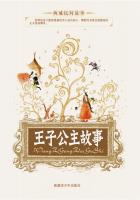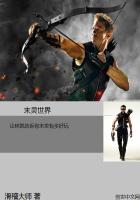他们在编撰《中原文化大典》过程中,有一段共事的经历。孙先生总负责,周先生是书法卷主编,两人并肩工作。周先生有时深夜来电请教孙先生某个问题。治学严谨的孙先生便帮忙查考,孙先生戏言成了周公的大秘书。两人虽居一城,距离不远,但之间也通信,有手札,常常是有情而抒,这种传统的交往方式他们还保存着,于现代网络通信社会着实奇特,似乎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周先生以书法名世,诸体皆备,以隶书最长,有“周家隶”之称。对周先生的书法,孙先生称之为文化的雄强大气。他以理论家的眼光评论周家隶“有自家面目,有周氏语言”。
周先生多年来坚持书法理论研究,出版了多本书论著作,孙先生认为,他是书界不多的几位创作与理论双翼齐飞的大家,对新一轮书法复兴具有引领作用。
周先生有很深厚的文学功底,读书很杂,各门类都有所涉猎,孙先生对朋友的文学生涯也颇为熟知,他指出周先生书法的养分所在:“周先生作为书法大家,对文学一往情深,青年时尝试过小说创作,中年以后诗歌散文达到很高境界,在文学艺术方面有‘通吃’的倾向,这正是其书法的底蕴所在。”
翻开新近出版的《周俊杰自书诗词选》,看到他的《六十初度》:“……雷鸣耳顺情难已,笔落云飞体益坚。正剧渐从辛巳启,千声万籁入毫端。”其豪迈雄强之心处处可感。周先生大量的阅读、思考及不断的诗词散文写作,使他的精神处于当代思想的高层次。
把文章写好,要大量地读。把字写好,要注重“临”。写好书法就要有基本功,现在不缺观点、主义,缺的是手下基本功。这是周先生的感言。
古人云,学书“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已届古稀之年的周先生仍是气宇轩昂,他坦言自己还在追险绝,充满激情,追求险绝奇峰仍是他现阶段的书法创作目标。
正是因为在各自领域的非凡造诣,才使两位大家相吸相引,互相尊重。孙先生这样对照两人:“在做学问做事方面,周公雷厉风行,讲究事功。我耽于思想,性格比较萧散,大半生在文坛度过,有许多东西能给当代添上一笔很好,不能留下也很好,保持心灵的宁静感。”
书法创作是孙先生六十岁后重要的目标,他认为书法在中国文化、文学理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极抽象、简单,但艺术的要素极丰沛。孙先生从文艺理论切入书法创作,从书法创作、理论来探究东方美学要义,从传统来看,书法也是中国文人必备的素质。孙先生在书法创作中进入绝佳的精神体验,他这样表述:“书法可以使人心花怒放,忘乎所以,气韵流畅,并进入禅意。”
因为对书法及其理论的钟情,要在身边寻找可以为师又可以为友的目标。在老朋友中,周俊杰是最合适的人。孙先生曾送他一联:“书法为师文为友,茶道同品酒为仙。”孙先生称:“这种交流使我更快地进入书法堂奥,得益甚多。”
作为书法家的周先生是如何看待孙先生的书法呢?周先生曾说过,在当代中国作家圈里,孙先生的书法使其他人都黯然失色。孙先生的行书、楷书直入晋人。基础与学养打得越坚实、越厚实,书法才能写得浑然天成而又充满元气。
与孙先生交往后,周先生的文风也有变化,他真诚地借鉴孙先生的文章风格,并自省写批评文章如果过于冷静就不好读了,若兼具文学性,气韵就会不同。周先生曾慨然赠诗孙先生:“使我成名皆为酒,舍君无处可论书。”
周先生与孙先生两位大家亦师亦友,互为影响,实为后学之典范。两人一旦坐在一起,便会谈论最近读的文章著作,对一些美学观点、文化思潮展开讨论,彼此心领神会,灵犀相通。孙先生曾说,当代文人普遍存在的浮躁学风,我们没办法整体上改变,但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小范围内改变。孔子曰“独学无友则孤陋寡闻”,我们在两人之间造成小小的良性学术气候。
省黄河迎宾馆内,立着一幅当代石刻巨制《黄河迎宾赋》,可作为两人的友谊见证。石刻的文赋作者为孙先生,书丹则为周先生之隶书,他们的才思如两股别样的清流,交汇浸透在彼此的艺术生命里。
孙、周二位先生爱饮酒在圈内是有名的,因为资深,故也是品酒专家,对国酒茅台鉴别最准。圈内传闻,如果席间上的是茅台,两位先生先是小口品之,酒水在口中轻轻一过,马上放下杯子:“不典型!”再不思饮。
在一次晚餐上,孙先生告诉在座朋友,他即将到南方参加一个重要的文学活动。而周先生也告言大家,近日要赴台湾进行书法交流,二位老友将有一段时间的分别。两人遂频举杯中物,嘱托云云,互道珍重。
分别虽然只有数日,出行皆乘二十一世纪现代交通工具,舒适快捷,决非古人游历之漫长险恶,可他们身上还是拂来一袭厚朴的古风,如李白之于杜甫,之于汪伦,透出几分西出阳关的薄暮苍凉。
从文学里走出的书家
他应该有三个身份:作家、鉴赏家、书法家。
一般人眼里,一个退休老干部,人际关系总要疏淡些,不比在任时的热闹。但他是一个例外,办公室的茶水从来流水似的不间断。
他就是赵世信先生。书法家周俊杰先生称他为“侠之大者,情之浓者”。说到底,这些都与他的个人修为有关,凡事能够推己及人,替他人着想。与他交往,大家觉得温馨,觉得快意,加上他对文学和书画发自心底的热爱,所达到的至深境界,使其在艺术界有极好的声誉和地位。
读他的小品文《梦画小记》,其对书画的痴迷可见一斑,“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披衣而坐,赏玩画作,顿觉游移青山绿水之间,祥云缭绕……余性喜书画,亦爱收藏,非求拥有,但望过眼,如是近四十载,既成生活之不可或缺……”
四十年的收藏史,可想有多么资深了。他解释说,从前的书画工薪族花点钱还是能收藏的,而现在书画市场价格虚高,搞收藏就难多了。
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琴而后晓声。因为收藏,经他过眼的古帖、名帖很多,时时翻阅、观赏,其眼界自然异于常人。虽然不去刻意临帖,但他写出来的书法却有大家之风,翻阅他的书法集,散发出浓郁的书卷气息,或古拙,或奇崛,或悠然,在视觉与内涵上给人独特的艺术享受。
书法家王澄是他相知多年的老朋友,王澄称他的字“常透出几许雅逸情调,几许书卷气息”,是真正的“知者”、智者。他自己也常说,喜欢“有味儿”的字,这个“味儿”想必是朋友所说的雅逸情调与书卷气息吧。
这种情调和气息从何而来?周俊杰一语道破:“他压根儿就是一介文人,从文学里走出来的书家。”
一言以蔽之,这一切来源于他对文学的痴情,对美的热爱与追求,对情的专注与投入,对世间万物的深深体悟。
苏轼、林散之是他喜爱的书家,那自由、随意又透出法度的风格流露在他笔墨之间。近来,赵先生又喜欢上何绍基的字,他书法中的飘然清逸、稚拙灵妙在此得到印证。作品“碧树数丛堪作障,青山一半不知名”,写得端严神凝,却又掩饰不住骨子里的风雅。他与书法中的雄强派不同,他们是“大江东去”,狂野不羁,他却是风轻云淡,信步从容。他们走平坦坦、直通通的大马路,他偏爱曲径通幽、芳香四溢的花间小径。
他不像有些人因书法而为书法,他还有作家的身份。书如其人,笔墨腾挪间有文学的底蕴滋养着、烘托着,才可以随处意趣,翩然生姿,演绎绝妙的意境。
“清凉世界”是赵先生书写的一条横幅,挂在他的书房,望之空阔玄静,淡雅隽永,寄托了作者和主人的行事格调与淡泊心境。
熟悉他的人都说,赵先生身上有一种古代“士”的精神。他虽钟情收藏,但常常收而不藏,不为收藏所困,有好几幅大师级作品被他拱手送人。问他为什么舍得,赵先生幽然回应,当然不是随便送,一是不“要”不送,二是不是“家儿”不送,只送懂它的朋友。
赵先生之于文学,与字画一样,同样也是痴狂,早在1979年还在部队期间就创作出长篇小说《合欢》,这部反映海峡两岸悲欢离合的力作,一经面世便受到读者青睐,并被绘成连环画刊载。
从部队转业后,他选择到条件艰苦的河南省仪封园艺场。在他的治理下,园艺场变成了一个花果诱人的桃花源。被这种纯朴美好的劳动氛围所感染,他创作了一系列意境优美、诗情画意的抒情散文,《葡萄园风情》《果棚下》《仪封观花》……如晨晖映照下的一串串露珠,光彩夺目,传递出那个时代特有的美质和光芒。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心灵的故乡,有自己写作的源泉,正像沈从文情系湘西的那条河流,赵先生笔下微漾着柳公河的涟漪。
他的散文集《沧桑》塑造了一系列小人物,真实记载了生活在豫东柳公河畔的人们,他们的质朴、狡黠、小诡计在他的笔下一一呈现,活色生香。他熟悉这种世俗生活,并没有简单以道德的层面冠以好恶,而是诉之以深刻人性。因为怜悯所以懂得,这些生活在乡村环境的小人物牵扯了他的心,其生动的乡村俚语让人意会解颐,其人物悲欢令人叹惋。
正像他不为书法而书法一样,他也从来不为诗而诗,诗作抒性灵而无匠气,突如其来的灵感,往往出现神来之笔。两年前的云南之行,异域风情触发了他的诗兴,一组古体诗使他重新焕发艺术青春。他写《看走婚舞》,随口拈来,又暗合了当地的走婚风俗,“暮烟四合绣楼西,阿夏相期眉眼低。绕去缠来无限意,一声鸡叫泪沾衣。”更有趣的是《摩梭女敬酒》,“一曲酒歌世外音,轻交玉臂更销魂。摩梭淑女早知好,五十年前要走婚。”后两句的“突发奇想”写得更为巧妙,不由让人会心拊掌。
在这个阅读渐被人们遗忘的物质年代,他依然把阅读作为一种习惯,时时关注着文坛。去年,他买来刚刚入选茅盾文学奖的整套书,常常看到深夜。有作者出书,登门拜访,希望能写序言鼓励,他都尽量予以满足。今年初夏刚刚出版的《寄情》一书,就收录了他为书画家和文学作者撰写的序言,文章点评独到,遣词精妙,阅之给人以启益和快感。
虽然早已退休,生活还是多姿多彩。书画,文学,如同两个红颜知己相伴,使他不至于寂寞。两个都为他所钟爱,使他割舍不得,书画带给他精神上的沉醉,文学泛起他对人生和世界的旖旎情思。
至今,他仍旧保持上班的作息规律,只不过更多时间坐在茶案前,泡上一壶香茗,燃起一支烟,淡看庭前花开花落,四季更迭。身边依然新朋旧友往来不断,饮茗、品字、赏画,一拨儿拨儿几乎踏破门槛。
如今文艺界不乏埋头苦干的人,却更需要有热心有威望的长者,引领寂寂于荒野,正在四处徘徊彷徨的年轻人。不止一次听到有人感叹,像他这样好的前辈不多见了!
许多年轻人愿意和他交朋友,愿意坐他身边,喝着他亲手泡制的上等好茶,无论是文学、书画,还是家事、国事、天下事,年轻人娓娓道来,赵先生听得饶有兴味。对于年轻人的虚妄、偏执,始终若暖暖煦阳一般,不动声色地轻拂着、打量着、宽容着。又像历经沧桑的河流,洞知一切,又悲悯所有。
年轻人从他身上传承文化和做人的美德,感知他的睿智和大度,他也被年轻人的活力和新锐所裹挟。他总是敏锐地发现和捕捉,为后来者敞开胸襟,乐意看到年轻人的成功。遇到有艺术发展潜质的年轻人,他总是助其一臂,办画展,出书,忙来忙去,乐此不疲,仿佛是自己分内的事情,所以他备受年轻人的尊重。
早在十年前,身为省人大书画院院长的他重磅出版《大河风·河南省优秀青年书画家提名展作品集》,一下子推出四十位年轻且有潜力的书画作者。至今,大河风书画集已出版十五集,许多作者早已是活跃在书画界的佼佼者,在全国乃至海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同样在六年前,担任省直作家协会主席的他多方筹措资金,出版了五卷本,约一百五十万字的《南丁文集》,实为河南文坛罕见的气魄和壮举。南丁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即在省文联工作,且长期担任领导职务,从他的文字中可以窥见半个多世纪以来,河南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因而此文集有其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
在他今后的日程中,还有一长串与他有关或无关的,有待施行的计划,他所策划组织的十二集纪录片《中国书法三千年》正在拍摄中,该片追寻三千年书法发展的轨迹,以高科技手段展示与传承中国书法艺术,使观众领略书法艺术在历史长河中的演变发展及其独特魅力。
因为需要,因为无数有意义的事在等着他,所以他不会老。在岁月面前,好像用了什么障眼法,他把人间的沧桑和风尘隐藏起来,沉淀下去,大家看到的,还是他阔远的目光,洒脱轻盈的笑谈。
窗外,繁密的花蕾等着结果。案头,浓浓的笔墨,默默的笔管,静静候着他,将每一个簇新的日子泼洒浸染。
禅画
在模糊的儿时记忆里,家里有一开本不大的彩色画册。父亲讲,画册的作者杨振熙是他的一个同学,在省城一家出版社工作。
豫北小村庄隔着黄河南岸的省城,那个闭塞的年代,出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省城因遥远而神秘,但省城里那个画家的名字却记住了。
几十年后,父亲不幸病故。我也因“自己的梦想”将人生疆域从豫北移至省城。偶然参加一个在嵩山举行的大型画家笔会,在会议开列的长长名单中发现了他,父亲高中时代的同学,我儿时读过的画册作者杨振熙先生。
那天的仪式是在沥沥秋雨中进行的,雨中的山峦如黛似烟。打听确切后,我做了一个决定,趋身上前与他攀谈。
面前是位六十多岁的老人,看上去从容恬然,如果父亲活着年龄应该和他差不多。
我先是作了自我介绍,道出父亲的名字,他讶异地望着我,口中喃喃自语:“在这里没见到尚某某,没想到,却见到了他的女儿……”
及至中午在酒店用餐,席间我过去敬酒,和他谈起小时候读画册的故事,他又发欷歔:“今天没和尚某某喝上酒,却见到了他的女儿。”
那次活动之后,我替父亲续上了这段缘,几次登门叙旧。我的出现对于他是个意外,这意外又使往事复活,他在我身上看到了昔日同窗的身影,如果父亲和他对饮,两人一定会把酒尽欢。
在他六楼的工作室,挂着一幅幅意境淡远的山水画,有夏日绿荫、田边小放牛,有深山古寺、流水孤舟。凝视片刻,便有丝丝清凉沁人心脾。轻轻啜着香茶,听他回忆青年时代,畅谈人生艺术。论起年龄,他略长于我父亲,我便叫他杨伯伯。从杨伯伯的追忆中,我体会出父亲作为一个农民子弟的无奈和苦涩。
父亲和他是高中同学,同在辉县百泉苏门中学就读。他曾随我父亲在我家里住过半个月光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