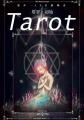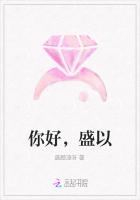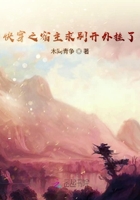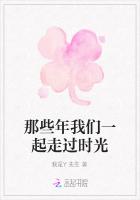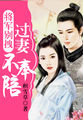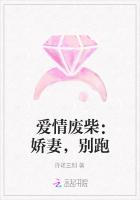经历了两任丈夫,严歌苓指出了中国男人与西方男人不同的爱情观:西方男人总是给对方留下很大的空间,所以不经常争吵,不像中国夫妻那种胶着的亲密程度,非要你活到我生活中,我活到你生活中,一方非要管住另一方,谁给你来的电话我都要知道。而西方夫妻,在感情与经济方面更为独立。
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有何不同,她如此界定:“在美国,我算是中产阶级吧,大家的生活都差不多,差距不大,不存在攀比。比如各家的车子悬殊不大,都不是豪华的那种。在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人的压力是大的。现在我回到国内,看到国内人们的压力挺大,大家都在追逐利益,变得很庸俗,失去了高贵,这非常可怕。”
论起年龄,严歌苓说,最喜欢四十岁以后的这些阶段,在心理上比较放松,比较知足。失眠症治好以后,也特别乐观,身体有了一个改善。生理影响心理,所以特别平静,觉得现在就很好,生活没有欠我的,生活给我的已经够多,再也不需要什么。
在自己周围扎起自守的篱笆,拒绝外界诱引。这份沉着的内质便是淡定、娴雅。女人的这种气度何尝不是浮世中鲜见的精神操守。看似无所求,实则内心已趋丰盈、圆满。
手边有安妮宝贝的书,随手翻开,有这样的句子:“做一个好看的女子,相信海誓山盟。”心里一惊:海誓山盟说的何止是男女旷世之恋,于作家,则是与笔下文字深入血脉的恋守,持久恒远才会成就其笔下的苍凉与繁华。
一声蛙鸣
对莫言作品的认识,还是从他的《红高粱》开始。之后,几乎他的每部小说都引起文坛的震动与热议。长篇小说《蛙》的出版给文坛带来了一股旋风,也引起媒体的追逐、采访,我也有一次对他进行电话采访的经历。
最初联系莫言时,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于是,把电话打到他家里。家里人说出差了,最初在石家庄,过两天又说在青岛,查网上信息,这几天莫言一直在为《蛙》作签售,但手机依然没人接。于是探路文学圈朋友,有人说作家李佩甫与莫言关系好,便打电话给李佩甫老师,得知莫言一些情况。接下来发短信给莫言,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听到莫言的声音。因为降大雪机场延误飞行时间,他暂留青岛,元旦也回不了家,约好回京后接受采访。
几天后的一天早上,突然在报社接到莫言的电话,说是一小时后要开会,现在有空。于是就有了关于《蛙》的交谈。莫言精力旺盛,口才甚好,极善讲,语言严密又有逻辑,遇到这样的作家,采访起来特顺意。
为了这次专访,我特意到中原图书城买来《蛙》,日夜阅读做了功课。《蛙》中的内容都是近几十年我国发生的事情,读来感同身受。
那些事情我大都经历过。我生孩子时适逢计划生育紧张时期,当我从部队休完产假回来,发现我们县城的电影院,即县城繁华地段,上下扯满标语,像是正展开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什么“想跳井没人拦,想上吊给你绳,想喝药给你瓶”,等等,标语一条条写得触目惊心,目的只有一个——不准超生。
堕胎、代孕,都触及人性的深层,让人感受到现实与愿望、个人与社会的悖论与残酷,应该说,这是一场不可避免、难以化解的尖锐冲突。《蛙》涉及的是敏感题材,关系到我国的基本国策。读后我很自然地想到,只有莫言这样的大家才有勇气这样的雷区,一般人不敢写,写了也出版不了。
当我提出自己的疑问时,莫言首先否认自己的这份“特权”,他说自己并不是大家,人人都可以写,这样的题材别人的作品里也有,只不过没有作为主要的来写,没有当作敏感题材来挑战。
莫言先是叙述了我国上世纪80年代国家推行的强硬的计生政策,他用理智、辨析的态度来讲计划生育,他说,对于家庭,人们违背了自己的愿望,中止怀孕的妇女更痛苦。对于国家,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政策落实到每一个家庭,从官方和民间的角度,对计划生育都有切身的体会。
莫言不由联系到自己:“三十多年来,计划生育一直是基本国策,影响了几代人。拿我来说,我,我的女儿,女儿的下一代,都受到它的影响。独生子女并没有减少家庭负担,在家庭里没有玩伴,成长中伴随着孤独感。另外,独生子女的肩头承受的精神压力也很大,家长望女成凤,望子成龙,形成社会性的攀比,孩子的消费也是水涨船高。再一个是人口老化,一对夫妇要面对四个老人的抚养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问题会慢慢出现。”
计划生育是了解中国的一个便利窗口,多年前一时走红的小品《超生游击队》反映了农村的一些超生现象。莫言说,网上出现了代孕公司,现实中出现包二奶生孩子等,非常混乱。这个问题摆在眼前,无论是作家还是老百姓都不能回避,写作这样一个题材当然具有挑战性,会带来强烈的后果。回顾三十年来的计划生育,中国大地发生了许多惊心动魄的事,文化与历史的因素纠合在一起,《蛙》的写作揭示了中国巨大的秘密,是一个时代的总结。《蛙》如果能够引发人口学家的思索则更好。
在《蛙》这部小说中,主人公蝌蚪是一个军人,被迫而违心地严格执行计生政策,对于从军的莫言来讲,这一人物显然有他的影子。莫言并不讳言:“的确,蝌蚪身上有我的影子,这样的人并不是一个,我可以归类其中。蝌蚪的精神历程也是我的精神历程。当年我们都冠冕堂皇地以各种借口来掩盖自己的欲念,这就是那个时期知识分子的灵魂写照。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许多人没法抗争,办过违心的事。这样的一个背景很重要,小说是写别人,也是写自己。”
“归类其中”的莫言,在小说中有拿自己说事的真实性。在读《蛙》时,一直觉得作者隐隐贴在那层薄薄的窗户纸后面,感觉到他呼吸的热度与哈气已经在融化这层纸了,基本上书中的蝌蚪就要和现实中的莫言重合为一了。在许戈辉对莫言的采访中,莫言谈得更加直接:“如果没有这个独生子女政策的话,那我起码也是两个孩子,甚至三个孩子的父亲吧。”
从古到今,根深蒂固的子嗣观念流淌在中国人的血液里,不仅在农村,城里也是这样。从农村入伍的莫言,虽然在部队成长为专业作家,但终也逃脱不了这种思想的牵绊,随着年龄的增长,感到身边只有一个女儿是不够的。人生有些孤单的他,越来越追悔当年为了追求政治进步而做掉的那个孩子。对于喜欢大家庭、子孙满堂的中国人来说,确是人之常情。
写《蛙》也是写娃,蛙鸣等于啼哭的婴儿,他用这一隐喻,书写自己的罪恶感和被缠绕的欲望。他在《蛙》中写道:
每个孩子都是唯一的
都是不可代替的
沾到手上的血
是不是永远也洗不干净
被罪感纠缠的灵魂
是不是也永远得不到解脱
吹口哨的老头
那天上午,按约好的时间去省文联家属院拜访南丁先生。
进门寒暄后,南丁需要到书房去题字,我在客厅喝他泡的绿茶。一会儿,耳边莫名飘来一阵口哨,侧耳细听,那口哨轻巧,悠扬,忽高忽低,若有若无。
印象里对口哨的审美还停留在很久以前。许是社会生态发生了变化,人们几乎失去了吹口哨的心情,这心情应该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艺复兴”时有过,电影电视一演到谈恋爱的年轻人,配乐就会出现浪漫的口哨,画面也很文艺:绿荫匝地的寻常街巷,年轻的小伙子飞骑着单车,嘴里吹着口哨,去约会自己的心上人。现在到哪儿去找这样的情景,满大街的汽车,满大街的焦虑面孔。
南丁从书房出来了。“刚才是你在吹口哨?”我好奇地问。
他笑了,反问:“我吹了吗?”当一个人专注地吹口哨时,他本身就是一个制造音乐的乐器。
“我是无意识吹的。”南丁又补充,“我常常是这样无意识地吹。”
“哦?无意识更美妙。”
无意识也更让人羡慕。
这个八十岁老头,心一点儿也不老。省诗歌学会每次采风,南丁先生几乎都要出席,在每次举办的诗人联欢会上,第一个节目都为他准备,他的经典节目几乎都是同一首信阳山歌,或者叫酸曲。大意是“鸡蛋没有鸭蛋光,男孩子没有女孩子香;去年清明亲一口,今年重阳还在香。妹儿哟,好比蜂蜜蘸洋糖”。淳朴的山歌,盖过了所有华丽的诗句,哼到最后,他总露出颇为享受的笑意。
去年的元旦前夕,诗人们在东区欢聚迎新,坐在首席的南丁应邀为大家助兴,仔细一听,竟是王菲唱红的《传奇》: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
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
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
想你时你在天边……
缠绵,深挚,以及苍老执著的磁性,就像捧着一束玫瑰,满目繁华晃得你目眩情迷,逼得你无处可躲。他的歌声如此,内心却是怎样的绮丽漫漶。从酸曲到流行乐,这位文学老人的年轮并没有因为岁月而增添沧桑的刻度。
最早近距离走近南丁先生,是几年前七月的一次南阳诗会。晚上,几位诗人都在挥毫,为淅川县荆紫关镇现场作诗献艺,一些青年诗人则趁此机遇索取诸家墨宝。已经晚十一时多了,南丁门前仍是车马喧喧,毫无安静的迹象,他不时拿出纸巾拭汗,想必胳膊也写得酸沉了,腰背也挺累了,但他只是坐在椅上稍微靠一靠,权作休息,脸上始终笑颜盈盈。只要有后生过来求字,他暖阳一样,将他的厚爱送上去。
我也有幸得到一幅“静水流深”。当我离开大厅时,已近午夜,回首望见头发花白、毫无倦意的南丁还坐在那里,如同守望着什么。
这个季节的雨水很丰沛,夜里由白天的中雨转成了小雨,隔窗聆听,那雨的滴落却是多情的,是对大地无声的浸润。
翌日,在去丹江水库的途中我和南丁先生有过短暂交谈,那是由一篇南丁写的评论说起,在那篇评论中,南丁提到“要我写”与“我要写”这个论题,既有对青年作家的肯定,又有善意的忠告,给人以创作的教诲和启悟。
在丹江水库的游览船上,一时风急雨骤,雨珠横飞,坐在船舷边的南丁却是不动声色,悠然观望。
南阳诗会后,我在朋友那里借到一套《南丁文集》。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沉浸其中,小说、评论、随笔、散文、诗歌,皇皇五本巨著几乎囊括了文学体裁的所有门类。南丁这名文坛宿将,他的文学活动就是河南文坛几十年的珍贵缩影。在评论卷,他对河南文学界享有盛名的老作家及其作品几乎都有评论和“画像”。他怀着真挚的情感谈与他们之间的交往,谈他们的作品,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他写苏金伞、青勃、李蕤、华山,写乔典运、张一弓等,给人留下形象感性的认识。
南丁有一个独特的文学观点,他把文学称作精神能源学。他说,文学应当开发人们精神中本来存在的能源,开发人们精神中本来存在的煤电油气。一个提供精神能源的人,本身就应该是一个精神能源丰富的矿藏,达观,仁厚,相信未来,有足够的力量抵御平庸生活乃至恶劣的生存环境。
南丁曾说,我和文学有点拉郎配的意思。那个年代,讲究的是服从组织分配,干一行爱一行。这样,南丁和文学的关系,就是先结婚后恋爱的关系。他不但无怨无悔与文学结婚,而且高产,优生优育。
南丁负责省文联多年,称自己干的是服务行业,实践证明,他关注发现夺目绽放的鲜花,也关心寂然无名的野花小草。
一位青年作家说,南丁先生虽然年事已高,但站在他身边,你会感觉到他依然是有力量的。他有篇文章《且把花甲当花季》,其内在的艺术生命力与年轻的心态,使人们难以把他当作通常意义上的老人。他身上既有中国传统文人的渊源,又有让人耳目一新的浪漫诗意,洋溢着让人赞叹的生命活力。这大概是老派文人独具的魅力吧。
书文为友,茶酒同品
从外表看,孙先生与周先生如同两个闲云野鹤,实则内功修得很紧,学问在花甲之后继续奋斗,事业上还当成中年来看待。孙先生六十岁后沉浸墨海,书风自成一家。周先生七十岁生日时,有人赠他诗:“新人乍入七零后,气宇轩昂又逢春。”
所述二位先生,即文艺理论家、散文家孙荪,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周俊杰。
孙先生儒雅文质,典型的学者型作家,作家型学者。因为长期做文学理论研究工作,养成一副敏锐多思的面孔。比起周先生,孙先生似乎要慢一拍,说话慢声细语,又注重讲话的抑扬顿挫,轻轻一句评语,四两拨千斤,足以使对象现出全貌。
周先生长孙先生一岁,爱好颇广,感性外露,体格雄健,年轻时被称为“黑豹”。他嗓音朗朗,席间喜讲通俗故事、典故,浅显通白,余味深长,往往逗得一桌人喷饭。性格热烈奔放的他,身上还有些许浪漫色彩。他有一本书法著作,封底整版是他的个照,背景衬以滔滔白浪,其笑看世界的神态竟酷似一位伟人。
他们是不同类型的人,一个若清茶,一个如浓酒。其专攻也不同,一个文学一个书法,却甚为契合。
二位交往甚笃,谈文论艺、饮酒赋诗,孙先生邀请周先生参加文学界的活动,周先生则邀请孙先生参加书法界的聚会,一周内少则三次,多则五六次。两人的友谊,拉近和沟通了文学与书法。他们的交往,不仅是生活中的交往,更是精神与学识的互相探寻、印证和提升,对更加深远艺术境界的共同追问。
孙先生以评论成名,散文也颇有建树。较早的具有代表性的评论专著是《让艺术的精灵腾飞》,文章缜密严谨,观点新颖独特,充满文学色彩。而近年写作的《风中之树》是一部研究当代作家李人格与艺术的扛鼎之作,此书的写作孕育了十多载。曾问及为什么要专门解读作家李,孙先生说:“李是中国当代文坛大将,文学豫军当代领军人物,他身上体现了中原文化的丰富和深厚,所以对他的解读具有标本意义。”
孙先生的散文写作从丰富的人生历练出发,从生活细微处着笔,抉发生活的诗意,娓娓道来,亲切自然,闪烁着灵光与哲理。散文集《鸟情》《瞬间解读》《生存的诗意》等文采飞扬,既充满妙趣又别有韵味。名篇《云赋》曾入选高中教材,妙趣斐然,多年来为人称颂。
散文与评论,孙先生驾着这两匹马车,驰骋在文坛上,为文坛带来快意诱人的风景。
当他从省文学院院长的位置退下来之时,曾经主持过《河南新文学大系》的孙先生又担纲《中原文化大典》执行总主编暨《文学艺术典》主编的重任。
对浩瀚无比的中原文明进行梳理、展示,没有深厚的学术素养、超强的宏观驾驭能力,根本不可能理清头绪。在孙先生等人的主持下,一系列规范出台。在各分典相继拿出初稿之后,孙先生又逐卷审阅,组织评审,拿出切实的评审意见。应该说,他深厚的学养,强大绵密的思辨力,殚精竭虑的心力,对大典的成书起着巨大作用。周先生如此评价孙先生:“《中原文化大典》有‘中原《四库全书》’之称,孙先生可以说是当代编撰中原文化的纪晓岚。”孙先生很是自谦,他说我们很难和古人比。但主持编撰这样一部皇皇中原文化巨著,就好像进去了九曲十八弯的黄河,曲折繁复,再出来看当代艺术现象,就可以高屋建瓴,驾轻就熟。编撰的这个过程,可以获得更宏观的眼光来看中原文化、中原艺术,使得对中原文化和中原艺术既有信心,又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