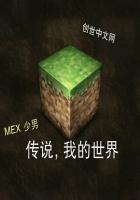“唔——哦,唔——哇。”猫头鹰不祥的叫声,一下接一下从远处传过来,给树林增添了阴森恐怖的气氛。
“啪。”一滴血落在金生的鼻尖上。
还没有来得及擦拭,他又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搭在了肩膀上,很轻很轻,轻得几乎让人觉察不到。
金生毛骨悚然。一股凉意从脚底升起来,瞬间窜至头发梢,整个人一下子变得僵硬了,周围静得出奇,只有头顶上的血,还在继续往下滴。
一点。
两点。
三点。
有一根触须样的东西,从金生的脖子后头,缓缓划了过来,停在了他的颈窝处;又一根触须顶在了另一边。
金生全身的神经都集中到了这个地方。他觉得,这两处像尖刀顶住一般,慢慢刺入肉中。热热的血流了出来,顺着左右胸部,直流到了脚踝处!
“啊————————”
金生的精神完全崩溃了。他狂叫着,夺路狂奔而去。
村子东头,响起了锣声。锣声密集、响亮,中间夹杂着嘶哑的“救命”喊声。不一会儿,锣声中断了。不用说,锣肯定被敲破了。
没过两秒钟,村子的西头又响起了急促的锣声。不过,这锣才敲了三四下,就戛然而止,一切又复归平静。
尔后,村中响起了开门声,吆喝声,杂乱的脚步声,小孩的哭声。
天终于亮了。太阳升起来,那颜色就像一大团血,洇洇湿湿地染红了半个天空。村子正中的大树下,聚了一大群人,他们有的站着,有的坐在地上,一个个疲惫不堪,精神萎靡。在他们面前,摆着三具尸体,全都血肉模糊,有一具只剩半连脑袋了,连面貌都难以辩认,样子惨不忍睹。
晨风吹过,引来几只苍蝇,围着尸体嗡嗡地转。飞了一会,它们都落到了血迹上,贪婪地享受着美味。
谁也不愿开口说话。
除了阳光照到人身上,投射在地上的影子在缓缓移动外,时间就好像凝固了。村子的某处,传来了呼天抢地的哭喊,把个村子衬得蔫蔫的。
何一鸣咳了两下,沙哑着嗓子说道:“老少爷们,事情已经发生,伤心也没用了。眼下当务之急,还是让死者入土为安。大家都回去吃早饭,吃了到这里集合,再商量怎么安葬这三个人。还有,我看何村是呆不下去了,大家要有心理准备。有亲戚朋友的,就到亲友家住上一段时间,看以后的情况再说。有可能的,最好把家给搬了。”
“说得轻巧。我们祖祖辈辈都住在这里,房子田地也在这里,说搬就搬?”一个中年人大声嚷嚷起来。
“我不搬。”“我也不搬。”好几个人响应着。“往哪儿搬?就是死,也要死在这里。”
“你们不搬我搬!”说话的是二楞子,他梗着脖子,大声说道,“你们还嫌死得不够多吗?我还年轻,不想就这样死在这里!”
“啪!”有人抽了何二楞子一嘴巴。大家定睛一看,是二楞的爹。“你个畜牲,你忘了你是怎么长大的啦?你就这么怕死!搬搬搬,往哪里搬?是福不用求,是祸躲不过。老天要让你死,到哪里都一样会死!”
“是啊,与其死在外头,不如死在家里。”
“娘的,我就不信抓不住这个鬼!大不了,我们跟它拼了!”
“对,这话有理。眼看谷子都要入仓了,把谷子一收,我们有的是时间。只要大家齐心协力,一定能躲过这场灾难的。”二楞爹的话,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
何一鸣没有再说话。乡土难离,乡情难改,就算面对死亡,大伙的心思还是放在辛苦半年得来的收成,和劳作几代好不容易修起来的房屋上。趁着大伙不注意,他转身向村外的张庄走去。
万重岭高耸入云,自半山腰以上,就云雾缭绕,除非特别晴好的日子,人们很难欣赏到它的真正面目。顾名思义,山有万重,丘壑众多。山顶大风刮个不停,鲜有高大的树木生长。这里的气候与山下迥异,有时山下艳阳高照,山顶却风雨交加,甚至冰雹连连;山下冰封雪飘时,山顶却是风和日丽。一些地方长年四季见不到阳光,积雪经年不化,寒冷彻骨。
就在那云卷云舒、鹤起鹤落的半山腰上,有一座说不出名字的山峰。山呈东西走向,形似笔架,中间高高突起,两侧分别罗列着两个小峰。在主峰前,有一大块空地,空地上匪夷所思地修着一座道观。
道观并不大,山门由一块块石头垒就,没有用过任何泥沙灰浆,却整齐稳当。圆形的拱门上,端端正正写着四个大字:“空空道观。”观内,有一横两纵三幢房子,形成一个小小的三合天井。三幢房子全由木头建成,数十根一人粗的大柱子,顶起了一座大殿,大殿正中央供着道教的始祖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又名老聃。他长须飘飘,道髻高挽,道袍宽大,道骨仙风。最令人瞩目的是他手中的桃木剑,他左手拿着剑鞘,右手挽个剑花,双眼看着剑尖,嘴唇微张,似在吆喝,欲降魔捉鬼。
神像前的供桌上,摆着一个古铜色的香炉,青烟袅袅直上。大殿正中,有一位五十来岁的道人正在盘腿打坐。从殿后面转过来一个年青道士,向着中年道士恭敬地递上一张纸条,说道:“三叔飞鸽来信,请师傅下山一趟。”
道长展开纸条看了看,思索半晌说:“也好,叫上阿土,明日清晨下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