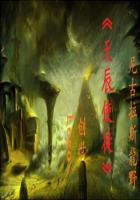秦文轩做梦也想不到月儿竟然会上了九龙山的麻风寨。
九龙山是秦文轩儿时的童话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无论醒着还是睡着,都是童话。神仙鬼怪、仙女高人、土匪强盗、野人老虎、野猪长虫,什么什么都有。九龙山上有个很大的林场,秦文轩的舅舅就是林场里的场长。秦文轩他们一伙常到林场去玩。在上山的一路上,他常常跟同学们对对子,对唐诗三百首。林场的森林里有好多鸟儿。九龙山绵延不过数十里的山脚下,怪石嶙岣,茫茫林海里,杉树尤多。林场的五六个工区就隐没在那逶迤的树海里。高山顶上有一片处女草原,是高山牧场。亚热带地区什么都生长,一年四季都是绿色的世界,有郁郁葱葱的翠竹,再上面是松树,再上面是灌木,再上面则就是牧草了。他和小伙伴们在山里挖过药材。山里有很多药材,最值钱的是“紫草”,很不容易挖到,挖了晒干,拿到集市上,一根紫草能买几块钱,碰上一棵紫草,他们就会欢呼起来。
然而,九龙山上也不单单有绝美的风景,也有一个很不吉利、很可怕的地方——麻风寨。那个寨子就座落在比九龙山的高山牧场地势还要高的山头上,那个寨子里的人全都是麻风病人,所以那寨子是完全封闭的,绝对不让外界的人进去。据说那寨子里还关着***一个伪省长,和一个***的将军。麻风病是一种严重传染性疾病,为防止扩散,那里的麻疯病人是绝对不许出来的,寨子里通常吃的东西都是专门有人从外面运送上去的。有个麻疯病治疗中心就专门把守在上山的唯一路口,控制着寨子里所有的麻疯病患者避免他们同外界人接触。
秦文轩全然想像不出那个寨子里的麻疯病人是怎样生活的。只听村里人传说,那麻风寨里的人看上去都十分可怕,有的没了鼻子,有的没了眼睛,多半病人的脸上全都是坑坑洼洼,看上去模样十分可怕。寨子里的麻风病人死了之后,一切用品都得一把火焚烧干净。尸体得装进一只密封的罐子里,撒上生石灰,深深地埋入地下。
秦文轩他们村子里的大人们吓唬起自己的伢子来,最厉害的一句话就是;“不听话就把你送到麻风寨去!”所以,在秦文轩的感觉里,那里无异于人间之外的一处可怕的地方。
那么在月儿出走之前,还发生了些什么呢?
秦文轩一再催问之下,母亲才期期艾艾地告诉他有关阿月的事:后来有一次,月儿差点亲手将那充满忌妒、常对她施行暴力的林场工人活活地扼死。再后来,月儿的境况就更加凄惨了,月儿被男人家用一条铁链子锁在家里。但月儿到底还是跑了,据看见的人说,月儿是拖着半截沉重的铁链子跑了的。那是在一个月夜里,至于月儿去了哪里,就有各种的说法,最多的说法是,月儿上了九龙山,去了那个令人闻之色变的麻风寨……
一连许多天,秦文轩都心情极度沉郁,他眼前仿佛总有月儿的影子,他看见月儿拖了一条铁链子,踉跄行走在蜿蜒崎岖的九龙山的小路上,树枝掳扯着她的衣裳,只有清冷的月光伴着她的孤独的身影……
他的心在呻吟:月儿啊月儿,你为什么要到那个可怕的麻风寨去呢?难道那麻风寨里的日子就好过吗?你是在逃避着什么?你居然是在逃避这属于正常的人的世界吗?
绝望犹如镪水腐蚀着他的心。到哪里去寻找月儿?月儿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月儿在高高的与世隔绝的九龙山上,山上无人,秦文轩又一次想起了野人的传说。月光如水照缁衣,一片惆怅……
秦文轩从月光下的田野边挽起一根狗尾巴草。思绪便闪回到童年的时光了。在九龙山上,他和月儿一起上山打柴,一路变着法子做游戏。山路的世界除了那耸人听闻的野人之外,还有无穷的玩法。光是那满山遍野的毛竹林,就给小伙伴以无穷乐趣,将两棵毛竹扯弄得弯下腰来,将两棵毛竹的竹梢儿挽结在一起,便是一张舒适的吊床了,月儿就抢先坐在那张“吊床”上,荡来荡去地打秋千。她快乐地荡着的样子,就像是草叶上一只小小的瓢虫。秋千荡累了,秦文轩就采来一支狗尾巴草,将那狗尾巴草折断递给月儿,告诉她:“用手紧紧地捂着,一口接一口地朝手心哈热气,嘴里要一直念叨‘狗仔儿出来,狗崽儿出来!’不一会儿就会有一只小狗崽儿出来的。”月儿说:“不会是真的,你一定是骗人的。”秦文轩说;“骗你是小狗,你照我说的去做,不停地这样叫,手里就会走出一只小小的狗崽儿来,还会汪汪汪地叫唤呢。”月儿还真的相信了他的鬼话,不听地往手心里哈气,一声接一声唤“狗仔儿出来!狗仔儿出来!”她一回头,秦文轩已经抢坐到那竹子的秋千上去了,还得意地笑着,月儿才知道上了他的当,故作气恼地跑过来捶打他:“水伢子你真是坏死了……”
寂寞沙洲冷,却有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魂影……这是苏东坡的词。这意境传导给秦文轩以寒冷和虚无,他好似读懂了,又好似陷于更大的迷惘,更空冥的虚无。
通往九龙山的公路早几年就修好了,现在开着车就可以一直开到林场的场部门口。那天,秦文轩坐着车去了一趟林场,在场部见到了舅舅。气色红润的舅舅看样子已经准备要退休了。吃着茶,秦文轩跟舅舅询问起了那个麻风寨的情况。
舅舅说:“早就没了,原来是个治疗麻风病的点,早几年就撤销了。”
“那寨子里的人呢?”
“谁知道,一个人影儿也见不着了。”
“难道都……”
“麻风病可不是一般的病……”
“现在,可以随便进那寨子里去了吗?”
“可以是可以,但谁去呀,谁有那兴致去那不吉利的地方啊。再说,车路才通到场部这里,往上还有十几里地呢。”
秦文轩还是执意地去了一趟麻风寨,他在崎岖的山路上几乎跋涉了整整一个下午,那一路上连一个人影儿也没见着,去到麻风寨的时候,已经是夕阳西下的光景了。但见满目一片荒草,像大海海底的景象。歪歪斜斜的木楼多半都倒塌成一片废墟了,露出荒草的断壁残垣还留着被焚烧过的痕迹,四下里看不见一个人影,只有喳喳唧唧的鸟鸣,并不悦耳,却聒噪出一派让人提心吊胆的死寂,秦文轩浑身不禁有一阵糁人的寒意窜过……
深山里,又落下了
一片刚懂得翻译阳光的嫩叶
小妹不知道那叶子正是她自己
她只是扯一兜兜猪草
扔进虎口般的的背篓里
只是摘吃又苦又涩的野果子
不知道又苦又酸的正是她自己
她只是倚在青石上
读天上的云朵
像是读一页页课本
她的课本早已被阿爸糊了窗子
而那飘往山外的白云,
总要停下来看她几眼
看弯了又弯的山路几眼。
离开故乡的那天,秦文轩还亲眼目睹了一场宰牛仪式。宰牛的仪式是很肃穆的,得把牛的眼睛闭住,用一块黑布蒙起来。因为牛是土地的神灵,牛就像是农家的亲人。
那天,全村的人都集中在平坝子上,由年长的老人念念叨叨地念经,而所有的人都紧闭眼睛,不忍目睹这场面,那抑扬顿挫的经声,颂扬老牛的恩德和辛苦和不幸,哀悼牛,与其说是对一样生命的尊重,不如说是人对自己、对自己命运的哀悼,人人脸上的表情都是真诚的,没一个人笑,没一个人大声说话,杀牛没有用刀子,所以看不见血,而是用绳子将那老牛渐渐地勒紧、勒紧、再勒紧,听不到牛的呼号,你只能感觉到牛的挣扎和地的颤抖,最后老牛轰然倒地的瞬间,像电影里的一个慢镜头,那个时候,山路有一阵萋萋的风吹刮过,风声像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