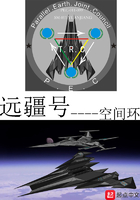27、深深地呼吸
莫斯科餐厅的氛围一向是温馨的。
邻桌独坐着一个漂亮的女孩,双手支颐,显然在等待她的朋友的到来,果然,不一会儿,一个手捧鲜红玫瑰的帅哥便匆匆而来,女孩先接受了鲜花,随即接受了男朋友的一吻……
不约而同,他和蓝菁都朝那一对恋人投去羡慕的一瞥……
蓝菁轻声说:“瞧这幸福的一对儿。”
秦文轩感叹:“天底下所有的幸福都是相似的,而不幸却各有各的不幸。”
“把老托尔斯泰的名言略加改变?”蓝菁瞥了他一眼。
“依然放之四海而皆准。”他报以哲人似的一个微笑,“不是吗?瞧瞧,同样是爱情,可你跟今天那古怪的老头子就另当别论了……”
“得得得,你就别哪壶不开提哪壶了。”蓝菁赶紧摆手,如同躲避瘟疫似的。
他说:“不过,我想这下应该没事了,一旦那让人匪夷所思的老头子死了心,你的劫难也就终于可以告一段落了。”
“但愿得吧。”蓝菁轻轻叹一口气,“不过,你知道什么叫不可理喻吗?”
“你是说那个怪老头?”
“那只魔戒一般的戒指。它就好像一道咒语,自从搅和上它,我的生活整个儿都改变了……”
他说:“这听起来像是一则童话、一个寓言故事。”
“好了,别煞风景了,咱们还是换个话题吧,”蓝菁挥了挥手,像要从眼前拂去一片梦魇,“我更想听你讲你们大山里的野人故事。”
他问:“我还有一情不明,今天你为什么偏偏选择我去为你做这个挡箭牌呢?”
蓝菁定定地望着着他,她的目光很是专注:“因为我别无选择。”
“好像是一篇小说的题目。”
“除了你,我身边好像没别的朋友了。”
“怎么会?你蓝菁难道是个孤家寡人吗?那你还怎么当这个作家呢?”
蓝菁一字一顿,准确定位:“我的意思是我身边一时还真找不出比你更适合扮演这个角色的朋友了。”
秦文轩仿佛才发现蓝菁的微笑其实是很美的。
秦文轩说蓝菁:“你当初不是在医院里当医生的吗,怎么后又搞起文学来了呢?再说你也不丑啊,人家说,只有丑女人才退而求其次地搞什么文学,你是怎么回事,犯傻了?”
蓝青说:“大概是觉得生活挺没劲儿的吧,就随手写写划划。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一家报纸登出了一条征文启事。一冒热气,写了一篇文章就寄去了,没过几天还真就发表出来了。这是十年前的事。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涂鸦,满以为自己可以吃文学这碗饭。”
“就这么一发不可收拾了?”
“但有一点你不清楚,”蓝菁惨然一笑:“当时我想,我真够幸运的,能在成千上万的文章中脱颖而出多不容易啊。然而事实却另是一回事。”
“怎么呢?”
“说来好笑。后来那报社的一个编辑跟我熟了,才给我揭开了当年的谜底,说当时他们报社其实总共才收到三篇征文稿!”
“噢,原来这样!”
蓝菁苦笑说:“你瞧啊,这就是支撑了我十年的梦想!说来真够可笑的,是吧?我要是早知道这事,准会泄气死的,人生总是这么捉弄人!”
蓝青对秦文轩说:“上次你在笔会上见到我的时候,其实正是我最落寞的时候。”
“我怎么没觉得?”
“那是你迟钝。”
“可为什么事那么落寞?”
蓝菁欲言还止,顿然有了几分黯然。
秦文轩知道蓝青是三年前离婚的,她有一个女儿,跟着前夫。所以,蓝青现在应该是独身女士。
蓝菁搅动着咖啡:“还是说说你们山里的事吧。你曾经给我说起过那个叫月儿的女孩子,还说到了月儿的老阿婆。你说那个老阿婆居然还见过野人?究竟怎么回事啊?”
秦文轩于是向蓝菁娓娓道来。
大约在十多年前,有一次,月儿的阿婆突然从村里失踪了三天,人们在山里找到她的时候。阿婆已全然不省人事。醒来后则问什么也不回答,只是呆兮兮地哭。人们从她身上发现有许多长长的毛发,那绝不是人的头发。村里的人就猜测说,月儿的阿婆一定是被山里的野人掳去做了一回野人婆。
于是月儿家就更多了一层晦气。
在村子里,老阿婆本来就是个神秘人物,据说她常躲在家里,在草纸上写一种谁也看不懂的古怪文字,据后专家考证说,那便是女书,一种只在女人之间秘密流传的神秘文字,据说是写女人们的受苦心情和她们之间神秘的心灵约定的。现在这种古怪的文字现在基本上失传了。
更要命的是老阿婆还放过蛊,20年前,月儿的老阿婆给她的男人放了蛊药,结果,男人没有及时地赶回来。终究是死在了外面。据说村里的女人们当年都这样干的。因此没有谁指责老阿婆放蛊有什么不妥。问题是别家的男人都回来了。唯独老阿婆的男人一去不回头。老阿婆的蛊药毁了她的幸福。说起来,也怪她男人没能按事先说好的时间赶回来,并非他在外面好上了别的女人,而是由于天灾人祸交通断绝的缘故没能及时赶回来……
老阿婆从此在村里便抬不起头来,老阿婆就守着独生女儿,也就是月儿的母亲,过着孤零零的日子,一天到晚说不了几句话,瘦得只剩了骨头和一层皴裂的老皮。月儿的阿婆身上的巫气很重,谁都不敢搭理她,阿婆也不主动跟谁搭讪,迎面见了人,低头擦身而过,仿佛一个哑巴。
照村里的老例,如果一个女人放了蛊,过了20年还不解蛊,那她就必须再放一次蛊,否则她自己就会死于蛊毒。老阿婆若再不放蛊,她就得死。所以,村里人纷纷传言:“当心哟,老阿婆要放蛊啦!”每当山外来的货郎挑着担子进了村,一帮小孩就会不怀好意地对那货郎说:“去月儿的家里吧,月儿的老阿婆家里干净得很,老阿婆家里还有香香的腊肉,管够吃!”初次进山的傻头傻脑的货郎,听了这话,还真说不定直奔老阿婆家投宿去了呢。村里各家的女人都紧张地提醒自家男人,万万要提防老阿婆放蛊。一旦中了蛊可就不是闹着玩的,谁碰上算谁倒霉。解药是没有的。
那时制造蛊药的配方已揭开了秘密,据说是一个研究这方面的学问的先生从村里一个濒临死亡的老寡妇嘴里套出来的:用一百种有毒的虫子,放在一起,叫它们互相厮咬,晾干,配以女人的经血,秘密地放置在她们的胸前,给她们的心爱的丈夫悄悄地做了手脚,以往村里的男人们出远门时,只要一听到老婆说:你可要早点儿回来啊——男人们听到这般的话,浑身就会禁不住瑟然一抖,知道老婆给他放了蛊了,这可是要命的事情,丁点马虎不得。男人在外面办完了事儿,无心在外做拈花惹草的勾当,恰算着照着和老婆事先约定好的日期,颠巴颠巴赶回家来,大老远便高声喊叫:“堂客,我回来了!”
村里的女人们就是用这种办法制服住自家的男人的。一般的外人哪里晓得这其中的讲究。特别是那些走村串寨的货郎们,不知道老阿婆的底细,就更容易一脚踏进陷阱……
倒霉的事情总是一件连着一件,后来,月儿的母亲又疯了。
所以说,月儿家三代女人,没有一个有好命的。
“月儿真是够可怜的。”蓝菁感叹,过了一会儿又问:“那个月儿呢?她后来又是怎么样了?”
秦文轩摇摇头:“请原谅,我不想继续这个话题了。”
蓝菁也才忽然意识到,过于沉重的话题与此时此刻的优雅氛围竟是那么的不协调……
缄默一阵之后,蓝菁忽然感叹:“我忽然想出几句诗。”
秦文轩打趣地说:“不会是朝着什么的‘一路狂奔’吧?”
蓝菁浅浅一笑,随口吟出几句诗:
潜入海底
深深地呼吸
带血的气泡
将孤独
涂上每一个鳞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