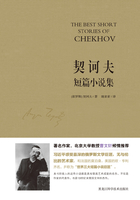我一按下接听键,电话里立即传来很关切的声音:“木森,你还好吧?”
听到如此的声音,我的鼻子竟然不争气泛起了酸,我忙说:“霄姐,我还好。”
“钱够吗?我刚才在你的那张卡里面打了两万块钱,不够用的时候你说一声,一人在外自己要小心点儿,也别太亏待了自己啊!”
“知道了霄姐,呵呵呵,你怎么像我妈似的那么罗嗦呀!”我掩饰着内心的酸楚,装着很无谓的样子跟霄姐说。
不知道为什么,人越是在危难的关口,越是听不得如此柔情关爱,它就像一缕丝线,深深探入心底,把内心深藏着的娇弱,一点一点牵扯出来,不管你是娇柔的女子,还是铁打的汉子,在这柔情似水的言语中,由不得泪盈满眶。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觉得我很老?我在你眼里就那么老吗?我说的话你就那么烦啊?是不是喜欢听月儿那样的小姑娘在你怀里撒娇,你才不嫌罗嗦啊?”
又来了,又来了!这怎么与月儿又扯上关系了呢?什么时候月儿又在我的怀里撒过娇被你发现了?
噢,对了,上次在我的工作室里是有过那么一回。唉,丢了老大的面子!可那是在月儿误喝了药酒才——我干嘛跟你解释这么多?你是我什么人啊?我这不是越描越黑吗?嘿嘿嘿,还是绕过这个不提,装糊涂不说的好。
我一听霄姐这样的言语我的头都大了!要是在平常,我听到她这样罗嗦,我会夸张地做出痛苦状,立即向她讨饶,希望她快快打住,假如还不成,我会赶紧找个理由,立马逃之夭夭。
霄姐就怕别人说她老,不管别人是故意还是无意,当然也没人敢在她面前故意说,除非是老板(老板是个有风度有气质的人,这样的话根本就不可能说),否则我会让说错话的人知道什么是祸从口出的。别人无意中说了她,她只会气在心里不理人,表现出很大度不予计较的样子独自走开,可要是我无意中说了她,得!那我当天的日子就甭想好好过了,她非要问清楚了我什么意思,直到我苦苦求饶被她严重打败,她才会不计前嫌嘻嘻一笑饶了我,我经常被她弄得哭笑不得。
其实,她应该知道,她现在这个年纪正是女人味十足的时候,不都说半老徐娘风韵犹存吗?况且离半老还有那么一截子距离,自己又很会保养,曾经有过辉煌的时装模特经历,身材好得都无法用语言来描述,该凸的地方绝对的凸,该凹的地方又是彻底的凹,绝对没有一点点累赘,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都是那么魅力十足,显得比那一帮姑娘们还年轻、还有味道多了。
没听过鹤立鸡群这一说吗?这就是专门说你霄姐的呀!霄姐你就是那只孤傲的高贵的聪明机智又不失温柔体贴善良美丽的领头鹤啊!嘿嘿嘿,当然,这些话是不可以让你听到的,否则,你比南极的企鹅还能显摆,还要跩呢!
霄姐不是不讲理的人,她做事头头是道非常果断干练,红楼里面大大小小男男女女没有一个不佩服她,我们娱乐城能够在当地异常的红火,里面帅男靓女那么心甘情愿,一待就是好几年,都是与霄姐的工作能力分不开的。
她对别人非常讲道理,但我却享受不到这么好的待遇,只要我稍不留神得罪了她……唉,不提也罢!
我听她又如此与我胡搅蛮缠,我赶紧说:“得,得,得!我错了,你饶了我行不?你把我当成你肚子里的一股气,抬一抬漂亮的小屁屁,给放了行不?”
“你这个臭小子,跟你姐说话也没大没小?呵呵呵!”霄姐也感觉到这个节骨眼儿不是开玩笑的时候,于是,又正色道:“木森,你自己要当心点啊,你打伤的那个小青年,现在还在重症病房没有苏醒过来,你下手也太重了,医生从夜里抢救到早晨,总算没有当场死去,但现在还没有脱离危险期,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还在重症病房观察着呢。”
“其它还有什么情况没有?”
“警察已经来过这里了解了经过,已经备案了,都在找你,你最好躲远一点儿,千万这时候不要让他们找到了,只要人不死就有办法解决,要是现在被他们抓到,肯定要把你关起来,除非那个小青年不死,我们好想办法保你,要是死了,你可就完了啊!”
我能够感受到,霄姐说到这时候已经有点流泪了。我在仔细地听,霄姐接着说:“木森,你千万千万要藏好,不可以大意了啊!你是个聪明有头脑的人,姐就看中你这点,自己一定要小心,没有钱了你只管说,我给你把钱打过去。”
霄姐是一个细心的人,她知道干我们这行随时都有可能遇到不测的事情,万一遇到麻烦需要到外地躲避,身上没有钱是很困难的,但这一般遇到的又都是突发事件,当时身上不可能准备有很多的现金,即使自己随身装了张银行卡,卡里面有大量的钱,有时候也是不敢随便去银行取的,怕的是警察已经监控了银行卡,去了也就等于暴露了行踪。所以,霄姐就私下里用她的名字给我办理了一张卡,平常也不用,但我随身始终是装着的,只要是到了危险的时候,她就会往卡里面打钱,我再从柜员机里面取,一般警察是想不到的,所以很安全,让我在外不至于过得太窘迫。
她这样做是要冒着一定的风险,万一犯的是死罪,被警察发现是她在援助,那她的罪也不会轻,她明白这个道理还主动帮我,说明她是个非常够义气的人。
霄姐说的也很有道理,这个时候那小子还不清楚是死是活,万一我被警察抓到了,那小子死了,我岂不是这辈子就玩完了?即使那小子没有死,警察一时半会儿也不会放了我。他们会把我严加看管起来,直到那个小子脱离了危险,霄姐和老板才能想办法把我给保出来,即使最终是出来了,但之前一个阶段还是要在里面受罪的。
所以,就像霄姐说的那样,我一定不可以大意,一定要时刻提防着随时而来的灭顶之灾。我就说:“我知道了霄姐,我会小心的,现在手里边还有钱暂时不需要了。你还好吧,生意怎么样?”
“我还好,你走了这儿还有你那一帮兄弟在照应着,建钢和冬子他们都很用心的,你放心吧,这儿你不要考虑太多,关键是你自己啊……”
手机里突然没了声音,我知道霄姐是为我担心,在极力忍着眼泪和我说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过了好大一会儿,我才说:“霄姐,你也多保重自己。我挂了,有事再联系。”
“嗯。”霄姐轻轻地说了一个字。
我把手机从耳边拿下放在手里看了好久,手机上的信号始终在连接着,霄姐不忍心先挂断,我望着手机上的时间一秒一秒在跳动,不知道应该怎样再去安慰霄姐,终于叹了一口气,还是按下了停止键。
这是一个尚未竣工的楼,四周的墙壁已经砌好,还没有最后泥上一层厚实的墙面,整整齐齐码在一起的红砖,就这样突兀在眼面前,显得每一个房间都十分的狭小,地上狼藉一片,也许是顽皮的小孩经常光顾的原因,北面大客厅一面墙的拐角留下了几摊清晰的尿印,蜿蜿蜒蜒交织在一起,似一副看不懂的抽象派的画,在其旁边贸然凸显一泡努力盘旋向上的屎,像极了缩小版挺拔的山峰,只是由于时间久了,早已干瘪了下去,从而失去了原有的苍绿。显然这里已经很久没有开工了,与周遭机器轰鸣的工地相比,这里愈加显得寂寥与压抑。
楼上有许多窗口,只是还没有安装上窗户,从窗口望去,远远的天灰雾蒙蒙,风不时从这面窗口进来,又从另一面窗口出去,吹去了楼里的潮湿和污浊,却怎样也无法吹去我心中的郁闷与无奈。
我的视线朝下望去,心里在想着大海怎么还没有回来?我拿着手机在手里把玩着,想给大海打个电话,但又怕他和警察纠缠在一起,忍了忍终于还是没有打。正当我准备把手机装进口袋,忽然,老远看见大海朝着回家的方向赶来。
靠!才多久不见,这小子怎么弄成了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