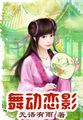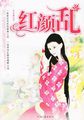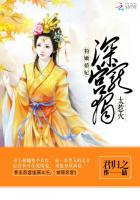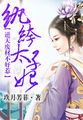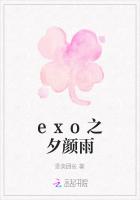接到益州来的信,李恪着实乐了好长时日。
十七想也不想甩下一句话:“肯定是杨书瑾给你音信了吧,也不知三哥乐什么,人家现在又不是你的。”
“唔,你是愿意见她笑不似笑的模样还是这般怡然自得?”李恪倒未变脸色,笑着问了一句,十七顿时了然,也不禁莞尔。
如果用尽全力抓不到,倒不如放手来的干干脆脆。李恪也不是拖沓之人。
“等朝中之事安定,三哥打算怎么办?”
“十七以为还能如何?你必也是知晓才会救出杨崇敬不是,”微微抿茶李恪一笑,看向她又道:“我们这样的身份,如何能逍遥自在,我不犯人亦有人要犯我。”
“是,三哥,我当初也有私心,被框框条条束缚了太久,这也不能做那样又不行,看着她便总觉一切都还有希望。”
“十七,我若有能力护得你们,该是多好。”李恪轻叹,伸手抱住她。
“没事的,三哥,我已经长大,自己能够保护自己,你心底惦记着我就已经很开心,”皇家情薄,李恪却打小对她很好,能到这份上实属不易:“看来我们兄妹倒也不比书瑾他们差到哪去。”
“唔,那自然。”
明明没有什么可以摆弄的两人却还是张罗了四五天,家里安顿好之后开始想着安生之计。
倒也不是没钱花活不下去,只是总不能真的什么不做天天在家腻歪,感情再好久了也难免生厌。当然这句话只针对杨书瑾而言,其性情之不安分,有目共睹。
杨书瑾那开爿小店的想法首先被否决,二人本就身份特殊,这益州虽然与长安城偏远但也还是大唐国土,抛头露面万一有人认出他们再要走可是难上青天。杨书瑾也明白,便皱着眉头细细帮衬思量起,稀奇古怪的想法不停往外冒:
开妓院?受了一记幽幽白眼;
情报局?杨崇敬额上青筋乱跳;
啊,要不开武馆吧,这么一来她还是太极拳的鼻祖……杨崇敬直接无语。
“好了,这事情交由我来想,我们出自官宦人家,看似能写会描,但拿来谋生活却是一无是处,约莫也只能开个私塾教人识字。”杨崇敬迅速打断她滔滔不绝的天马行空,说出自个脑中想法的大致走向。
撑着下巴撅起嘴不满他的一口否定,想想他的话又道:“诶,开私塾是挺低调,但很没新意呐。”兄妹再度陷入苦思。
不料两日后,杨崇敬真的拿出了主意——替人修字补画。
此想法得到了杨书瑾的大力赞同。
前些年魏王李泰成立学馆后,整个大唐盛行出一股子收藏字画以彰显学识的风气,当然其中多为做做样子的有钱人,收来的字画甚为贵重却不会保管,以致很多惊世之作被损,难逃丢弃的命运。杨崇敬一手好画,且对各家手法都甚为熟悉,补画根本是小菜一碟。
当然杨崇敬的考虑不止于此,还深深顾及了杨书瑾。她本来就什么都不会,唯一拿的出手的也就是写两个字而已,修字补画便意味着她也能帮得上忙。
这活计低调又有爱,杨书瑾给予了高度评价。
地址选在一家装裱字画的店家隔壁,杨崇敬与那店家说好让其帮忙做宣传,进一笔生意三七分成,店家自也是十分乐意。
平定下来,杨书瑾倒也是很有良心的及时将一切汇报给远在长安的李恪,洋洋洒洒写了不少废话又对近日里皇上立晋王为太子一事加以叮嘱,最后愣是用了两个信封才装下。信送出之后,杨书瑾这才知道,原来李恪给他们兄妹的那两个侍卫原来是做送信之用,小心谨慎之极。此番思量又不免让她一番敬佩。
虽这般两个侍卫是有些大材小用,但不得不说效率的确快了很多。想当初她在安州给杨崇敬写封信,一来一去少则一月,多时两个月也都十分正常。所以大半个月后接到李恪的回信不免诧异了几分。
“吴王是否还好?”看着她诧异,杨崇敬不禁搁下手头事情走近问。
“没有,我还没看,只是感叹速度快。”回神连忙拆开,瞅着封上那名为“吴恪”的落款又是一笑。
擦擦手,杨崇敬也没告诉她其实信件是可以被人拦截下这一事实,微微抿嘴接过她看完的一张。
“皇上改立晋王一事果然与李恪有干系。”看完信杨书瑾皱眉轻轻道。
“你不早已料到,没想吴王对你这般信任。”轻轻一笑,将信又收好。
“唔,我也没想到,利用晋王压下魏王的确是一个好办法,”点头对李恪信中之事表示赞同,又嘻嘻一笑凑到杨崇敬面前:“于是,你是在吃味?”
“是又如何。”揽过她脑袋对着唇轻轻一啄,勾唇笑着。
杨书瑾没骨气的闹了个大红脸,喃喃道“这是在店里,注意注意”,说完却又自个忍不住回亲了一口,咳了两声:“嗯哼,回家看我怎么收拾你!”话是说的很大气,回到家却也只有被收拾的份。
日子在收拾与被收拾中过得挺有滋味,杨书瑾奉着普及科普教育的理念,小心翼翼跟杨崇敬说了近亲生子的重大后果后,杨崇敬若有所悟,道:“怪不得王大人才华横溢,千金却生的有些痴傻,原来表家兄妹也不行。”
杨书瑾的意思当然不是为了表达这个,他的独子杨静业在那场大火中亦没有保住性命,也就是说杨家至此绝后。
“你又想多了,不管是一场大火还是论罪而处,杨家上下都逃不了一死,静业死的无辜却着实好过亲眼看着家破人亡,如今杨家已灭,你我本因都是死人,还活着便是上天恩典,该知足了。”
“那如果一直没有孩子……”自己毕竟比他多接受了近千年的文化,在这个养儿防老的年代来说,不要孩子的思想还是太先进了一些。
“听你说适才那番话我的确有些诧异,不免心下一空,只求不得也唯有作罢不是?”只短短一瞬杨崇敬道就思量出结果,就好似根植心中一般,这般想着杨书瑾也不住笑了。
二人除了杨志诚一贯并无关系深厚的亲眷,过继什么的是指望不上,领养应当还是可行的。
揣着这个想法平日里没事也会去关注一下,而随着时间过去,兄妹二人修画补字渐渐在益州城也小有名声,日子清闲却也挺充实。就好比回到当初的杨府,彼此之间毫无间隙,亦没有什么烦心事。
益州的生活倒是稳稳当当没出什么乱子,可一年一年从长安来的书信却是让杨书瑾有些担忧。
太宗似乎想从上一届太子那里吸取教训一般,对新太子是极度护佑,几乎遣了朝中所有重臣为太子师,不得不说这些大臣均是腹中甚有才华者,但才华却不止于教学这一方面,比如为正太子之位而做出的小动作。
贞观十七年前太子初被告发谋反时,太宗念情,只将他贬为平民流放黔州,没想十九年时猝死黔州,不要说李恪,他兄妹二人远离长安城都觉得事有蹊跷。
而贞观二十年,太宗也觉晋王性弱想改立李恪为太子,不想遭到长孙无忌大力反对,以致太宗都有所怀疑是否因李恪非他亲外甥而如此这般。只最终太宗仍是坚持初始意见,立晋王李治,封李恪为藩王遣往封地安州。
杨书瑾是觉李恪现如今争权夺位的心思比从前要淡了很多,可就算他这么想别人不会相信,有心人若想陷害,怕李恪仍旧难以清闲。
所以偷偷去安州看望他们的想法断然被李恪驳回。只道暗线多,不宜涉险。杨书瑾明白,不住黯然了好几天。
隔日李恪从安州捎来不少物什,说是约莫隔掉几月会安生一些,适时再接二人前去一聚。
这一适时竟然是等了一年有余,书信比在长安城时还慢下几分,杨书瑾没料李恪行动会如此受限,心想与太宗年迈必有着不可或缺的关系,扶持李治的人自然会想着办法除去这个颇得民心、还被皇上提名的吴王了。
想要遣书问个究竟,益州意外来了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