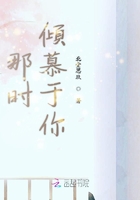大军走出大别山时,已是十月初五。
大别山外,处处皆为秦晋两军交战的战场,为了防备中线大军出山遇伏,十天前,护军便派了一万八千人守在出山要路接应。
抚军是最先出山的,李穆然一出山,便遇见了熟人统领护军一万八千人的都尉正是昔年新兵营前军都尉拓跋业。
四年不见,拓跋业鬓如染霜,但玩世不恭的性子却没有改。李穆然与他会面的时候,隔着老远就闻到了他身上的酒气。想起昔日之事,李穆然不觉暗自好笑。
拓跋业骑马到了李穆然面前,翻身下马,抢先拜倒。李穆然不肯受他的礼,也忙下了马,上前两步膝下一弯,把拓跋业托了起来:“拓跋都尉,向来可好?”
拓跋业道:“托将军洪福,末将很好。前边十里处有一县城名为金寨,城中设有驿馆,请将军带军到金寨安营后,前往驿馆歇息。”他言谈举止不卑不亢,可却让李穆然觉得他和自己之间生分了很多,再不像自己当百将时所遇的那个都尉了。
李穆然略微有些不快,但也知二人身份已变,拓跋业只怕比自己更加难受。他没再多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道了一句“辛苦”,便转身上马,传命下去,抚军继续向东,直往金寨而去。
抚军抵达金寨时天色尚早,李穆然被拓跋业的亲兵请到了金寨驿馆中,等候慕容垂等人。他闲来无聊,本想在城中四处走走,可是放眼望去,街上除了兵还是兵,比军营之中还要乏味,便绝了出驿馆的念头,找驿丞要了份最新的邸报先自看着。
那邸报上写的全是近些日子东线战况。看样子,圣上已占着寿阳城,与北府兵隔江相望。这些日子两军在水上你来我往,打了不少小仗,秦兵输多胜少,可是晋国惧怕秦国强大的兵力,也不敢过于紧。双方在淝水僵持不下,已有三四天了。
李穆然看完了邸报,将其放在一旁,不由阖目叹了口气。他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形终于发生了:秦兵没来得及度过淝水,水战又不能取胜,长此以往,大军屯于寿春只会空耗钱粮,难有进展。只希望圣上能及早意识到此战已成鸡肋,早日收兵回朝才是。可若当真退兵,国中朝中必然乱作一片,苻坚如日中天的声威,就此将一蹶不振。
李穆然站起身来,走到窗户旁往外看去。驿站之外,是川流不息的兵士,他们每个人的神情都很凝重,比抚军士兵要紧张许多。想想也对,东线打得如火如荼,金寨往前直至淝水都是一马平川的,他们面临的是每日都可能偷袭过来的晋军,抚军比起他们自然是轻松得多了。
李穆然又耐着性子等了将近一个多时辰,那张邸报被他翻来覆去看了许多遍,直到每个字他都几乎能背下来,慕容垂和慕容冲二人才终于到了驿馆。
慕容氏叔侄二人说笑间走进会客厅,见了李穆然后,慕容垂笑道:“肃远久等了。”
李穆然微笑道:“不算太久。末将一直在看邸报,不知不觉时辰就过去了。”
慕容垂道:“东线战事已成拉锯,圣上催了好几次要我们赶紧支援,今明两日在金寨略作休整,后日就启程。”
李穆然问道:“是和圣上合军,还是绕路而行?”
慕容垂道:“往南走颍口,再东进,与圣上形成掎角之势,两面夹击。”
颍口位于淮河与颍水交界处,到颍口后顺留而下,下一处便是淝水与淮河交界的寿阳。金寨距离颍口不过四五十里的路程,大军赶得快些,一天便能赶到。
李穆然正自暗算时间,慕容垂又笑道:“今日休息,肃远就别只顾着想军务了。拓跋都尉安排了接风酒宴,一会儿可别喝醉了。”
李穆然笑了笑,暗想拓跋业安排的酒宴,只怕那真是“酒”宴了。他见慕容垂话里似乎还有话,便问道:“大将军,酒宴上还有别人么?”
慕容垂颇为神秘地笑看了他一眼,道:“酒宴上没有,酒宴之后就有了。至于是什么人,我先不告诉你。”
李穆然满怀好奇地跟着慕容垂、慕容冲二人去了接风酒宴,觥筹交错间,他才见到了昔日他熟识的那个拓跋都尉,不由想起那一年南阳城百花楼中,他自己作为百将陪席之事。那时他还是个懵懂无知的新兵,时间一晃而过,眼下他已是手握一方军权的将军了。而想起了百花楼,他就不由想起了两位故人,一位是郝南,一位则是翠锦了。只可惜郝南这次没有跟着拓跋业一同过来,而翠锦也就是严府的那位石氏了,不管怎么说,那终究是他生命中的第一个女人,虽然是死在他手里的,可这时回想,难免有几分唏嘘。
酒足饭饱,慕容垂带着二人到了驿馆后门。李穆然不知大将军是要自己见什么人,甚至猜测是圣上从寿阳赶了来。然而没想到的是,三人到了后门,等了小半个时辰左右,就见慕容烈在前带队,十几个亲兵簇拥着四辆马车停到了门前。
第一辆马车下来的是慕容垂的小段夫人。
第二辆马车下来的是慕容冲的夫人。
第三辆马车,下来的竟是郝贝!
李穆然已无心关注第四辆马车里坐着的是什么人,只是怔怔望着郝贝,而郝贝也怔怔地瞧着他。两人四目相投,几乎都疑身在梦中。李穆然愣了好一会儿,直到慕容冲在他身后轻推了一把,笑道:“肃远,你看人都看傻了!”他才蓦地反映过来,几步走到了郝贝面前,唤道:“阿贝!”
郝贝紧紧拉着他的手,眼泪在眼眶中转了几圈,但还是生生憋了回去,只是脸却涨得通红:“相公!”
李穆然对她温然笑了笑,旋即拉着她走到慕容垂面前,道:“大将军”
他还没说完话,慕容垂已截口说道:“我怕长安不稳,才让她们收拾东西出了长安。明天就要北上去祭祖。”
“明天”李穆然扭头看着郝贝,暗忖两人只有这一天相聚么?明日她们北上祭祖,看来慕容冲推测中的,大将军的确有意攻取邺城。如今所有人的家眷都已逃出了苻坚的掌控,那么以后造起反来,后顾之忧便算是没有了。
李穆然长舒口气:总算郝贝是离了长安那个险地,暂时安全了。直到这时,他才知道分别多日,他究竟有多牵挂郝贝。虽然平日军务繁忙,他很少想起她,可这时见了她,他竟抑制不住嘴角的笑,只想多瞧她几眼,多陪她几天。可是只有一天时间这太短了。
他恍惚间听到慕容垂说让他和慕容冲好好陪陪各自的夫人,又说明日辰时夫人们便要离去,随后他就拉着郝贝回了驿馆自己的房间。
李穆然与郝贝到了房中,他把门甫一关上,便一把搂住了郝贝。郝贝只轻唤了一声相公,后边的话便全被李穆然的吻堵了回去。她身子一轻,已被他拦腰抱起
两人翻云覆雨,几度欢好,也不知折腾了多久,才相拥相抱,倦极而眠。
李穆然睡到半夜,迷迷糊糊觉得唇上一动,他睁开眼,见幔帐之外灯火昏黄,幔帐之内郝贝伏在自己怀中,正忽闪着一双大眼睛,伸手轻摸着他唇上方长出的胡茬。
李穆然微微一笑,问道:“怎么了?”
郝贝枕着他的臂弯,轻笑道:“我在想你要是留了胡子,是什么样子。”
李穆然笑道:“那我现在开始留,等打完了仗再见面,你就知道了,就怕吓到你。”
郝贝咯咯笑道:“不要不要,我还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你要是一脸大胡子回家,我赶你出去!”
“回家?”李穆然微愕,郝贝难道以为这次是真的北上祭祖,以后还要回长安么?
郝贝道:“是啊。我留了李顺看家。我把家里收拾得好好的,每天都等你回来。”她把头埋在了李穆然怀中,低声道:“相公,我很想你。”
李穆然心中一暖,将她又抱紧了些,附在她耳边低声道:“我也很想你。阿贝,我有正事要和你说,你要认真听。今天说的话,千万别跟别人讲。”
郝贝看他如此郑重其事,忙打起了精神:“什么事?”
李穆然沉声道:“阿贝,你们这次离了长安,以后只怕很难回去了。”
郝贝大惊,连声问道:“为什么?”
李穆然低声道:“秦晋大战一了,大将军就要反了。”
郝贝整个人愣住了,可是她自幼长在慕容家,对于慕容垂的野心,或多或少也有了解,只是没想到这件事情来得这么快,这么急,这么突然。她怔了怔,问道:“你呢?”
李穆然道:“我跟着一起反。正因如此,大将军才会把你们接出长安,就是为了不让我们担心呐。”
郝贝长于军务,自然明白李穆然所言的重要性。她静了静,略略平复了一下心绪,才蓦地抬起头来,直视着李穆然的眼睛,道:“相公,你尽管放心去!我能照顾好自己,绝对不会出事!”
郝贝说得笃定果断,让李穆然心中一片悸动。他紧抱着她,笑道:“这才是我的好妻子!”
得他称赞,郝贝甚觉得意:“那当然啦。不过眼前这场仗怎么办呢?”
李穆然道:“输多赢少。但我早做了准备,我不会有事。”
郝贝点头道:“好!”她只说了这一个字,不多问也不多言。她对李穆然的能力是全然信任的,从没有质疑过他的任何想法,甚至对他的一切决定都是全然的支持,这与冬儿是截然不同的,而李穆然爱的也正是她这一点。李穆然心中感动之余,想起曾答应过她的事,便道:“阿贝,这场战打完,我要去冬水谷参加冬儿和庾渊的婚礼。之后我就再不见她了。”
郝贝听到“冬儿”二字,身子不由微微一动,可她并非全然不知好歹,与李穆然相处这么久,她也知道他能做出这个决定是何等不易。她轻笑了笑,道:“其实我也不是真的就不让你见她。那时非要你答应我只是想知道,在你心中究竟是我重要些,还是她重要些。”
李穆然静了静,随后道:“你是我妻子,谁也比不了,自然是你最重要。”
郝贝听了这句话,眼中一潮几乎哭了出来,她轻声道:“相公,对不起,之前我对你不好,以后都不会了。”
李穆然微笑道:“没事。不吵不闹,何来夫妻?”
次日一早,几人依旧到了驿站后门,送女眷离去。郝贝临上车时,李穆然紧紧攥着她的手,笑道:“保重保重,就是保住重量。下次见了你,你要再瘦,我要不高兴的。”
郝贝白了他一眼,笑骂了一句“讨厌”,语罢,提裙上车,进到车厢中后,又掀帘看了他一眼,说了一声:“等你。”
李穆然“嗯”了一声,随后就见车马辘辘,渐渐行远。过不多时,那车已消失在道路尽头。他第一次想让郝贝陪自己一同在军中,可也知大将军断然不肯。毕竟,慕容垂此次让诸位夫人到金寨,一是为了告诉他们家眷无碍,二来,则是告诫他们家眷的确在他慕容垂的掌握之中。
慕容垂拍了拍李穆然与慕容冲的肩膀,道:“别看了。咱们收拾收拾,也该回军中准备明日启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