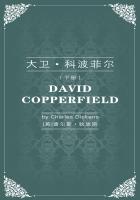“郝作家真是雷厉风行啊,我前天才把请柬发出去,今天你的策划方案就出来了,真是神速啊。我到你办公室,还是你来我这里?”刘青在电话那边问。
“当然是我到局长办公室了,怎么可能让局长到我这里屈尊呢?”郝从容放下电话就奔了文化局,她心里明白自己去见刘青的真正目的是想打听演员祖灵艺。
刘青没撒谎,的确是刚刚开完会,办公室里一股烟味,在局长办公室开会,不会是什么大型的会议,最多是分管部门的头头小聚,郝从容一猜就猜到了。
刘青说;“什么事能瞒过作家的眼睛啊,文学是人学,一点没夸张啊。”
郝从容笑笑:“别借机炫我了,你开什么会、什么规模,跟我也没关系,我跟你只谈工作,我刚刚在办公室初拟了一下晚会的方案,你看看,合不合你这大局长的胃口。”
刘青让郝从容坐在沙发上,又倒了杯茶,然后坐在郝从容的对面看策划方案,看了一会儿,欣喜地说;“这方案不错呀,相当出新啊,看样子我让你当我们晚会的总策划,还是慧眼识珠啊。”
郝从容趁机道;“演员的阵容很关鍵,邀请什么档次的演员决定着晚会的成败,我上次帮省里一家单位策划了一台慈善晚会,因为演员档次不高,应该说成功率不是很大,但赞助拉了不少,从经济的角度考虑,还是很不错的。”
“你们邀的哪些演员啊?”刘青忍不住问。
“都没什么名气,就算方菊是大牌的了,还有什么祖灵艺等等,都是新演员,因为电视台现场直播,上边领导推荐了不少新演员,哪个领导都不敢得罪,都得上台亮相。”郝从容故意把祖灵艺抛了出来。
“小祖这个人你可别小看,她身后的背景大,她是带编制到市歌舞团的,全额事业编制,除了团长,只有她占了这样一个编制,我亲自给她办的手续,来那天省委的小车亲自送来的。”刘青眩乎地说。
“你别让我眼晕了啊,她背景再大,又能是什么背景?”郝从容追问。
刘青看看郝从容,觉得她问得过细了,便说:“什么背景我也不太清楚,好像是她的亲姑姑是省里一个演艺院团的副团长,她姑姑的老公公曾经是一名老干部,据说现任省委书记就是他举荐提拔的。”
“哟,这背景够厉害的,这个人倒可以利用一下。”郝从容脱口而出,暗想难怪省委办公厅秘书长给她写条子推荐呢。
“利用她什么?”刘青警觉地问。
郝从容感觉自己失口了,急忙说;“利用她请些名演员给晚会助阵啊,你这台晚会是由政府出资的公益性质的晚会,名演员越多越好,当然他们的出场费也很可观,这笔钱从哪里出你要有所思量。”
刘青想想说:“名演员不必太多,有一两个撑撑场面就可以了,究竟请谁最后再商定吧。”
郝从容急忙说:“这事我来办,保证请的人让你满意。你把祖灵艺的手机号码告诉我怎么样?”
刘青一下子意识到郝从容来找他的真正目的了,她是奔着祖灵艺来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个女人,嗅觉太灵敏了。上次因为斑点马画展的事情,刘青已经跟郝从容打过交道了,她的办事效率和讲信用的程度都让他称赞和佩服,她在市委换班子的关鍵时刻突然来找祖灵艺,要她的电话号码,这里面说不定暗藏玄机。他认真地看了郝从容一眼,郝从容也正看他,两人目光对视的一瞬间,又快速移开了,刘青暗想但愿我能帮你搭个梯子,你从这个梯子攀上去了,我以后也好迈大步。
刘青立刻说出了祖灵艺的手机号码,跟着又说:“她的手机经常不开,她还有一个小灵通,你也记上吧。”
郝从容飞快用自己的手机记下两个号码,说:“看样子你真是跟她联系紧密呢。”
“哪里呀,祖灵艺当下是市歌舞团的台柱演员,我能不关心名演员的行踪吗?领导必须是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啊。”刘青卖乖说。
郝从容笑笑,暗想这个刘青副局长也真不是个省油的灯啊,他能很周全地考虑事情,安排布局,的确是一个干才。
为了不让刘青生疑,郝从容又跟他谈了一些与本台晚会不搭边际的事情,诸如艺术院团的改革啊,人员的去留啊。
刘青不以为然地说:“文化产业好啊,可是有几个艺术院团能顺利转轨成为产业?中国最难做的事情就是人员安排,留谁去谁,谁比谁的艺术高超,到时候还不得人脑袋打出狗脑袋来呀。改革这样的问题呀,最好还是留给别人去做吧,弄不好一片骂声,古往今来,教训太多了。”
郝从容只笑不语。她端起茶杯喝茶,将茶喝尽,而后告别了刘青,匆匆回到自己办公室。
进了办公室,郝从容第一件事情就是给祖灵艺打电话。
十一个自然组转下来,祁有音心里对长水村大体有谱了,这里一缺资金,二缺人才,想发展生态农业,必须有足够的资金和知识型的人才。而这十一个自然组里最困难的组当属山脚组,可这个组的自然资源又最丰厚,背靠青龙山,植被茂盛,空气中负氧离子的含量是城市的数十倍,发展旅游观光产业的优势得天独厚。但这里地处偏僻,交通成为大问题,尽管村里修了生产路生活路,可与旅游观光产业的要求相比,这样的路只能算初级路。
祁有音在山脚组住了三天,这三天她始终跟孙大妹在一起,每到一家,祁有音的心里都会不平静,留守的农家妇女既要下地侍弄苗木,又要给孩子烧饭,家里有老人的还要侍奉老人,可妇女们大多没什么抱怨,自力自强的意识很浓烈,有一位妇女在祁有音面前伸出满是老茧的双手说:“你看我的手跟男人的手一样坚硬,男人们在外边创业,我们在家照样能赚钱,只是这赚钱的路子太窄了,山脚组靠山却吃不了山,如果这里能发展旅游,我们家家户户都可以办农家乐,我在外边看过这样的地方,很来钱的,发展好了,男人们都守在家里了,不去城市打工了。”
祁有音安慰她说:“等着吧,这一天不久就会到来的。”
祁有音在孙大妹的陪同下,还看了山脚组被长水村评定的五好家庭,她们进院子的时候,媳妇正给坐在院子里的婆婆梳头发,婆婆九十出头了,思维清晰,只是前排的门牙掉光了,媳妇很细心,把婆婆的头发梳通后,将木梳衔在自己的嘴里,用一根暗红色的头绳扎住头根,再用一个黑木卡子捌在脑后,九十多岁的老婆婆头发长到背部,除了头顶有点泄,鬓角有点白,只看这头浓发真不相信她已九十高寿了。
孙大妹在一旁介绍说:“九十高寿的老婆婆我们山脚组有六个,眼下都很健康,都是媳妇侍奉着。在家的妇女其实很累呀,我常想要是山脚组经济发展起来了,办个敬老院,不光城里老人进敬老院,农村的老人也照样进敬老院,老人难恃奉,老小孩老小孩。”
梳头的媳妇说:“谁都有老的时候,我婆婆常说,小孩别笑白头翁,花开花落几时红?我现在好好恃奉婆婆,将来我老了,我的儿媳也会好好恃奉我,我现在是给孩子做榜样呢。”
祁有音听着想这里的民风如此朴素,真应了那句老话了,“近山而仁,近水而慧。”在省妇联她看了太多的因婆媳不和引起的家庭矛盾,有的导致了家庭的破裂,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媳妇不敬婆婆,而婆婆又不接纳媳妇。山脚组远离城市,交通闭塞,却保留了这么好的传统美德,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莫非是城市的开放破坏了原始的美德?……这个问题,祁有音回去后要好好思索一下,中国的妇女,特别是农村的妇女,在和谐社会究竟要承担一些什么?
晚上,祁有音住在孙大妹家里,这使她们有很多话谈,白天看到的东西,到了晚上,坐在农家院里,享受着清澈的月光,一幕一幕看过的情景像过电影一样在她的眼前浮现,她便不停地问着孙大妹,孙大妹也就不厌其烦地答着。
祁有音:“在家的留守妇女,对在城里打工的丈夫放心吗?”
孙大妹一笑:“开始不放心,村里进城的男人也确实做了很多对不起老婆的事情,偷鸡摸狗的,老婆摸到了影,纷纷跑到城里闹过,也想离婚。后来觉得离婚对孩子不好,闹闹也就算了,男人嘛,想让他们一辈子跟一个女人一条心是不太可能的。就拿我来说吧,我那口子自从离开山脚组,就没怎么回来过,回到家也像走马灯似的打个照就走,后来我听说他在城里养了小女人,有一天我就闹去了,正好他跟那小女人在一起钻被窝呢,我是晚上去的,之前把他的住址打听得一清二楚,到那里就把他们逮住了,可那小女人根本不在乎,竟当着我的面说:‘你丈夫不爱你了,他只爱我,不信你现在就问问他。’未等我吱声,他真说话了,他说:‘我们离婚吧。我的确不爱你,我只喜欢城里的女人,城里女人细腻会生活,哪像你这样,粗粗啦啦的,只配喂猪打狗。’那小女人越发得意了说:‘呆瓜,识相点吧,赶快回村里吧,这里不是你呆的地方,这是城市。’我当时气得火冒三丈,还击她说:‘早晚有一天,你们城里人会往我们乡村跑。’小女人嗲着声音说:‘你们乡下人永远赶不上城里人,乡下人好不容易吃上肉了,城里人吃草了;乡下人好不容易娶媳妇结婚了,城里人又分居了……’她说了一大串话,都是贬乡下人的。回来后我就发誓要把山脚组建成美丽的家园,吸引城里人到这里养老,可我的能力毕竟有限。要是有人来我们这里开发投资,山脚组一定是个美丽的世外桃园。祁主任,您能为我们山脚组招商引资吗?”孙大妹用渴盼的眼光望着祁有音。
祁有音未置可否,没把握的事情她是不轻易许诺的。她想到杨亮,她大学时代的同学杨亮在她的鼓动下,给长水村盖了一座小学校,也算是很有贡献了,她能否再去鼓动他来山脚组投资建农业科技观光园呢?杨亮会不会骂她得寸进尺……祁有音不想继续思考这个问题,便将话题转到刚才的对话上,不由问:“那你现在跟丈夫的关系怎样?……”
孙大妹坦率地说:“本来从城里回来后,我是想跟他离婚了,可我舍不下婆婆,我婆婆86岁了,她32岁的时候我公公就死了,她守着这个儿子过了一辈子,我如果把她扔下走了,那个小女人是不会恃奉她的。所以婚也就没离,这房子是他回来盖的,我婆婆摸到了我们俩闹离婚的影,气得生了一场大病。我坚持没离婚,一方面是为了婆婆,另方面也是为了孩子,孩子正读高一,我怕对孩子的身心有影响。至于我自己嘛,我真没考虑那么多。再说,什么爱情不爱情的,到了我这个年龄,就是在一起过日子,愿意过就过,不愿意过就散,但不能伤害了别人。”
祁有音听着,暗下里偑服着孙大妹的胸襟,尽管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却能看到平凡生活中的奇倔。国家近三十年的发展,物质生活和人们的观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些东西的改变令人弄不明白究竟是对还是错,比如离婚率的高涨,这是一种进步还是一个误区,而离婚后是不是人就真的自由了?不承担家庭责任是人的真正解放吗?……
月亮的清辉静静地洒在小院里,透过树影落在她们身上,祁有音感慨道:“你刚才说的那句话很好,婚姻的成败要以不伤害别人为好,家庭就是一个小社会呀,我这次下来扶贫,顺便想搞一些这方面的调查,实事求是地写一篇论文。”
孙大妹说:“难得有省里的干部能深入到组里,祁主任您这么能吃苦,家里人没意见?”
“家里人支持我下乡扶贫,没有家里人的支持,我来不了。”祁有音说。
“您那位也是干部吗?在哪里工作?”孙大妹又问。
“他是个普通干部,也在省里工作。”祁有音急忙转移话题,有关她的背景,事先已跟省扶贫办打过招呼,不向任何人透露,否则会给她的扶贫工作带来不方便。如果知道她是省委副书记的夫人,谁肯安排她住在山脚组孙大妹的家里呀,那她还怎么调查研究、获得最前沿的生产生活情况呢?
一只蚊子落在祁有音的胳膊上,飞快地叮了她一口。祁有音开始抓痒。
孙大妹站起身,从房檐下扯了一根用艾草编织的火簾绳点着,小院里立刻弥漫起艾草的青香,祁有音已经好多年没闻过这味了,她大吸了一口气。
蚊子跑了,祁有音和孙大妹的心都在艾草的香味中安定下来,孙大妹继续跟祁有音讲述山脚组的事情,东家长李家短,哪家的女人能干,哪家的女人孝顺,哪家的女儿嫁出去了,哪家的新媳妇怀了孕,家境好的人家都不肯多生孩子了,低保和独生子女费对计划生育工作起了一个推动作用。……
夜静得出奇,风声像是一支小提琴曲,给城市和乡村的两个女性伴奏,她们越说越兴奋,把天边的大毛愣星都说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