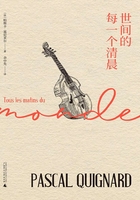“不碍事不碍事。”三把火急了,“传说嘛,传到哪里就在哪里说。”
见三把火的背影尾随嘉宾进了一线天,伪游客一哄而上围住沈局长索要贵宾卡。“排队排队,”沈局长将金光灿烂的贵宾卡捻成扇形举过头顶说,“成群结队的像什么话?两三个两三个进去,拿出游客的好奇来。”
白达卷起红旗握在手上,指挥车辆调头排好,让老师们带队撤走鼓号队。
临时培训的三个导游,来自第一医院的护士叫徐光华、来自实验小学的叫吴琳、来自机关文印站的叫李春玲,跟劫波凑在水泥浇铸的伪木屋里正好是“波光粼粼”。四人抬出售票桌打标分,劫波人小胆大,也比她们专业,主动肩负起望风的重担:坐在面路的位置,见有人来马上掀起桌布一角遮了扑克。
然而,“波光粼粼”却好景不长,李春玲没两天就走了,原因是文印站是承包的,经理说了,要嘛赶紧回来打字,要嘛我换个人打字。水波没有光如何粼粼?三个人打不了标分,打争上游还是可以的,劫波仍然坐面路的位置。紧接着吴琳也要走了,她男朋友在部队当连长,喜欢的就是教师,而不是导游。沈局长出于创建拥军爱民模范城的长远利益考虑,尊重连长的喜好,同意吴琳回校上课。
四个人少了两个,还能玩什么牌呢?尖乌龟吧。为了防止对方算出自己的牌,每次洗完牌都要抽掉一部分,劫波也没有固定的位置了,因为经验告诉她们,根本就没人会来买票。没有游客,就两个导游兼售票这么玩着,便玩出一股寂寞来,有时峡谷里会传出一声莫名的怪叫,徐光华身子一哆嗦就生出悔意。“还不如回医院算了。”她说。
“医院有什么好?”劫波手里洗牌、嘴里说话,“你以为你是医生还是护士长,你不过是个小小的化验员啊,拜托。”
“化验员好呀,工作清闲,环境又干净。”
“整天屎啊尿的,还干净?”
徐光华往后一仰,“呀”的一声怪叫,“没想到你这么庸俗,劫波,你身体里不也有屎有尿吗,男人照样把你当金枝玉叶。化验是科学不是美学,科学是来不得半点含糊的。”
“好了好了,”劫波将牌往桌上一拍,垛成两堆说,“快,抓牌。”
两副精美的蝴蝶牌扑克最终留不住徐光华一颗孤独的心,离开售票处那天,徐光华细细打扫遍地的落叶、擦拭堆积的尘埃,擦到铝合金钱箱时,徐光华发出惊声尖叫。劫波扔了抹布扑过来,到底是一场虚惊:钱箱里有一条蠕动的毛毛虫。徐光华捂住胸口惊魂未定,陪衬出劫波的从容,只见她打开钱箱,倒出毛毛虫,伸脚一踩,地上便成了一抹绿色。怀抱铝合金钱箱,劫波突然哭了,悲伤像放飞的白鸽,翱翔在伪木屋狭窄的空间。
“全是骗人,哦——,旅什么游,哦——,一分钱票没卖到,哦——,人倒跑光了,哦——哦——。”
徐光华离去的毅然决心被劫波三两下就哭没了,摘了一段手纸,帮劫波揩去泪水。“你也走吧,”徐光华建议,“我们一起走,一走了之。”
劫波“咣”的一声抛下钱箱,泪水又下来了。“你会化验,我会干什么?我读的就是旅游,我就会做导游。要死,我也死在这里。”
劫波并没有死在售票处,她灵机一动就得出结论:平时是断乎没有游客的,双休日守在那里就可以了。双休日一般稀稀拉拉会有几个来路不明的外地人,间或出现一对行装繁杂的情侣。有客人就好,收多少钱是小问题,关键是劫波不再寂寞。
那么,劫波平时在哪里呢?在哑巴的摩托车上。劫波斜背大书包的样子仿佛是个逃学的高中生,里头沉甸甸的,似乎装了十几门功课的书本作业。其实,劫波不是什么逃学生,而是帮姐夫收钱的财神爷;书包里也不是什么课本作业,而是一捆一捆的百元大钞。
在桃源,哑巴不再是个歪脖子搬运工,而是启蒙大众心智的开拓者。哑巴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人们,金钱自我繁殖的时代来临了。此前,纯朴的桃源客家人只知道钱可以买米、买油、买液化气,买房、买车、买自尊心;拙笨的人将钱藏进枕头里,每天晚上细数一遍;聪明的人将钱投进股票、期货市场,企图圆一个发财梦。现在好了,《鸡蛋的梦》一夜之间家喻户晓,这个蛊惑人心的故事是如此简单,简单到文盲都能听懂;这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又是如此深刻,深刻到最精明的生意人都跃跃欲试。
大家都在讲鸡蛋的梦,哑巴自己却被蛋壳困住了。桃汛那里每月要交六百六的会钱;亲兄弟明算账,婚礼上借贷的十万块,还了五万给白达,但每月三千的利息是要哑巴支付的。面对困境,不需要经济头脑、也不需要挖空心思,凭直觉哑巴就知道“以会养会”。一边靠桃花会得来的现金支付会钱、还借贷,一边寻找新的机会突围。
哑巴的家里盛况空前,从机关干部到果农、从医生到病号、从人民教师到下岗工人,甚至乞丐、甚至妓女,他们手里攥着、口袋里掖着、信封里装着从银行新取的存款、或者刚从客户手中接过的皱巴巴脏兮兮的纸币,被一只看不见的手驱赶到方家。方家像激流中翻腾的旋涡,又像高速运转的摇奖机号码珠,谁也来不及、也不愿意、更不可能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作冷静的思考,就被飞舞的会单迷了心窍。
方家的凳子再也不用擦了,会员的屁股将它们蹭得一尘不染;方家的地板再也扫不干净了,络绎不绝的人流带来数不清的垃圾。此外,方家的墙角总是留有可疑的痰渍、卫生间总有冲不去的腥骚尿液、洁白的毛巾也不知被谁抹得黑不溜湫,到处是喝过的茶杯、到处是踩扁的纸团、到处是水果皮瓜子壳。
新婚的花季忍无可忍,什么也没说,以“要写东西”为借口,住回陶家去了。当然,花季也用不着背一个象征离家出走的行李包,因为她自己的东西全都还在陶家。其实,哑巴知道,花季离他而去还有一层难以启齿的原因:自己阳萎了。自从新婚之夜花季问他“你是不是性变态”之后,哑巴的生命之根就从未雄起过,道理很简单,哑巴根本不敢叫花季唱《桃花结》,因为提这个要求本身就证明了他的性变态。当然,花季唱了《桃花结》哑巴就能重振雄风吗?天知道。
哑巴没空送气,阿强也不用他送气。阿强的燃具店也成了竞标桃花会的场所,液化气空筒横放垫好坐在屁股下,几箱未拆装的液化气灶垒在一起就成了填写会单的桌子,连铝合金卷帘门都不用开。收银的金牙齿整天不知去向,她收自己的会钱都忙不过来呢,哪有闲工夫去计阿强的蝇头小账。这样,哑巴的行径就倍受质疑,老婆不见了,却整天载着小姨子满桃源市乱逛。
焊了铁架的嘉陵70像先皇驾崩的老宫女,苍老、腌脏地蜷缩在墙角;而新买的进口大绵羊则像得宠的妃子,光彩夺目又趾高气扬。哑巴抖擞精神,白天载着劫波收款付款,晚上通宵算账。新粉刷的洞房墙壁上,贴满了各式各样的会单,会单泛滥成灾,没几天就遮盖了那个桃汛手剪的大红喜字。
劫波比花季矮一点,正值不识愁滋味的青春少年,在厦门被麦当劳、肯德基喂得结结实实,从背影看,屁股沉甸甸的。别看她屁颠屁颠跟哑巴瞎忙乎,其实也没干什么,只是将纸币按新版一百、旧版一百、五十分好,每一万元扎成一捆,码几捆在摩托车后箱,其他堆进新购的保险柜。二十、十元的就管不了那么多啦,扔在一个纸箱里了事,劫波要零花,抓一把就是。哑巴对钱有某种伟人式的冷淡,男人只要跟钱保持一定的距离感就意味着他有更大的志向,正是这种冷淡,让劫波对哑巴深深着迷。
会员散尽时,哑巴喜欢嚼着口香糖欣赏劫波数钱:尖尖的额头在灯光下闪烁亮泽,一缕长发遮住了半边脸,明显的双眼皮使洁净的眼角现出隐约的鱼尾纹,大门牙若隐若现,神气的鼻尖慢慢地挂上了细密的汗珠。哑巴陶醉了,陶醉在一种心痛的怜爱中;劫波陶醉了,陶醉在钱账的数算中。哑巴看出来了,劫波爱钱,尤其爱数钱,数钱的时候有一种天然的快感和天赋。正如劫波自己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