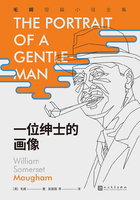而刘蓉娜播报新闻的时候,在电视里也常说“朴副省长”,当面也是那么叫着。所以,朴昊洋身边的人和相好的朋友,平常都叫他“朴副省长”,没哪个直呼他“朴省长”。
朴昊洋在电话里道:“强贵啊,你那里没人吧?”
张强贵回答道:“没其他人,就我一个人。”
朴昊洋道:“你等着,我马上就到。”
即刻,张强贵的耳机里就只有“嘟嘟”音在空中回响。张强贵从朴昊洋的声音中已听出端倪,事情有些不妙,很可能朴昊洋没当上代理省长。那又是谁当上了代理省长呢?
突然,手机的音乐声骤然响起来。
张强贵瞟了一眼,是刘蓉娜的手机号码,便接了起来。
“蓉娜小姐,你好!”
“张总呀,朴副省长有消息吗?”
“没有。你得到朴副省长的消息了吗?”
顿时,张强贵就有些幸灾乐祸,忘乎所以。他想朴昊洋果然够哥们儿,果然没有先给这个骚娘们儿打电话。
当然,要是朴昊洋当上了代理省长,为博得肉床单的欢喜,为刺激刘蓉娜激情满怀,为巫山云雨之时多些滋润,先给刘蓉娜打电话也说不定。今天事出有因,男人要以事业为主。
“张总啊,你真的没得到朴副省长的消息吗?”
耳机里的娇柔声中伴随着一份迫切。
张强贵这时候更加坚信自己的判断没错,朴昊洋没有给刘蓉娜打电话。由此可以判断,朴昊洋竞选代理省长已经失利,这个“港都蛟龙”又要屈尊一届,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了。
“朴副省长也许还没有散会。我们再等等吧。”
张强贵敷衍道。心里也有些焦急不安。他担心自己说得不投机,会惹得她反感,到时她在朴昊洋的耳根边吹些于他不利的枕头风,搞得朴昊洋与他不和睦。以后自己的事情,朴昊洋就有可能撒手不管,不闻不问。
刘蓉娜的那个玉门窑儿,自己和朴昊洋都接触过,多少有些留恋。可是女人都鼠目寸光,又只顾眼前的实惠,常常口无遮拦,朴昊洋与她的那些破事儿,只怕早晚会被港都市的人们知晓。
“张总呀,朴副省长真的能当上代理省长吗?”
张强贵此时很心烦,心想你和朴昊洋也有一腿,经常在一起厮混,要说朴昊洋的升迁问题,你应该第一个知道,连你这个与朴昊洋最亲密的人都不知道,别人又怎么会知道啊?
但是,张强贵心里虽这么想,在口头上却没有说出来。
“蓉娜小姐,目前我也不知道,又不便给朴副省长打电话,只有等着。我估计朴副省长已经散会,稍后定会有消息。”
“张总啊,你知道消息后,要给我打个电话哟!”
“我知道消息后,马上给你打电话。”
“我相信你张总不会忘记的,拜拜!”
张强贵本也想说声“拜拜”,却没有说出口。他想这个女人如今不是自己的肉床单,而是朴昊洋玩弄的尤物,过于与她亲近,会使朴昊洋吃醋而反目成仇。与她保持一段距离才明智。
张强贵本不愿想这些烦心事儿,可刘蓉娜的影子又在他的脑子里根深蒂固了。那是很早以前,刘蓉娜才调电视台工作不久,张强贵的事业也才刚起步,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们邂逅了。
他们邂逅不久就好上了。但张强贵已经结婚,家里有娇妻和乖巧的儿子,刘蓉娜也就没有强求,只与张强贵做露水夫妻,求得一时的快乐。
张强贵想毕,又骂道:“刘蓉娜,你个骚婊子!”
他刚骂完,手机又响了。
张强贵对手机的蓝屏瞟了一眼,是朴昊洋的手机号码。
“强贵啊,我到花都的楼下了。”
“您好!我已经作了安排,您乘电梯上来,我在门口接您。”
张强贵仍没说“朴副省长”,在情况不明的特殊时间里,不直呼朴昊洋的官衔才明智。倘若朴昊洋当上了代理省长,依然叫他“副省长”,他心里头舒服吗?谁都有个虚荣心。换位思考,无论谁都虚荣作祟,神仙也难免。如果朴昊洋没当上代理省长,却叫他“省长”,说不定会被他误认为是嘲弄,我们多年的哥们儿关系可能就毁于一旦,以后就别再指望他办事儿了。这年头的人就是这个样子,相互利用,各求所需。
张强贵挂机后,开门出去了。
他平常自己很少开门,若要出去,便按个键,立马就有侍卫生闪进来,鞍前马后地忙碌着。
今天他却一反常态。
花都大酒店48楼的走廊里,铺着一寸多厚的猩红地毯,脚感舒适,像踩在薄薄的雪地上的那种感觉,轻飘飘的。
在走廊里值班的侍卫生,平常没事做,可坐在专用的沙发上小憩。这层楼的侍卫生,只为张强贵一个人服务,只要张强贵没有朋友来或不走出办公室,侍卫生就无所事事,站着也是和自己的腿过不去,只有傻瓜白痴才会久久地站着。
但是,如果电梯房的指示灯亮了,抑或张强贵办公室门上方的指示灯忽闪着,侍卫生就如临大敌,闪电般地站起来。
很早以前,有个侍卫生坐着小憩,被张强贵撞个正着,结果被炒了鱿鱼。朴昊洋知道这个情况后,把张强贵责怪了一顿,说你强贵显摆也要分个场合,常换新面孔,对我和蓉娜来这里多不方便。
张强贵想想也在理,被炒鱿鱼的那些侍卫生心里一定有气,对朴昊洋和刘蓉娜来这里的情况,就会胡说八道。
自此以后,他就放宽了限制。
张强贵走出会客室,径直来到电梯房的门口。
他对电梯房的指示灯瞟了一眼,见指示灯的上升箭头飞快地变换着,知道朴昊洋快到48楼了。便对常在会客室里忙碌的那个侍卫生瞅了一眼,努努嘴,示意他进会客室去张罗,做好招待准备。那个男侍卫生扭转身,向会客室走去了。
张强贵提了一下裤腰带,然后双手的五指张开,从两边太阳穴往后拢了拢头发,又将西装衣领整理了一下,这才聚精会神地盯着电梯门。指示灯的上升箭头终于定格了。
只听“咝”的一声响,电梯门开了。
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走了出来。在他的身后,电梯门又“咝”的一声闭合,随即降下去了。
这个中年人就是朴昊洋。他神情有些沮丧,与以往判若两人。他的准确年龄是四十七岁,由于保养得好,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四五岁。国字形的脸上,红润泛光。
张强贵见朴昊洋灰心丧气的样子,顿时没有了主见,也不知如何招呼为好。见朴昊洋径直向自己的会客室走去,便跟在他的屁股后头默默地走着。
在他们的脚下,柔软的猩红地毯,一起一伏。
朴昊洋走进张强贵的会客室,在左边褐色真皮的沙发上坐了下来,将一个纯白色绣着鱼儿花纹的背垫塞在背后靠着。
然后,他的双腿成小八字形摆开,左手臂靠在沙发的扶手上,右手搭在一个蓝色的背垫上,神态肃穆,俨然一副名公巨卿的派头。他不管是在会场,还是在办公室,都是这副姿态。
男侍卫生马上将“雪鸟牌”极品烟,给朴昊洋敬上一支,并打燃火机给朴昊洋嘴里的烟点燃火。接着,便把朴昊洋来这里专用而且已沏好的铁观音茶端来,放在他面前的茶几上。
随后,男侍卫生才给张强贵端来已沏好铁观音的专用茶杯。
以前,张强贵对在会客室服务的男侍卫生反复嘱咐过,说沏茶敬烟,客先主后,对客人要恭而有礼,不要乱了章法。
男侍卫生忙乎完毕,知趣地走出去了。
张强贵的贴身侍卫生都清楚,来会客室的人物非同一般,老总他们有要紧事相商,待在会客室里会影响他们说话。所以,谁也不清楚他们老总的事情。
朴昊洋见侍卫生已走,便说:“强贵啊,那事没成。”
张强贵虽然事先有心理准备,但得知这个真实情况后,心里顿时像打破了五味瓶,那滋味说不出地难受。没想到斜叼在嘴里那支烟的烟灰,没来得及弹到烟灰缸里去,掉落到大腿的西裤上了。
他回过神来,赶忙站起身轻提裤子,掸掉落到西裤上的烟灰。
“谁当上了代理省长?”
“省委副书记米盛庆。谁也没想到会提拔他当代理省长。”
张强贵暗吃一惊,因为他很了解米盛庆的个性。当初,张强贵的商场刚起步,与对手竞争激烈,为把业务揽到手,便雇请黑道上的朋友,把对手打成了残疾。后来,对手经常上访。那时候,米盛庆当政法委书记,追查案子很紧,非要查到幕后的黑手不可。因此,张强贵被查出来判了几年有期徒刑。
张强贵叹了一口长气。往事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这是怎么回事呢?米盛庆没有过硬的背景啊?”
“米盛庆被提拔起来,我想一定与巡视组有关。”
“巡视组,什么巡视组?我从没听您说起过?”
“巡视组是由中纪委、中组部联合组成的。成员都是部级岗位退线的领导干部。省级领导都由他们监督着。”
“按您这么说,巡视组掌管着生杀大权?”
“巡视组的职权只是了解情况,没有办案子的权力。但是,省级领导一般被提拔上去,绝大多数是由巡视组推荐的。”
“朴副省长,既然是这样,巡视组当初在港都市巡视的时候,您为什么不告诉我?我要知道是这样,肯定会摆平他们!”
“强贵啊,你以为你的能力能通天哪?那是些什么人,即使你强贵给他们送座金山,人家也不会要,他们不会在这时候犯错误,毁掉一生的清白!”
张强贵很不自然地笑了一下,刚才因心情激动只顾说话,忘记了手中的烟,这时候想借吸烟来掩饰尴尬,孰料手中的极品烟已经燃完。无奈,他只有再点燃一支吸着。
“朴副省长,代理省长是不是真没办法挽回了?”
“没辙了。今天已经宣布,再没有回天之术了。”
“如果米盛庆有重大的腐败问题,他还能当代理省长?”
“强贵啊,米盛庆腐败要有证据,空口说白话没用!”
“朴副省长,米盛庆腐败,我有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