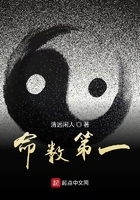易琛面上带着让人心怡的微笑,一副丝毫不抵抗的态度,却在围着他的雇佣兵想要靠近时面露痛苦之色,惨白的额头上冷汗淋漓,唬得他们连退几步,生怕莫名摊上一个伤人的罪名。
没办法,虽然在战乱区他们可以横行霸道,但到了和平地带,却必须得遵守该地的公民法则。也许这个法则执行起来会比一般人宽松点儿,却不会宽泛太多。
“他没有急性病症。”
这是看不下去的冯盈开了口。她冷冷盯着易琛逼真至极的表演,眼底神色越发冷凝。
她这些年从没放弃过搜集易琛一家的私人信息,这一点还是能保证的。
易宛秋闻声暗自吃惊,若是表演,未免太过逼真。但冯盈如此胸有成竹,不可能是说谎……
心随念转,她微微皱眉,不解地盯着易琛没有一丝血色的面颊。
因不知真假的痛楚额角跳起了根根青筋,大颗大颗的冷汗顺着额头一路蜿蜒至白净的下颌,就连那清澈透底的眼睛内含着难言的惊恐,毫不作伪。
怎么看都是个饱受病痛煎熬的弱气书生。
不禁让人无论如何也想不透为什么他会是那个心思狠极的幕后之人。
得了冯盈的准话,雇佣兵们无所顾忌地将易琛也送了出去,为了保险起见,还特地拨打了急诊热线将他送上了救护车。
徒留下易宛秋还在穷极无聊地思索着面相与心地之间的联系,在将身边人都扒拉完一通后,她终于满意地得出了结论——两者毫无关联。
冯盈看着她不知忧愁的神色轻轻叹了口气,这一个星期以来,除了最开始的那封情书,余禹竟是一点动静都无——这与他一贯的风格相去甚远。
易疏那边也没有什么进展,倒是苏笙曼和胡扬联起了手,使得他在公司的处境越发岌岌可危了。
……罢了,尽量不惊动她,把这件事处理干净吧。
沉沉的暮色透过窗台浸进来,显然已近黄昏。
冯盈敛去翻腾不休的思绪,对着精神不济的易宛秋放柔了嗓音:“打了一天的瞌睡了——你去睡吧。”
听到这句话,易宛秋缓缓回神,恍惚地意识到又有一个无趣的白天即将过去,而她竟然已经度过了如此之久没有自由的日子!
本想慷慨激昂地抗争冯盈的独-裁主义,却没料到现实的万般残酷——睡意忽然漫天而来,莫说渐变懒惰的思维,眼皮也快支不起了。
“嗯……”
只在心底定下明天一定要踏出大门的宏愿,易宛秋含糊应一声,一路强撑着回到二楼的房间,扑在榻上一睡不起。
轻飘飘的思绪如同泡在棉花糖里,又软又绵,直让人昏昏沉沉、颠颠倒倒。
等易宛秋慵懒地睁开眼睛时,她觉得自己肯定是在做梦,不然眼前如此熟悉的场景作何解释呢?
倾城日光娴静而温婉地凝望着她,象牙白的古罗马柱齐整地矗立两旁,幽静的湖面漾着浅金色的粼粼波光,将易宛秋纤袅的身形映得明净如诗。
穿着白纱的妇人赤足自古堡里奔出,一脸焦急地呼唤:“少爷,小姐,你们在哪儿呢?”
这是一幕极其灵异的场景,她自然而然地无视了咫尺之遥的易宛秋,顾自用手做喇叭状四处探寻。
思绪随之混沌些许,易宛秋眨了眨眼,近乎怀念地盯着妇人黝黑的面庞,在原地顿了刹那,举步跟上她行迹匆匆的身影。
穿过一处芭蕉林,再越过一片椰子树,妇人终于在一处清澈的浅滩前停下了步伐。
紧随其后的易宛秋凝眸望去,一男一女两个小孩正俯下身子挑挑拣拣地从溪水里捡石子,捡起一颗新的便丢下一颗旧的,兀自玩得不亦乐乎。
“阿姨?”
注意到这边的动静,小女孩回过头来,照例无视了易宛秋,只仰着一张精致的巴掌脸看向黑面妇人。
“唉哟,你们这两个小祖宗可让阿姨一顿好找。”说着,妇人明显长松了一口气,“我烤好了黄油面包,就等着你们呢。”
小女孩双眼一亮,回身扯着那小男孩的袖摆,趾高气昂地命令道:“阿姨做好吃的了,我们回去。”见小男孩有些不乐意地嘟着嘴,她哼了一声,“钟晴,老头子不是说了吗——‘客随主便’!这是我家,你得听我的。”
小男孩生气地甩开她的拉扯,低声说了一句消失在热风的话。
在这副画面里,小女孩同样生气的面容和妇人无奈又纵容的神色都很清晰,唯有小男孩的音容极端模糊。
易宛秋不禁靠近一步,想看得更仔细,却见那个小男孩忽然抬起头来直直望向她的眼睛,咧嘴一笑,洁白的牙齿反射着日光格外闪亮。
怔了一秒,易宛秋蓦然发现浅滩上所有的小石子忽然如同聚光灯一样发出闪耀的光芒,齐齐悬空漂浮,密密麻麻地朝她扑将过来。
怎么会这样?!
思维空前地清醒,易宛秋又惊又惧地僵立,漆黑的眼珠一动也不动。
“唔……”
冷汗淋淋地直起身,易宛秋的思绪还停留在发着光的小石头将她活埋的那一刻。突然,放在枕头边的手机发出“呜呜”震动,她平复了有些急促的呼吸,五指四处摸索着捞起一看,发现是一条来自备注为【黑历史君】的短信。
“下楼,我在你家。[笑脸]”
看清短信内容的一瞬间,一阵潮水般的晕眩蜂拥而来,直扑得岸上的易宛秋摇摇欲坠,一时竟分不清究竟是被石子砸死来得痛快,还是再次与那位客人面对面来得凄惨。
——要是有什么魔法能够召来一场大风,将他吹回大西洋彼岸就好了!
虽然不切实际,但这的确是易宛秋此时唯一的愿望。
“有礼物,快下来。”
几乎只隔数秒,又来了这样一条短信。
易宛秋懒懒瞥一眼,不做理会地磨着牙。不大会儿,屏幕忽又亮起。
“再晚礼物就被鲨鱼啃了,不骗你。”
……当她是猪呢?
不知道诱拐别人的时候谎话得编圆一点吗?
不屑地从鼻腔里喷出一口气,易宛秋头疼至极地听着手机不断发出的呜鸣声。
她真的不想下去——就算继续闷在家里也比面对活生生的黑历史好呀!
这么残忍的事……
犹豫了又犹豫,拖拉了又拖拉,易宛秋终是在短信的连环夺命催之下拾掇好自己,不怎么情愿地打开房门,步下楼梯。
未及看清人影,冯盈难得爽脆的笑声就如清风飘入易宛秋的耳际。
就知道会这样……某些人就是靠一张嘴行遍天下。
一个白眼还没翻完,她果然听到了那小子满嘴跑火车的夸赞:“姐你别笑,要是我们俩一起走在街上,保准其他人都觉得咱们是一对姐弟呢。”
冯盈被哄得眉开眼笑,眼角细密的纹路都舒展开了,“你呀,真会说话。”
虽然不是第一次听到这类夸赞,但只有面前这小子的神情让她觉得最真诚、最贴心。
要不要每次来都把她的亲妈哄得对他俯首帖耳、言听计从?
再这样下去她都能预料到自己失宠的一天了!
危机感大盛的易宛秋小跑着冲上前挤进两人中间坐下,充满敌意地看着钟晴。“钟晴,你怎么来了?不是忙得很吗?”
钟晴的五官很深邃,立体至极,尤其是一双亮若点漆的黑眼睛,一眼望去就如同无垠的星空,亘古冰冷,无端给人以强烈的窒息感。但当他笑起来,这种极端锋锐的侵-略感就被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毫无压迫感的柔和之意。
此时他就在笑,笑得意味深长,又孩子气十足。
“我是来办公事的——奶奶准备在z国加大市场,所以先派我来打前锋。如果情况符合预期,就干脆驻扎在首都。”
听了这话,易宛秋石化了,表情僵硬,怔怔重复道:“驻扎在首都?”
钟晴是钻石钟家的继承人她是知道的,但钟家的大本营不是一直在欧洲吗?
“对呀,至少接下来的两年内我都不会离开z国,说不定我还会在y市开一家分公司呢。所以你又丢手机也没事——反正我可以随时来看你嘛。”
看到钟晴得意的神情,易宛秋几乎都能把他那句话自动翻译过来——“你别想摆脱我,我跟定你啦……”
霎时只觉天也昏地也暗,前途黯淡无光。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很多时候,青梅与竹马之间并不像《长干行》所描述的那样两小无猜,反倒是一种你嫌弃我、我也嫌弃你的互相瞧不顺眼。
易宛秋和钟晴两人就是如此。
对于她来说,钟晴从来不代表着什么值得追念的美好时光,而是一份不折不扣的黑历史。
伤心得哭鼻子却哭出了鼻泡反被笑话,换牙期间的漏风嘴,想撒谎却被骗时候的傻样子……这类数不胜数的糗事不仅加重了她对钟晴的嫌弃,还让她对与钟晴有关的东西避之不及。所以她尝试了无数种方式与钟晴断绝联系,丢手机、丢邮箱、丢企鹅号……但很可惜,最成功的一回也只维持了三个月。在她刚刚舒一口气的时候,钟晴总能阴魂不散地复又出现,让她的满腔成就感都化作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