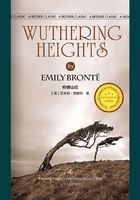电光火石之后,老齐被绊倒,球已经缓缓滚出了底线。
我和老齐同时看裁判,裁判没做判罚。我和他又抬头看大屏幕的回放——屏幕上清楚地记录着,在齐达内被放倒的前一个瞬间,袁夙的脚尖先碰到了皮球。
我没有犯规。
我颓然倒地,听见自己重重的呼吸。我赢了齐达内,赢了老范……赢了……
我甚至没有听见完场哨。用一颗麻木游离的心去感受欢腾的球场,是不是即便人声鼎沸般狂热,也难抵冬夜的萧索?我瞪大眼睛望着看台一角,不知怎么眼底就蓄了一层雾气。
然后我看见老齐站在不远处,带着赞许,授以微笑。我和齐达内交换球衣了。
“You played well. ”老齐操着一口不标准的法国腔英语说。
本有许多话想对这样一个英雄去讲,一时间,全然无措。老齐见我抿着嘴,不像是愿意搭言的样子,随即拍拍我肩膀,转身离去。
“Do you……”我最终还是开了口。
嗯?几步之外,齐达内回过身,一脸好奇地看着我。
“Do you feel happiness?” 我这样问道。
似乎谁也不会想到,那个比赛中大放异彩的小伙子,一脸忧伤地站在齐达内的身前,憋足了勇气,问了那样一个问题。他的语气是平和的,眼神却是期待的,就像在死寂的汪洋中期待一根草一盏灯。
齐达内先是一愣,随即笑了。那个一生中从未闹过绯闻,已经是四个孩子爸爸的国王,微笑着点头:“Yes,sure! ”
意料之中的回答,轻盈而厚重,如同落定的尘埃。
12月23日,到此结束。
飞机于24日中午抵达B城。周镁桐惊讶地看着我出现在邦泰大厦的12层,财务部的员工们纷纷起立鼓掌,为我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庆祝仪式,我方才知道周镁桐的部门昨晚集体放假,包下酒吧观看我的比赛。
十分钟之后,周镁桐的喜悦已经由袁夙的回归转移到那些个香港周生生的珠宝礼盒上。周镁桐乐滋滋地拉着索琳,逼着我一样样地将珠宝摆在大理石的办公桌上。
周镁桐问我挑选这些一共花了多长时间。我告诉她两个小时。
“咦——这是什么?赝品吧?”周镁桐拿起的是一条925银祖母绿吊坠。镶嵌其中的祖母绿宝石切割精美,是一条小鱼的形状,泛着细腻的鳞光。那的确是件赝品,是在香港的淘宝街上买到的,99港元。
周镁桐把玩了两下,不屑地放回到盒子里,那眼神告诉我:很没品。
我大大方方地对她说:“这个不是买给你的,是给索琳的。”然后我挤出一个很官方的微笑,“索琳,这次时间匆忙,没有时间带什么像样的礼物。这条吊坠……希望你能喜欢。”那两个小时,一半花在周生生,一半花在淘宝街。或许真的很没品,但那的确是我能淘到的最好看的饰品。绿宝石的银坠,让我一下子想起索琳,她白皙的脸上透出玉色的光。
索琳接过,抿唇道:“谢谢。”
周镁桐她们此刻正忙得不可开交,我稍作停留后便请辞离开。并且在出门的时候,对着“花开诱惑”有片刻的出神。
手机响起短信提示音。
周镁桐:夙夙,你才走了三天,怎么感觉像一个世纪?
周镁桐:夙夙我想要你。
周镁桐:我看见你笑得很疲倦,但是我一刻也等不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我回复了一条:办公时想这些问题,很容易出错吧周镁桐小姐?
周镁桐:我没在办公室,我在车里。
……
不言而喻。我在电梯间按下“-1”。
车内的暖风和周镁桐最喜欢的轻音乐混合在一起扑面而来。她正歪头看着我,眼神半明半媚,三分邪气的笑容在唇际流连。还是方才的装束:七公分的高跟鞋,白色的衬衫外是范思哲套装,笔挺的上衣,精致的一步裙——我知道,其中已经做了手脚——这方面的情趣周镁桐向来就不缺乏。
紧张局促中还夹杂着自己的意愿,使得这样一道快餐不到一刻钟便结束了。周镁桐还没有从方才的意境中脱离出来,胡乱地吻着我眉际的汗珠。她伏在我的胸口喃喃道:“夙夙,你不在的三个晚上我一直在做同一个梦,梦见你走丢了,不回来了。知道吗?小熊肚子里的硬币已经过半,我不敢再放,我怕终究会有一天,那里再也放不下一枚硬币。幸福会不会也是一个定数?就像我现在抱着你赖着你,这么贪心,会不会也有一天,突然就满了,再也存不下一点幸福?
“夙夙,我不要它白白溢出去,我要它永远都存不满。我们明天就去民政局吧!
“而现在,”她说,“我要带你去一个地方。”
周镁桐高兴地宣布全组再次放假一个下午。平安夜的当天得到宝贵的假期,员工无不欢呼。历恒看了一眼索琳,没有说话,继续埋头做事。索琳则少有地,发了长达三分钟的呆。
再次从楼上下来的桐桐已经换好了厚厚的羽绒服,精神焕发。整个人都变得轻盈。我问她去哪里,她只回答了两个字还愿。
说起来略显荒唐,这是周镁桐四年后第一次来龙云寺进香。这倒也无妨,滑稽的是,在西方上帝过生日的时刻,一贯西化的周镁桐竟然想起回拜东方的佛祖。
于是可以想象龙云寺的萧条,没有悠扬的钟磬,甚至就连香蜡祭纸的味道都被十二月苍凉的空气稀释得无影无踪。周镁桐扯着我的手,咯吱吱地踏着厚厚的庭霰残雪,兴致勃勃地沿着那些系满红绸的黄桷树一路寻来。
终于,她的眼睛一亮。眼前的一棵小黄桷树上,枯叶落尽,褐色的枝干张牙舞爪地伸向天空,在那枝干上挂着一颗醒目的红绸。风拂过,红绸迎风招展。周镁桐雀跃,一指上方:“那就是我许的愿!”
随后,周镁桐将“红绸为佳姻,墨守不解缘”的传说悉数讲给我听,说到神奇之处,声情并茂不能自已。
“夙夙,你也一并许个愿吧。很灵的。”
我笑着摇头:“你刚不是说过了么,‘遇诚则速,速达则灵’。我的心不诚,就算我许了愿,佛祖又怎么会显灵呢?”
“乱讲话!”周镁桐说,“这是姻缘,怎么会有不诚之人?饶是玩世不恭,心头也有一处最柔软的情结吧?夙夙,我喜欢你万事随意的处世态度,但是有些领域你随意不得。感情是踯躅必较的东西,如果你连这样的信仰都没有,那岂不是在亵渎你心里的那个人?”
我很奇怪的是,周镁桐说的不是“我”,而是“你心里的那个人”。我怔怔地看着她,直到她扑哧一笑:你的心不诚,我还嫁你做什么!遂扯着我的胳膊撒娇道:“夙夙也来求一支姻缘签嘛……”
龙云寺的庭院四野空旷,细细碎碎地传来冬鸟的鸣声,愈显幽静。而我心里却被一个沾染邪气的微笑卷起了烟尘。
周镁桐的声音忽远忽近:如果你连这样的信仰都没有……
真的连这样的信仰,都没有吗?
一刻钟之后,我将写好的姻缘签挂在枝头。红绸裹着的是一个名字。
周镁桐始终在寻找当年那位老僧的踪影,无奈未果,只得请了一些香,跪在佛祖身前,双手将香举至眉齐。闭着眼,面庞恬静如水。远处的两颗红绸随风而舞,热烈而纠结。
周镁桐一直向我吹嘘着姻缘签的神奇,并且告诉我她在四年前的姻缘签里许下四字之愿,如今所愿已达,喜形于色。我在旁侧耳倾听,偶尔插上一两句话,多数的时间里我低头微笑,用筷子拨开浮在汤上的辣子。
平安夜,皇城老妈人满为患,围着热气腾腾的火锅,桐桐还是习惯性向我靠来。好像我的胸口永远比火锅更暖。周镁桐高兴的时候喜欢喝酒,不醉不归。对于这个日本人才有的不良习惯我曾经颇为恼怒。但是今天,我非但没有阻拦,反而莫名地和她一起推杯换盏,直到二人的脸上都罩上一层潮红。
桐桐醉眼迷离,“袁夙,你千万别告诉我你写了我的名字,那样的话,姻缘签就不灵了。”
我也有了几分醉意,笑着点头,“我不告诉你就是了。”
周镁桐又喝醉了。一头扎在我的怀中,赖着不出来。惹得周围男女纷纷观望。我捧起她的脸,轻轻地吻向她的额际。生生地令众看客们把脸别了过去。
“夙夙,背我回家。”
我说:“好。”然后我在众目睽睽之下背起周镁桐,在吧台结了账,走下楼梯。
外面已经银装素裹,平安夜的雪花安静地飘落,街边的酒吧透出微微的烛光。浪漫的催化之下,情侣们偎依而行,这样的街景足以致醉。我将外衣脱下,披在桐桐的背上。她在我耳边絮絮地呓语:“夙夙今天好温柔,说,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
我歪着头笑笑,“别动,伏好,我背你回家。”
“一直背着我,不许把我放下来!”
我仍旧是笑,“一直背着你,不放。”
我甚至在路边买了一只米奇头像的氢气球,周镁桐一路扯着它,笑出了声。酒气和她嘴角特有的甜味混合在一起,喷在我的脸颊上。
路过一家珠宝店时周镁桐示意停下,闭着眼,一脸坏笑地央求我买给她一枚指环。随后的五分钟我用身上全部的三张钞票买了一枚298元的黄金指环。
“要戴上吗?”我问。
桐桐摇头,“到家之后,我要你亲自给我戴上!”
从皇城老妈到我们的住所,两公里远,我背着周镁桐走了一个小时。行至一半,周镁桐在我背上酣然睡去,我放慢脚步,因为怕扰醒她。或许,也因为我舍不得将她放下来。
再远的路,也有走完的一刻吧。
轻轻将她放在床上,周镁桐仍然熟睡,微微笑着,眉间一片化不开的柔和,只是手里紧紧攥着那枚指环,宛如至宝。费了好大劲展开她的手掌,取出了那枚再寒酸不过的指环。我并没将它戴于周镁桐的手指,而是轻轻放在梳妆台的琉璃台面上。再细小的指环也终归是黄金打造,寓意永恒。有一个瞬间,那指环借着窗外直摇而上的烟花发出璀璨光亮,灼到了我的眼睛。
烟花在教堂上空淡淡引爆,圣诞的钟声敲响,午夜到了。我定定地看着烟花绚烂开放,稍纵即逝,连下一秒都是奢求。桐桐,我以为下一秒种,下一个场景就会爱上你,如今,时空已从无上的君王沦为内心的奴隶,而我,终究没有等到那个时刻。
也许她说得是对的——我不配拥有那样的理智。
当然,我也不配拥有理智支配下的幸福。
烟花散尽,我站在楼口,夜空下安静得如闻夏虫冰语。
“去哪?”一辆计程车停下,司机探出头,声线飘在我身前的空气中。
我回过神,缓缓地吐出四个清晰的字:“花开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