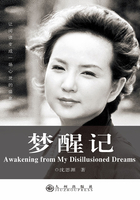一九九四年九月十二日,那是一个晴朗宜人的早晨。像往日一样,军营里响着振奋激昂的军歌:“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战士们排着整齐的长队,在连长的口令下有节奏地跑步,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我要去火车东站发整车的化工原料。
我穿上了那件合体的纱质优良纯白色短袖上衣,配上深蓝色纱裙,把一头乌黑的秀发扎起来,与我开朗的性格相得益彰。
洗漱完毕略施粉黛,清爽的淡妆看起来清新可人,修长的双腿加上皮鞋的高度,身材高挑,看着镜中的自己楚楚动人,我对着镜中的她微微一笑。很多年后,我仍然清晰的记得那个笑,像阳光下绽放的花儿那样绚丽,但是我永远不会想到这美丽的一刻,会成为我美好人生最后的纪念。
九月的气候,像孩子幼嫩的小手抚摸着母亲的双颊温柔而甜美,微风轻轻吹拂着我的脸庞,柔软的纱裙在风中微微飘摆。
那笑容始终挂在脸上,我取出深紫色的女式单车,双手扶把,昂首挺胸,好像我拥有了整个世界。是的,此时的我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我拥有了所有的美好,我真诚的感谢上苍对我如此厚爱:给了我一双可爱聪慧的儿女,给了我称心如意的爱人,让我成为这蓝天下最幸福最快乐的人。
马路上行人络绎不绝,车辆熙熙攘攘,如潮水般向军区体育馆方向拥来。兰州公交七路车和四路公交车相向驶过,就在这时,七路公交车摆着长龙似的车尾向马路牙子这边冲来,像发了狂一般,路边一个男士自行车被撞,跌跌撞撞地撞到我的自行车上。我的身体顿时轻的犹如一朵飘浮的流云,鬼使神差地从自行车滑下,向车体的腹部飘去,我的身体被卷进了公交车的底盘。
瞬间的改变,让我脑海一片空白。一切都在刹那间消失,一切都变的模糊不清,四周的一切都染上黑色的斑点在空中浮动,我好像进入了一条黑漆漆的隧道,那是死亡的方向,把我脆弱的不堪一击的身体无情的吞没,我在迷蒙中开始朝着死神所指引的方向下沉…‥
“快!快!不要堵塞交通!先把人拖出来!”
一双男人强有力的手,不知拉着我身体的哪一个部位,用力把我的身体拉出了车身。
我的意识慢慢苏醒,一阵剧烈的疼痛,感到呼吸困难泪水和额头渗出的汗混合在一起,挂在苍白的脸上。
旁边围观者说:“这个人脸色很差,恐怕完了。”又是那一双强有力的手,拉扯着我的双腿。怎么没有任何感觉?我看见他拉着我的双腿。但是腿好像离开了我的身体,我的知觉完全消失了。不祥的预感使我极度恐惧,下意识我问自己:难道我的脊柱损伤了?我的中枢神经断了?我要瘫痪了吗?二十六年医院工作的经验告诉我两个可怕的字眼:截瘫!
我恐惧地望着那一双男人的大手。声撕力竭的低吼,“不要拉我!不要拉我!冥冥之中,好像有几个人还有那一双男人的手。把我的身体拽起来。七手八脚的塞进一辆黄色的出租车内…‥
也许我就要死去,到我该去的地方。车辆颠簸让我又一次睁开无力的双眼时,我看见自己像一条蠕虫一般蜷曲在狭小的后座上。懵懵懂懂中,那几个人又把我从车内拉扯出来,把我平放在医院走廊过道的一条供病人休息的长椅上。
“药房”两个醒目的大字映入我的眼帘,看着男男女女老老小小的人在我的身边走过来走过去,像织布机上的梭子忙碌地穿梭。世界为什么突然会变得如此惨淡,我像大漠里的一粒飞沙,不知飞向何处。我的心此刻犹如坠入了十八层地狱,恐惧、悲哀、孤独、无助!
我对身边那个男人微弱地央求:“请给我的同事发个传呼,通知他们我现在的位置。”
此刻,不断加剧的疼痛猛烈地向我袭来。豆大的汗珠顺着发根如涓涓溪流汇入衣领,呼吸越来越急促。极度的寒冷使我的全身不断地颤抖。我似乎感觉到血压在持续地下降,几乎要降到冰点了,很快我就要休克,我就要死了。我生命要结束了,还在绽放的生命猝然凋零了。愤怒和不舍攫住了我的意识。
我不要死!我不要死!我要活下去!一个强烈的求生信号在我的胸腔里轰鸣:救救我,救救我——这几声微弱的哀鸣,像一只受伤的孤燕,在濒死之前悲鸣。我的双眼合上了,我想也许它永远不再睁开。
“谢姐!谢姐!你醒醒!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畔喊着。我努力睁开双眼,看见小华、小建、小明还有单位与我对面办公桌的同事,部门经理。
我费力地用很低的声音对他们说:“赶快找医生救我,否则,我就要失去抢救的机会,我不想死!”我又一次发出那凄凉、悲怆地求救,我紧紧握着小建的手,仿佛那是救命的稻草,我像水中的浮萍,命运的浪潮就要将我裹挟着走向死亡,可是那该死的卑微的求生的欲望却让我孱弱的意识片刻不宁,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渴望活着。
“谢姐!你要镇静。你感觉怎么样?”小建握着我的手,焦灼的看着我痛苦的面容。这时,一个穿着医院的工作服的年轻医生,在小明的指引下走过来,用医生特有的职业口气说:“把她抬进骨科病房,先放到治疗床上。”那语气冰冷而凌厉,像是发号施令的指挥官,朋友们按照他的意思将我抬进病房,可是他却交班去了,我绝望的望着门口,就算是宣布死亡也好。我的眼睛一眨不眨的注视着,我在等待,等待生命的奇迹。
不知过了多久,这段时间漫长的就像我等了一个世纪,医生终于来到床前,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金属器。护士用剪刀剪取我的内衣,用那冰硬的器械在我的胸部上划来划去,询问我的感觉。
“这里有没有感觉?”
“没有。”
“这里呢?”
“也没有。”
“截面还挺高?”
我绝望的摇了摇头,泪水已在脸上肆虐,顺着脖颈留下来,绵延不绝。
我什么感觉都没有,心一点点冷却,一个可怕的信号在我的头脑萦绕:我的脊柱可能有了麻烦,我可能要瘫痪了。
医生初诊后要求立即到CT室拍片。几个朋友商议,为了在搬动中不给我增添痛苦,小华提议把我和床整体抬起,直接去CT室。他们各自紧紧抓住治疗床的每一条支架,憋足了全身的气力。小华喊着口令,一二三,呼拉一声响。把治疗床平稳地抬在他们结实的肩上,前面一人不断地喊着:“借光!闪开!”
我被抬到半空中,因发冷而颤抖的身体如筛子般摇摆不停。我不知道自己的体重连同铁制的治疗床加起来总共有多少重量,但他们竟然走的那样稳健。
在危难的时刻,他们的真诚,好像在我的心里注射了一针强有力的稳定剂。拍完CT后,我的心里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执意要到我曾经战斗生活过的解放军第一医院。那里是我工作了二十六年的地方,也许身处难中,可想而知就想到“娘家,这个想法使我迫切要求转院,回到刚刚转业的原单位。
在我执意要求下,朋友们以分秒必争的速度找来救护车。
车启动了。我忍不住剧烈的疼痛喊叫,朋友们用手牢牢抓住平车让它悬空,以此来减轻我的苦痛。我出意外的消息不胫而走,在这熟悉的医院相识或不相识的人都在议论着:理疗科那个刚刚转业的谢技师遇到了车祸,撞得太惨了,可能不行了。而这一些与我又有什么关联,我只知道我回家了,我熟悉的地方,只是此去多年今非昔比,这惨淡的光景让我绝望到想与这个世界陌路。
此刻,我躺在明亮的病房,一种到家的亲切感似乎让不安的心里踏实了许多,我情不自禁流下两行泪水,泪眼朦胧中我看到房间里挤满了人,门口拥挤着不少探视的同事踮着脚,焦急地观望着。
主任与随后的几位医生很快来到病床前,仔细认真地给我检查,询问我当时受伤的经过。
我看着主任严肃的面孔,预感到我的伤情已经到了不可治疗的地步,还有危及生命的可能,但无论如何到家的感觉让我忐忑不安的心安定了下来,一切都顺其自然吧。
我听到他们在交换意见,马上紧急会诊,准备手术方案。
大妹得知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冲进了病房,哭得如同泪人:“姐!姐!你怎么了!你一定要振作!”
时隔不久,朋友都相继赶到,大家的神情都很沮丧。我不知晓,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他们是怎么得知这个消息的,但是他们的到来给我莫名的力量。
我睁着一双失神的眼睛想着幸福和快乐已经永远不属于我了,大颗的泪珠就像断了线的珠子滚落下来。
心爱的女儿依偎在我的身旁,脸上挂着泪不断地喊:“妈妈!妈妈!你怎么了!你看看我,我是你的宝贝女儿。”
我忍着剧痛,安慰着心爱的女儿,“不要怕,妈妈不会离开你的,妈妈永远爱你,现在你爸出差不知到了什么地方,单位通知他了没有,妈妈现在是多么盼望他能在我的身边。”
“爸爸的单位已经电话通知了,爸爸很快就能回来了。”儿子说,“妈,你有什么吩咐就对我说,我是家里的男子汉,刚才护士长说,怕长时间压迫发生褥疮。叫我们尽快想办法买些糜子。一会我和叔叔去花鸟市场买。现在大家都在主任办公室,讨论你的手术方案,还要爷爷签字。”
我说:“你去瞧瞧他们是否讨论完了,叫叔叔到我这儿来,我有话问他。”
过了一刻钟,同事来到我的床旁,不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安慰我。
“请你告诉我,我的伤情到底到了什么程度,你实话实说,不要隐瞒!”
“你别着急,也别太担心,你现在在医院。一定要听医生的话,你不会有生命危险,明天早晨,由主任亲自给你手术,你的情况会一天天好起来。”听他一字一句掷地有声的回答,我的眼泪又流了下来。不管他说的真实性有多少,即使是善意隐瞒也能让我平静下来,因为此刻我是多么需要安慰。
日后我才得知当时在讨论手术方案时曾怀疑到我的骨质可能有什么病变或是骨质疏松症。为什么碰撞会导致这么严重的后果,胸6、7、8、压缩性、粉碎性骨折。第二天的手术,要考虑到各种情况的发生及抢救措施,当时我的亲人的心都悬到半空中。但同事当时的一番话,让我感觉到这场灾难只是暂时的。在不久的将来终会云开雾散,欢乐和笑声还会伴随着我,我相信他的话,因为他是诚实可靠的人,他为了我忙碌了一天,他那善解言语,给我增添了勇气和力量。
人们陆续离去,病房处于安静状态,唯有心爱的女儿疲倦地爬在床沿上睡着了。
我凄然望着房间的一切。窗外的夜色很浓,繁星挂在天上闪烁着,一切都是那么自然、美好,但我胸部的疼痛好似一条毒蛇吐着鲜红的信子猛烈地吸食我的血液。此时,我虽然非常疲惫,但没有丝毫睡意,紊乱的思绪理不出个头绪,明天的手术是否能顺利成功。如果手术中发生不测,那么这将是我和我的宝贝相处的最后一个夜晚。
润,我的爱人。你在哪里,你快点回来吧。明天我就要手术。我多么希望能看到你,多么需要你的抚慰。想到此,难以抑制的疼痛又一次袭上我的心头,我清晰的感受到了生死别离的痛苦,刀割般的痛苦啊!
不!我一定要挺过去,就是火山我也要爬过去,强烈的求生欲给我坚持的力量。熬过明天,就是希望,虽然此刻我的面前漆黑一团,但我相信光明和希望就在不远的地方,也许熬过了明天,我的伤势就会有一个转机。
擦干眼泪,坚强些!
女儿趴在床沿憨睡,我心疼地看着女儿,心底掀起狂澜:无论如何,我也要渡过这道难关。我要储备所有的精力和心力,接受明天最严峻的生死考验。
第二天早晨,决定我生死,决定我后半生的日子到了。我被抬上手术室的平车。
一种难以形容的恐惧,向我袭来,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呐喊,亲爱的润,心爱的女儿,如果我有什么不测,你们一定要坚强的生活下去,我爱你们!我永远的爱着你们。
心爱的女儿紧紧拉着平车,拼命阻挡平车的行进速度,仿佛手术室的这短短几步就要成为她与母亲最后的诀别。女儿在声嘶力竭地哭喊:“妈妈!妈妈!你要好好的回来!”那一刻我的心碎了,我多想握着她的手,告诉她,“妈妈爱你!为了你们我一定要回来。”痛楚哽住了命运的咽喉,我一言不发,只在心里默默发誓,我要平安回来。
我的手术是由骨科主任主刀,还有全院最优秀的麻醉师。术前气氛十分紧张,麻醉师走到我的面前幽默地说:“别紧张,有我这个老家伙在场,一切都会顺利的。”他的一句话,似乎缓和了我紧张的情绪,到了这一步,怕有何用,生死有命,能把生命托付给这些熟悉的脸庞,给我的也是一种心安。“老天,保佑我吧!”我在心里默念。
我爬在手术床上,插上气管导管,手背上输着液体,胳膊扎着血压带,身上带着导尿管,总之一切都准备就绪。随着麻醉不断的加强,我的意识越来越模糊,渐渐的脑海里一片空白,也许这就是另一个世界。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当我睁开双眼,我已经躺在明亮的病房里,看到亲人焦急企盼的面容,这种感觉太新奇了:我的灵魂在阴曹地府里走了一遭又回转到充满阳光的人间,窗外的阳光洒在医院白色的被子上,跳跃着,就像我的心跳,明快而充满活力。这是一种死而复生的感觉,让我听到女儿在呼喊妈妈,妹妹在呼唤姐姐。
现在,我坚信我的生命不会终止,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在我的生命里装着满满的爱,我割舍不了我的亲人孩子,还有我日夜想念牵挂的爱人。
我心中的爱人一路疲惫,风尘仆仆,怀着不安的心情直奔医院骨科病房。我们四目相对,此时此刻,满腹的委屈,心里的酸楚犹如倾盆大雨瓢泼而至,泪水如决堤的江水一泻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