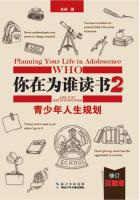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日
注:
这是陈毅为《新四军军歌》所拟歌词初稿。1939年2月,周恩来到新四军军部视察期间,众将士热情建议写一首军歌,并要求陈毅写歌词。初稿写成后,在叶挺、项英主持下,组织力量推敲修改。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以及军部秘书长李一氓、军政治部宣传部长朱镜我、政治部秘书长黄诚等都提出了意见。经集体修改后,改定的《新四军军歌》歌词与这篇初稿一起在1939年5月14日出版的《抗敌》杂志第一卷第三号上发表。发表时,编者注中说:“这原是陈毅同志为《新四军军歌》作的初稿,后来,军歌经过一次集体的改作,仅在第一节上还留下多少痕迹,但原作诗意洋溢,改题《十年》,一并发表。”歌词则署名集体创作,经音乐家何士德谱曲后,《新四军军歌》便立即飞遍了大江南。
附:《新四军军歌》歌词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
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孤军奋斗罗霄山上,
继承了先烈的殊勋。
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
千万里转战,穷山野营。
获得丰富的战争经验,
锻炼艰苦的牺牲精神。
为了社会幸福,为了民族生存,
一贯坚持我们的斗争!
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
东进,东进!
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扬子江头淮河之滨,
任我们纵横地驰骋;
深人敌后百战百胜,
汹涌着杀敌的呼声。
要英勇冲锋,歼灭敌寇,
要大声呐喊,唤起人民。
发扬革命的优良传统,
创造现代的革命新军。
为了社会幸福,为了民族生存,
巩固团结坚决的斗争!
抗战建国,高举独立自由的旗帜,
前进,前进!
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由宣城泛湖东下
陈毅
敬亭山下橹声柔,雨洒江天似梦游。
李谢诗魂今在否?湖光照破万年愁。
一九三九年
注:
这首诗是陈毅往来于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和茅山根据地之间,经宣城泛湖东下时所作。宣城,为泾县东邻县。
清晨
彭燕郊
每天清晨,
当太阳把金色的光芒交给大地,
夜雾就慢慢地向林子的后面退去,
初醒的原野就蠢动着万物的生的意欲了。
露水爱娇地在草叶的怀里跳跃着,
茅屋也发出了浓郁的稻草香,
我也总是那样、总是好像看到
大地是在慢慢地睁开它那惺忪的双眼,
是在慢慢地翻动它那硕大无比的
孕妇般肥壮的身子。
于是我更加急速地跑过田野,
我总是听到这些我常常听到的声音,
我已经和这些声音结下了不可解的缘分了:
栗子树上的知更雀总是那么热心地
叫着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春天来了,
农人们总是那样亲昵地呼唤着耕牛向田野走去,到市镇上去的乡民们总是兴冲冲地走着、
兴冲冲地谈论着各种各样有趣的新闻,
流水的淙淙的溅声和战马的笃笃的蹄声
也从来都没有问断过,
而在我的倾听里一点也不会迟误的
是我们那个跳上山坡的小号兵
从鼓起的双颊吹出来的
召集我们去晨操的火热的号音,
在鸟的歌、流水的歌、草木的歌、农人的歌、
战马的歌的
丰富而又和谐的合奏里,
立刻又加入了我们在操坪上发出的
“一、二二、三、四,一、二、三、四……”的叫喊声,
和那一步跟紧一步的
擦沙、擦沙、擦沙……的跑步声,
和那不时进发出来的
优秀的射击手的胜利的笑声……
——这是何等优美的
早晨的中国的赞歌呵!
春雷
彭燕郊
春雷驾着厉声的载重列车
从潮湿的云间
无阻隔地碾滚而过
——把天空
当大鼓敲捶
生命觉醒
土地蒸腾出强烈的气息
刺鼻的气息
浓郁的气息
原野
被各种各样的气味充满了
充满了牛蒡和酒糟的气味
染料和油漆的气味
酵菌和脓血的气味
头发和骨灰的气味
所有这许多气味
都被生命的热血所温暖
又被生命的急促呼吸所煽动
都这样
声音一般地颤抖着
向发出雷鸣的高空
竭力地呼喊着呵
阴云壅塞
大雨将临
好像有什么突然而来的打击
使大地突然地震颤了一下
于是,风呼啸
城市苍白着
村落低头
帆下降,锚落下
黄狗乱窜
蝴蝶折翅
鸟雀归巢
花落地,叶飘飞
门窗紧闭
烛火熄灭
电光闪闪
比十五六岁的少年的眼锋
还要锐利地
向烟尘、雨雾
翻卷在旋风里的乱草和败叶
横劈过来
一场空前的大变动在酝酿着
土地的氛围
畜棚般骚臭
人可以看出
土地
是怎样紧张地
咬着牙,切着齿
横着眉,皱着鼻
捏紧双拳
像一个满身浴汗的劳苦者
渴望着一瓢凉水从头顶淋下来一般
在等待着
大雨的降临呵
急速而又熟练地,像撕着破布
闪电腰斩了阴云
春雷扬起雨滴的尘埃
大地沉没在雨雾里
应亲热的召唤
而探首于大气之中的蛰虫
群队
换上了轻捷的新装
络绎于
欲雨的云天下——
抛掷着
阔大的脚步呵
望家 山
一献给我的故乡,家人
辛劳
落着雨,落着雨,
为了人世,天空是多么哀伤,
哭泣着用那不停的雨滴,
一点一点从松叶又流人小溪。
在这激响的小溪中,
流水翻着血红的浪。
在这不幸的村庄,
泡在血中,每个土粒,草梗;
哪里还有和平的风,
并不是因为这连绵的天雨,
野狗会告诉你,
在它暮夜的哀叫声里,
痛哭着流离失家的命运!
是灾难放开脚步,
是魔鬼的使徒;
比死亡还可怕的“皇军”的队伍。
刺刀闪着他们的荣耀,
用人的血染红的肩章,
在那死神的宠信的冠上,
那些大和民族的骑士,
桀骜地驰奔着马蹄。
枪口,枪口,冒着紫火,
怪蟒般的吐着毒舌。
带着死亡的呼号,
流星般的越过平野,
越过高高的山麓,
又从林梢头飞渡,
在这和平的村民头顶,
开放着不幸的鲜艳的花朵。
房屋同火神拉手,
那些房梁,和房瓦,
啸叫着,那火的鸡鸭;
像一片血色的虹霓,
朝夜,朝夜,装饰着天空。
这些日本强盗的拜访,
一个桃源般的村落,
就像蛇进了鸡窝!
山坡上的小草,
像昔日柔绿,像昔日茸茸;
但是,羊儿,
已煮熟在锅里,
在尖利的牙齿下,
做着人血渗合的酒肴。
山茶花,
正开得洁白。
芬芳犹握在,
赤身惨死的少女
那挣扎紧握的拳中。
山踯躅象征着她底命运,
被野鸟啄得凋零。
山鹰惊飞了,
落在山头,又飞起,
那愁惨的地面,它不敢停留;
那地面呵,
笼罩着愁云,
泛着血流……
天灾么?
蝗虫么?
雨点里夹着冰雹,
砸落了粗大的稻穗;
但,不是呵!
田里的稻穗低下,
却是因为盼想着粗壮的手臂
静谧的田园,
披上了看不见[的]丧衣;
哭泣,哀伤,是天上的雨;
谁还有欢笑?
欢笑的是日本强盗!
马蹄奔踏过水田;
坟山上冒着烽烟;
那些马扬首飞鬃,
嘲笑这居民的懦弱;
逞着骑者的傲慢,
摇着尾巴,饮着血,
在骷髅堆顶,嘶啸着天云!
不幸来了,
谁都要遇见:
今天,今晚,
谁知生死或者就是明天!?
追寻不幸的旅踪,
在每家茅草房里面,
若是暮夜有扣门声,
就有一幕悲剧:
假如你看见它底颜色,
那就告别了这人间!
在这横飞着死的村堡,
狗一咬,或风吹响了草叶,
小孩子立刻躲到床下;
年青的女人,
抹着煤烟,
想把脸抹成鬼样,
逃脱这怕人的污辱,灾难!
老人缩在草棚,
眼泪淋淋的望着天,
天是灰白的,
像他底心样愁惨!
“天爷哟!
你怎么就不睁睁眼?!”
成天杀戮着;
成天的叫喊!
那些意气飞扬的日本武士,
盘踞在这;
就仿佛到了他们的家园,
财产是祖先的遗留,
他浪子般的浪费着;
僻防着水,山溪般的流……
落着雨,落着雨,
死亡用雨丝来记数目。
落着雨,落着雨,
溪水涨着红潮;
所有的山石块都血肉模糊!
在山脊背,
长尾的喜鹊,不安的飞,
那黑老鸦彻夜的叫;
松鼠不再跳跃,
怕听见风里飘着号啕!
在高峭的山道,
一队队破烂的行列,
艰难地走,逃难的朋友;
背着孩子,背着破筐;
在油滑的草棵上,
跌扑着拄着蒿杖!
上山去呵!
逃到外乡……
哪里去呢?一片黑茫!
满腹愁怨离开乡土,
这祖宗流血,
用血喂得茁壮的地方!
现在盘踞着敌人,
那无人性的强梁!……
青绿得有点苍凉,
密列在山腰的松树。
夜问不敢出来,
那星星和月亮,
用暗云掩着脸,
从没见过人世这般凄怆!
小草心惊地摇曳:
金雀枝和常春藤叶:
黄金蛇不敢睡熟:
那许多悲哀的脚步,
践踏着山坡上的泥土。
刺果树秃了枝:
青草塞在口里;
谁见过这样贪婪;
疯狂的抢着,
谁抓多了,就眼含忌妒。
孩子哭咬着妈妈的干乳,
肚子瘪缩。快贴了脊背。
露宿在草丛;
林中遮不住雨水,寒风;
寒风吹着,仿佛铁蹄
高扬着,踢打着肌肤。
千年的古枫,
摇落红叶,为了愤怒;
夜虎不再呼啸,
为了雏虎。
竹叶响着,
那是哀叹的低歌!
愁惨的云朵,
不是无意的浓结;
金铃子哭着:
在这血色的大地,
哪还有明朗的温暖;
垂着头,那野生的铃兰!
没有一阵好风,
敢带起一颗泪珠吹过;
瀑布发着怒吼,
白练般的急流,
飞溅着驰进山窝。
躲在山头云里,
躲在古庙里的殿阶;
思想并且谈论:
不厌控诉——
谁能够沉默,
这天外飞来的灾祸!
“怎样啦,二弟!
你的老婆——
刚圆房,还没有满月,
而那新床……血……”
“咳,我的女儿!
十五岁的年纪:
也被……那天早上……
我的女儿……咳……
十五岁的年纪!”
“还有我的妈妈!
我的妈妈,五十六岁;
鬼子也是人么?
那样大的岁数,白发飘飞……”
“我的姐姐……”
“我的新生的牛犊……”
“我的白鹅……”
“我的谷地……”
“我的房舍,我的田地……”
“那些小猪哟……”
“天啊,还有我的羊啦……”
每个声音,
沉浸着血的泡沫,
篇篇血账……
落着雨,落着雨,
人们落着晶亮的泪珠!
“听听吧!
有耳朵的,有耳朵的,
你有耳朵的,听听吧!
牛在吼啦!
羊鸣伴着鬼子的狂笑;
人们的呻吟……”
有人在神座下,
呻吟,像溪水平静的时分,
又像亲人盖棺的一刹那——
“我的孩子……”
是一个年青的母亲;
她哀哀地哭诉:
“这些鬼子,这是人么?
孩子挑在刀尖上,
挥舞,盘旋,流着血肠……”
“怎样的夜里,
怎样的夜里……
呵,孩子没有死呵!
我去……”
一声尖叫,她疯狂地向雨中奔去!
人们全流下泪滴,
低下头——凄黑的夜,
凄黑的夜里,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嗷!”
尖叫声震荡着山林。
落着雨,落着雨,
天为着人们命运哭泣;
这些无家的愁苦的流民,
尖叫与哭泣,疯狂的雨。
有个老头,
他的白胡子飘来飘去;
泪不肯湿他底眼角,
因为那缠满的红丝;
他枯暗地望着天:
“有啥办法呀?
这是老天的意志!”
有一个老婆婆,
她底头顶全枯秃,
只有一个发髻垂在脑后;
她底嘴已逝去了年青的丰腴;
因为没有牙齿,
更因为她的独生子的奸死!
在人世还有多少呢,
荣华的希冀?!
有一个更为不幸的妇人,
她受过日本鬼子三次奸污;
在草坪,在河边的山石上,
在牛棚里的牛粪旁,
她曾晕死……
但,她活了,可诅咒的活呀!
庙中古旧的神牌,
冷默的就像尸骸。
妈妈拍着孩子,
一滴滴泪就落在孩子的脸呀!
那焦黄可怜的脸上;
秋天的草梗;
是被幸福所遗弃,
微微地,微微地呼吸……
落着雨,落着雨,
垂着头,就像旱天的禾穗,
低垂着枝干,没有生气——
这泥泞的悲惨的秋日,
忧愁流荡着,
又吹哭了庙外的风雨。
“不,我不愿意!”
有一个农夫,又是猎户,
也是这里的好汉;
若是谁没忘记他打虎的夜晚,
那夜晚睡在山上,
有一个猛虎蹿向他底叉尖,
那么容易,那虎就死在面前。
这故事,谁敢说不信,
他能把你从马上拉下,
无论你说完就跳上快马,
无论那马跑得多远,
并且骑者多么勇敢,
拉下马是一个强悍的青年!
若说。天空有个铁环,
他会拉着天,操纵着阴雨或晴天;
若说,地有个把手,
他会在春耕时候,
不用牛拖犁,
只手这么一翻,
就种上小麦和翠碧的油菜。
没有眼泪,因为羞愧,
更因为愤怒,他这般沉郁。
坐在神牌旁边,他思想:
破碎的家乡,
悲惨的草原……
“不,我不愿意!”
谁会忘记姊妹深仇?
谁愿意失掉家?
抛弃祖遗的田产?
谁愿意自己的猪羊
做成日本强盗的丰盛酒宴?
谁愿房子被敌人占?
谁也不愿挨饿在高山……
“不,我不愿意!”
愁惨的眼睛,
望着这打虎的儿男,
忧患把人们变呆了,
就像将熄灭的荒火,
只余微弱的火点;
他像风。他像火箭,
在那残烬堆上,
又慢慢煽起火焰!
“邻居们!
你们有没有胆量?
要报这血海的冤仇。
收复自己的家乡。
咱们自己来干!”
在这愁惨的人群中,
每个眼,被汨模糊的眼前,
泛上了血,泛上了火,
泛上了鬼子的马蹄,
泛上了锋利的刀尖……
“别看鬼子多凶,
我们是强大威风……”
“那飞机啦,
那枪火像赤练蛇……”
“去你的吧,飞机和枪火!
我们要看看,
铁斧子锋锐,
还是枪子的火?
还是镰刀尖利,
还是鬼子的大炮……”
“开过山石也开过瘠地,
多少麦子活在我们的手里;
想想吧,谷草垛怎样堆起?
茅屋是我们亲手盖造;
稻粒是我们自己捡起,
而且,这山上,你可曾看见过虎豹,
当雪夜,哪个畜牲能逃避?”
“对呵!你拿起你的弯刀;
你那松纹古剑也该磨利;
火叉子也是武器:
关刀要向敌人头上挥去!
扁担,竹杖……”
像风涛起在海上,
立刻就摇曳在暗默的空里。
“去啊!报仇去!”
呜呜哗啦!
呜呜哗啦!
落着雨,落着雨,
山岭上卷起粗暴的风,
反叛的雨点震响着大地!
就像夜里的山火,
蛇般地疾奔下山脊。
拉下马走在前面,
“去呵!报仇去!”
普罗密修士
偷来的火种,投在人问;
奔流和跳抖
一条燃烧的流岩!
四
落着雨,落着雨,
拉下马是一个火的引路者,
许多燃旺的火苗随在身后,
他又像一阵野风,
把荒火吹向乱草丛围。
他们悄悄地走近,
那“皇军”,醉了的守卫。
一声呼啸,
晴天的霹雳和棍棒齐飞;
从梦中,从酒杯里;
惊醒的鬼子兵,
顶上飞着血雨!
刀斧飞快地砍着,
没容敌人缓手,
枪还没有放响,
肩臂已竞连枪落了地。
机关枪被夺过来,
那射手带着梦里的微笑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