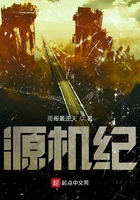过了一会儿,那位军医带着四名士兵抬着一副担架进来,洛伯林跟在后面。我从床上下来,整理了一下几乎要散成糨糊的大脑,对医生说:“你看我很好,可以自己走。”军医没拦我,示意两个士兵搀着我走出医务室,又把我扶上一辆救护车。救护车在两辆装甲车的护送下,把我送圆了分社驻地。这阵势不仅把曹卫圜和王雷吓了一跳,也让街坊邻居们吃惊不小。
两星期以后,我那几乎震散了的大脑,终于又紧密“团结”到了一起。其闯,德国军医每隔一天会来给我做一次检查。在洛伯林的一再要求下,分社没有对这一事件作任何报道。国际安全部队也再没有接受过其他媒体参与其夜间巡逻的请求。
全速闯雷区智斗塔剥班
在阿富汗有一处名胜是不能不看的,那就是巴米扬大佛的遗遮;也有一种“遗迹”是万万不可擅入的,那就是残留的雷区;还有一种“剩人”是最好不见的,那就是塔利班残匪。
然箍,2003年的11月初,记者赴巴米扬采访联合圜教科文组织的工作小组(该小组正对巴米扬大佛佛窟进行抢救性加固),“有幸”在一天之内拜大佛:闯雷区、遭遇塔剥班。
11月7日清晨,我赶在日出时分拍摄了一组巴米扬谷地的照片之后,同行的使馆老邓提议说,附近有一处阿米力尔湖,风光不错,值得一看。我跟首席曹卫国商量了一下,反正原定的采访任务基本上完成,抽半天时间走一遭,说不定会有什么新发现。
从巴米扬谷地到阿米力尔湖全程90公里,基本上是荒原,常常是车子开出十多公里也见不到个人影儿。不过一路上为独特的自然风光所吸引,不时地拍拍照片,走走停停,也不觉得孤寂。中午时分,我们到达了阿米力尔湖区。所谓到达,是因为前面没有路了,但见万丈山崖上有溪水潺潺而下,爬上山崖一抬头,便与阿米力尔湖的万顷碧波撞个满怀。真应了那句话,绝美的风景都在绝险处。阿米力尔湖是由七个与瀑布相连的火山湖组成,有如七颗镶嵌在山巅的翡翠。由于这湖面积巨大,又地处高原,日照强烈,每天蒸发的大量水汽使湖区方圆百里内的小气候变幻莫测。当日我们只在湖区待了半小时,当地的向导便指着东边半空中的一团黑云提醒说,东边已经上云了,一会去巴米扬的路上会起沙暴,你们得抄近路赶紧走。
按向导的指引,我们的车开上了那条近路。翻过了一个山头,往下一看,大伙全傻了。山坡下已经没有路了,只有前人留下的两道车辙,紧贴着车辙的是两列刷着红油漆的石头枣,我们闯进了雷区!路的宽度刚好可以通过一辆车,而且只能压着前人的车辙走,没有掉头的空间,稍有疏忽就可能触雷。这次算是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不敢越雷池半步”。
没有退路,只能硬闯了。
我刚要开车,老曹拍了我肩膀一下,把他的防弹背心递了过来:
“把这个坐到屁股底下吧,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此情此景,老曹这举动真是让我心里咯噔了一下,说不清是感动还是悲壮。我推开他的手,把自己身上穿的那件脱了下来,垫在了座位上。这时突然想起来,不知是谁曾经跟我说过,阿富汗的地雷多数是针对步兵的跳。
雷,这种雷一旦被触发要先从地下跳起半米多高再爆炸。我心想这地雷要跳起来总得花个工夫,只要我把车子开得足够快,即使真的.踩上雷,兴许也能躲过去。横下一条心,一脚油门踩到底,我们的:
“陆地巡洋舰”在崎岖的荒原上以120公里的时速飞驰着。双手紧;紧地抓着方向盘,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前面的车辙,两边不时有一具具触雷炸毁的汽车残骸闪过。直到路边再也看不见漆成红色的石。
头,我才慢慢把速度减了下来。这时才感觉到刚才一直死夕E地踩着油门的右腿一个劲儿地抽搐。过了雷区心情放松多了,大伙都长出了一口气,谁知这口气还没出利索,又出事了。车子翻过一个山包,前面是个大下坡,我把速度放得很慢。突然从路边窜出四个缠着头巾的大胡子,一人手里端着一把“AK一47”。四个黑洞洞的枪口齐刷刷地直对着我们。为首的一个大胡子冲上来一把拉开车门,枪口抵在我脑袋上,一摆手示意我熄火下车。我走下车来,用手指着身上穿的那件摄影背心上的国旗,告诉他,我是中国人,之后把两个大拇指并到一起跟他说:“中国和阿富汗是朋友!”大胡子把枪从我脑袋上放了下来,表情也放松了不少。他跟另外三个大胡子嘟哝了几句,其中一个拿出了一部海事卫星电话在讲着什么。过了一会儿打电话那人又跟这头目嘀咕了几句,头目冲着我们的阿富汗籍翻译扎比叽里咕噜喊了一通,扎比跟我说:“他说了,他们是塔利班,他们刚才请示了司令,人可以放走,但车要留下。”这时老曹走了过来,从兜里掏出一把零钱很大方地塞到头目手里,用力握了握,又用极其诚恳的目光盯着那头目,头目终于把枪往肩上一背,冲着旁边三个弟兄一挥手,顺着小路爬上坡走了。
我重新发动了车子,再次上路,大家都不言语了,车里静得让人难受。“曹先生,刚才你一共给他们多少钱?”扎比问老曹。“大概是十个美元、五个欧元外加四百多阿富汗尼,总共不到30美元。”老曹说。扎比琢磨了半天,冒出~句:“真便宜呀,也就半只羊的价钱。”
喀布尔离我很近
2003年12月17日,接到总社的电报,通知我和摄影记者王雷在完成阿富汗制宪大支尔格会议报道后结束任期回国。人的感情真是很奇怪,之前明明是盼星星鼢月亮似的等着这份电报,一旦真的要走了,又觉得心里一下子空落落的。虽然行程还没有最终确定,但行李却早早地收拾好了,脑子里一遍遍预演着与雇员们一起吃“散伙饭”,以及之后挥滑而别的场景。
接下来的日子颇不平静,整个大支尔格会议期间瞎布尔接连发生了五起恐怖袭击,最多的一次炸死了五个警察。在喀布尔这一年,这种场面见得多了,应付这种突发恶性事件的报道从技巧上讲已经很纯熟了。但在接近岁束时看到现场那遍地的残肢和血迹,心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颧。不禁要闽,为什么总有人过不了这个年!父母亲对阿富汗盼关注程度在2003年岁末这几天也上升至历史最高点,每次给家墅打电话,他们都会一遍遍地嘱咐我,千万注意安全……我知道,他们这后半句的潜台词是:“三百六十拜都拜了,千万别在临回国前出点岔子。”
谢天谢地,除了订票对遇到点困难,让既定的行期推迟了几天,一切还算顺利。真正告别喀布尔是在2004年1月18日,由于飞机起飞前一个小时才拿到票,忙乱中都没来得及跟雇员们说上几句惜别的话,更省掉了挥泪两别的章节。直到飞机降落在伊斯兰堡机场我才明自:我将不能常回喀布尔了。
早上7点40分,载着我和王雷的那槊编号为PK 852的巴基册坦国际航空公司的班机降落在了北京国际机场。从机场到新华社的路上那些穿梭的车流、鳞次栉比的高楼流露出的繁华气息让我一下子有些难以适应,甚至有些紧张。我知道,我有些时空错位,尽管人已经在北京了,僵心还在瞎布尔。
到外事局报到,分管瞎布尔分社的王萍一见到我,马上从桌上拿起一份电报,“你人还没到好事儿先追着你来了”,小王乐呵呵地把电报递过来。我一看,是老曹前一天夜里发的,还是特急电。电报大意是:阿富汗过渡政府总统府新闻办公室主任疆前通知分社,卡尔扎伊总统选中了我分社孙闻同志于2003年8月19日拍摄的一张其在阿独立日庆典上向群众挥手致意的肖像,总统拟请新华社协助洗印600张,用于大选宣传之用。“刚才跟摄影部联系了,徐祖根(摄影部主任)说了,外国元首选用新华社记者拍的照片用作大选宣传,这在新华社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活儿他们接了”,王萍说。
我说:“这下我又有的吹了。”“你值得吹的还不少,去年新华社亚太地区总分社总共得了22篇英文好稿,弥们分社独得9篇”,王萍又透露了一条好消息。“这些留着慢慢吹吧。其实你们最大的胜利就是平安地回来了,这比什么都强。”
“回来了?回来就好!”当我把回国的消息告诉国内的亲人朋友们时,一遍遍地听到这句话。当晚我坐上了从北京开往青岛K 25次列车。目的地:青岛;目的:豳家过年。“起来了,起来了,都下车了,你还睡。”19号一早,当车厢里其他旅客都下得差不多了,列车员用略带埋怨的“青普”把我叫了起来。说实话,一年了没睡过这么香的觉。
圆到家里见到了这一年来为我的安全最为担心的爹娘。当我急着打开箱子取出为他们准备的礼物时,听到妈妈轻声说了句:“瘦了,也黑了。”抬头看到爹娘额上的皱纹和两鬓的白发又多了不少,猛地想起这其中大多是因我而生的,心里不由一酸,一忍再忍眼泪还是流了出来。
临近除夕,窗外不时传来鞭炮声,头几次听到这类似爆炸的声音时,我还会下意识地打个激灵,想冲出去“出现场”。喀布尔情结在我内心深处已经打上烙印了,此生我也许不会再去阿富汗,但我永远不会忘记这片我曾为之激情澎湃的土地。除夕夜,当荧屏上那一串拜年的名单里出现“中国驻阿富汗使馆”时,我的心又飞了回去,因为喀布尔离我很近。
李宾1994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法语专业,同年被分配到中央电视台工作。
先后在海外中心的法语节目和英语新闻
节目组工作,1999年被派往法国巴黎做驻站记者,一直到现在。曾连续两年被评为优秀驻外记者。在法国驻站六年时间,见证了法国总统选举和法国政府的更迭。
——一六年法兰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