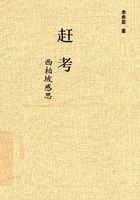于是,从2002年12月17日踏上阿富汗国土那一刻起,我毫无保留地奉献了自己的全部激情,力图通过自己的报道把读者脑海中对阿富汗那些管窥蠡测的印象连成一幅剪影。随着一篇篇文字的发出,我相信,读者应该看到了充满血腥的恐怖袭击、衣食无着的归国难民、步履维艰的战后重建,以及阿富汗人民对未来生活的无限憧憬……
飞向喀布尔
2002年12月17日上午,作为新华社喀布尔分社首批常驻人员之一,我与分社首席记者曹卫国、摄影记者王雷一道,从伊斯兰堡登上了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的班机。登机前每名乘客都被要求在一份声明上签字,大意是:我搭乘WFP班机飞往喀布尔完全出于自愿,我已经清楚飞机可能会遭到袭击,如遇不测,后果自负。
由于从此前新华社派驻阿富汗的八批报道组同志那里已经了解到会有这么一出,所以当时的反应是:“原来真是这样。”
登机后不久,机长发话了:“各位联合国职员,以及自愿搭乘本次航班的非联合国工作人员,飞机再过五分钟就要驶入跑道。由于此行目的地是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我们对途经地区的安全状况没有把握。我们知道,飞机的飞行高度在肩扛式榴弹发射器的射程内。
如果您对此行的安全尚存顾虑,可以在5分钟内离机,我们的工作人员将协助您办理退票手续。”
听了机长这番话,心立刻提到嗓子眼。我下意识地看看身边的曹卫国和王雷,三人用眼神交换了一下内心怪异的感受,又环顾四下,发现大家脸上的神情与我们差不多,但没有人流露出要走的意思,我们也就横下一条心,系上了安全带。5分钟后,飞机开始缓缓地滑向跑道……
“看,下面有个村子!”在阿富汗境内飞行了30分钟后,我第一次发现了一处可以称作“人类文明”的标志物。曹卫国和王雷也立刻凑到舷窗边,满怀欣喜地张望着我们在阿富汗境内发现的第一处人迹。
5分钟后,飞机在这处我称之为“村子”的地方降落了,飞机在跑道上疾速滑行之际,机场一隅一栋两层小楼上的几个蓝色大字KabulIntemational Airport(喀布尔国际机场)印入了我的脑际。终于平安地到达了。
走出机场,见到早已迎候在那里的上一批新华社临时报道组三名成员。三个月阿富汗生活在他们脸上催化出一种“夜半三更盼天明”的表情。于是,见面后不分长幼,不论性别,相逢的礼节跳过了握手,直接上升为拥抱。三天后,我们再次来到喀布尔国际机场,送别这三位前任战友,由于分享了我们带来的夹着祖国母亲体温的全部罐头食品,三人的气色已大有改善。临时报道组组长老汪,年过不惑但仍保持着诗人气质,步人海关前的最后一刻向我们哥儿仨用力一挥手,郑重地喊了一声“保重”。为期一年的阿富汗之旅真正开始了。
第一场战斗
进驻新华社喀布尔分社驻地的第一天下午6时多,大家正在整理行李,东边突然传来闷雷一样的一声巨响。二话不说,我们带上各自的“家伙”、开上车往东奔,边走边打电话四处打听。终于从驻阿富汗国际安全部队发言人高登-麦肯齐那里得到了确切消息:位于喀布尔到贾拉拉巴德公路沿线的多国部队德军威尔豪斯军营内一架直升机坠毁。由于判断准确,确认这一消息时,我们已经在通往威尔豪斯军营的路上。、我立即拨通了新华社香港亚太总分社编辑部的电话,向值班编辑口播了这条快讯。事后,从总分社的发稿月报中得知,我们对这一事件的报道最快,比紧随其后的法新社早了3分钟。
到达威尔豪斯军营时,现场已被封锁。我走到一名看上去像是最高长官的德国军官面前,调整出一幅严肃中稍带伤感的神情对他说:“你好。听说刚刚发生了一起悲剧……向你们表示同情。”那名军官一听,脸上严阵以待的紧张神情立刻缓和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悲凄的表情,沙哑着嗓音说:“真是一场巨大的悲剧,我们的五名战友牺牲了,坠落的直升机还砸死了两个小姑娘,小的才8岁,大的也不过12岁。真是一场悲剧呀!”听他开口了,我嘟哝了一句:
“天哪,究竟发生了什么?”“那架CH一53型直升机执行的是例行巡逻任务,可是升空不久发动机失火,5分钟后迫降时坠毁,”军官沉痛地说。得,该有的信息都有了。我掏出记事本写下分社的电话递给他说:“很遗憾在圣诞节前夕得知这个令人悲痛的消息,等你们举行悼念活动的时候别忘了通知我。”这位军官也马上给了我一张名片:“我是驻阿富汗国际安全部队德军新闻官托马斯·洛伯林,我会把你的问候转达罹难者家属。”
回到分社,我立即追发了一条“详讯”,再次成为对这一事件的独家报道。
这是我与洛伯林的首次见面。2003年2月,德国接管驻阿富汗国际安全部队指挥权后,他升任这支多国部队联合新闻办公室的总新闻官。我也就经常在各种场合见到他,通过他与驻阿富汗国际安全部队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当年5月11日,为感谢新华社对国际安全部队在阿行动全面深入的报道,司令部授权联合新闻办公室向分社颁发“最佳合作伙伴”奖章。
三个月后,德国把驻阿富汗国际安全部队的指挥权移交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洛伯林的任期也结束了。临行前,分社款待了这位朋友。当时我正在国内休假,本以为没法向这位朋友说再见了,没成想当晚洛伯林把电话打到了我家里,一开口就用上了那句我教他的中国话:“How are you(你好),哥们儿!”叫得我眼睛湿湿。
肚子问题
到喀布尔一个多月后,连续腹泻终于让每个人都掉了差不多10斤肉。大家都有些支撑不住了。于是痛下决心,动用出国时带出来的“战略储备”——两箱挂面。为了让有限的挂面发挥最大功效,当时的做法是每天中午吃挂面,而且三人只吃一包(500克)。
现在回想起来,正是这两箱挂面,让喀布尔分社在最艰苦的时候保存了战斗力。
在阿富汗生活和工作,首先面临的是肚子问题。所谓肚子问题又要一分为:二:其一是用什么东西把肚子填饱,其二是用什么办法阻止腹泻。
我们到喀布尔的时候正值冬季,本来就物资匮乏的喀布尔,蔬菜供应更为紧张,而且价格奇高,每公斤黄瓜要价6美元。能买到的比较适合中国人口味而且价格适中的蔬菜只有三样:土豆、洋葱以及像苹果一样坚硬的西红柿。
由于地处高原,紫外线照射强烈,再加上连续五年大旱,使阿富汗出产的所有蔬菜水果都具备水分少糖分高的特点,甚至还造就了世界上最优秀的土豆。据说阿富汗土豆是世界上淀粉含量最高的品种,内战前土豆曾经是主要出口创汇产品。有了这么好的土豆,再加上市场还算丰富的牛肉,我们自然而然地想起了一道名菜。
于是,正式入驻分社当天,我们就精心炮制了一大锅“土豆烧牛肉”,就着大米饭吃了个饱。谁知当天夜里,我们哥儿仨就“不敢放屁,只因腹内翻覆”难耐,不停地穿梭于各自的卧室和卫生间之间。
分社的三个:卫生间同时满员的情况,当晚至少发生过五六次。服用了三倍于正常剂量的黄连素之后,次日中午,我们三人的情况才逐渐平稳下来。哥儿仨一合计,很可能是牛肉有问题。于是,从冰箱里拿出前一天剩下的生牛肉,首席记者曹卫国一刀下去,我们不由倒吸一口凉气。只见切口处密密地排着一溜十来个黄豆大小的囊尾蚴。打那天起,我们再也没吃过牛肉。
后来才知道,阿富汗市场上出售的肉类都没有经过任何卫生检疫。肉类产品上虽然也能看到一个类似于国内卫生检疫专用章的印记,但只是表明牛羊符合清真标准。从第二天开始,我们就基本上以吃斋为主。待到“嘴里能淡出鸟来”的时候,我们会去市场踅摸一只活鸡,先煮,再蒸,最后上高压锅闷上个把小时,等吃到嘴里,这只经过各种办法严格消毒的鸡,已经只有肉的感觉而没有任何味道了。
即便如此,腹泻还是会不时光顾。经过反复论证,严格分析,我们发现罪魁祸首是当地市场上买来的大米。五年大旱几乎让阿富汗颗粒无收,所以,现在能买到的大米最新的也是五年前的产品。
这种大米原本已是土黄色,不法商人为了让它好看一点,会用牛油把它拌成金黄色。这种米做出来的饭,一开锅时窜出来的霉味能把人顶个跟头。
挂面总有吃完的一天。于是我们也开始就地取材,用土豆、洋葱和西红柿这“老三样”大做文章。一次,中国驻阿富汗大使孙玉玺的夫人马骅领着使馆几位年轻人来分社做客,我们奉献了一桌“老三样全席”,菜单如下:
头三道是凉菜:凉拌土豆丝、糖拌西红柿和老三样沙拉;跟着是几道热菜:醋熘土豆丝儿、西红柿炒鸡蛋、干炸洋葱圈、拔丝土豆、土豆丝鸡蛋饼、炸薯片;随后是一道老三样奶油浓汤;最后是一道甜品:巧克力土豆泥。
算下来当天一共做了十一道菜,使馆的几个小哥们儿吃得不住点头,大使夫人的评价是:“新华社的同志生存能力极强。”
现在,最后一包挂面还放在分社厨房的柜子里,即使在我们仨有人高烧超过39度,也没有用它换取卡路里。它将作为新华社喀布尔分社“博物馆001号”藏品和“镇社之宝”永久封存,用于记录那段艰辛岁月。
穿上背心出现场
经历了长达二十三年的战争,阿富汗已经走到了破产边缘。最突出的一个特征是“通信基本靠喊”。如何抢到报道上的先手,是对这里所有记者的最大挑战。迎接挑战的唯一出路就是充分发挥人的作用。在与美联、法新、路透等通讯社的竞争中,我们逐渐崭露头角,在一些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中取得了领先地位,逼着他们与新华社“对表”,在阿富汗激烈的新闻竞争中为新华社赢得了一席之地。
去年5月21日上午11时,喀布尔美国使馆卫兵枪杀三名过路阿富汗军人,当时曹卫国和王雷正赶往离事发地点不远的驻阿富汗国际安全部队司令部,准备参加那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听到枪声后,他们立即赶到现场,我在分社根据他们从现场采集到的第一手资料,在第一时间抢发了英文稿。曹卫国在电话里一再对我强调,三名阿富汗兵只是在转移库存枪支,他们搬运的只是空枪身,没带弹夹,更没有子弹。于是我在稿件中明确指出责任全在美方。
大约一小时后,美联社记者给我打电话,称他从美国使馆得到的说法是三名阿富汗士兵朝美国使馆开枪在先,美国警卫是被迫还击,“你们是否可以考虑据此对先前的报道作一下更正?”
“You are taking nonsense.Ⅱyou want,please fbllow OUI’reports,i±you don’t want,shut up.”(你在扯淡。如果你愿意,可以跟着我们报,如果不愿意就闭嘴)有了曹卫国的话垫底儿,我的回答有些不客气。
曹卫国和王雷从现场回来后,我又进一步核实了情况,并把美联社来电话要求改稿的事儿告诉了他俩。王雷说了一句:“他以为他是谁!”一小时后,王雷发出了照片,有两张特别有说服力。一张是三具尸体,可以清楚地看到三人的中弹部位分别是头部和胸部,而且是一枪毙命,说明他们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遭到了枪击。另一张是一堆散落在地上的AK一47型步枪,都没有弹夹,排除了三名死者开枪在先的可能。
当天下午,分社宾客盈门。由于美国大兵事后立即封锁了使馆附近的各个路口,我们的报道再次成为独家。路透社、法新社、《纽约时报》、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各路记者们竞相来到分社,希望进一步了解细节。外国记者们还挺了解中国风俗,知道头一回登门不能空着手。分社收获颇丰,共计啤酒一箱、波尔多干红葡萄酒两瓶、巧克力一盒。面对“贿礼”,我们哥儿仨采取了“糖衣照吃,炮弹退回”的策略,订立了严密的攻守同盟,对各路记者统一口径:“欲知详情,请到WWW.xinhuanet.com英文版查阅我们的通稿和照片。”
当天,除了美联社在报道中坚持与美国使馆保持一致以外,其他主流媒体都被我们争取了过来。尤其是王雷的那两幅极具说服力的照片,更是广为引用。这次报道真正让我们在喀布尔众多强势媒体中崭露头角。
在突发新闻事件中能否抢到先手,运气相当重要。但通过多跑路,少睡觉,勤打听,这种运气会时常眷顾我们。6月24日,我值夜班,25日凌晨2时手头给《参考消息》准备的一篇稿子已近尾声。
分社聘请的保安法鲁克突然冲进我的房间,指着外面冲着我喊:
“Bigproblem:,big problem!”(大麻烦,大麻烦!)我拉开窗帘一看,夹着浓烟的大火已经烧红了喀布尔南城半边天。我抄起防弹背心,冲出房间,边砸曹卫国和王雷的房门边喊:“出事儿了,穿上背心,出现场!”等我到楼下把车子发动起来时,他俩也披挂整齐拎着家伙上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