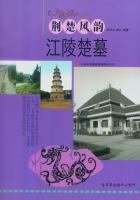沙新
秦坝关,这个名字我们十分陌生;但对50岁开外的“老宁夏”来说,这名字却是响当当的,就在20年前它还的船来船往,是黄河沿岸闻名遐迩的水陆码头。然而往日的繁荣已被时间的巨手无情地翻了过去,如今的秦渠乡却因远离市镇、交通不便、人多地少诸种因素,几乎被历史抛弃在黄河岸边了。
由青铜峡的峡口乡横跨过银平公路,沿一条土石路继续驱车前行,不久便进入了位于吴忠市最西端的秦渠乡的地界。这里给我们印象最深的便是随处可见的、盖得精巧、别致的清真寺。据乡党委书记何文斌介绍,秦渠乡回族比例占78%;全乡共有清真寺24座,有的一个村就有3座。这天是星期五,正是穆斯林的礼拜日,不少中老年回族群众身着干干净净的衣服,或徒步,或骑自行车向清真寺集结。
“好浓厚的宗教气氛”。我们起初这样想。但在深入采访中,我们却发现,这里的回民却具有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近两年更是注重对子女的培养。我们了解到,这里的回民群众没有一人将学龄少儿送到清真寺念经,甚至还流传着许多为了不误儿女学业,自甘负重的可歌可泣的故事。这种截然对立的现象简直是一个难解之谜,直至我们采访结束,也只解开了一半。
秦坝关大寺内热闹非凡,形同集市。据说这座并不宏伟的清真大寺以其历史的悠久而声名远播。一位正欲进礼拜堂的面容清癯慈善的老者被何书记唤住。这位老者叫马殿文,有8个孩子,只种着几亩薄田,却与两年前去世的老伴一起历尽辛劳,支持4个孩子考上了大学和中专,1个孩子通过考试被录用为干部。
我们来到马殿文家。这是我们沿黄河采访以来到过的最贫寒的家,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更见不到任何家用电器,一句话,嗅不到一点时代的气息。提起往事,马殿文眼中充满了泪水,但却说不出一句话来。他最小的女儿,今年22岁的马凤萍,一句一叹地给我们介绍:我们家共有8个孩子,我小的时候,家境十分清贫,大姐和二姐因此没能上一天学,至今父亲提起来仍追悔不已。“再苦再累我们也不能耽误孩子们的前程”。父亲和已过世的母亲自下了这决心,便承担起家里和田里的一切活计。大集体时一个劳动日只有4角钱,日子过得那个紧就不能提。这地方人多地少,如今人均也只有8分地。按最初的5口人我们家分到了4亩地,去年收入还算好才200多元。前几年,每到新学期来临,父亲便从街上称来几斤废黄纸,剪裁一番,给我们订作业本。我们的作业本基本都是写完了正面,再从背面写起的。大哥在金积上中学时家里没有自行车,父亲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将大哥一直送到5里路外的秦渠乡政府处,看着大哥没了人影才转身往回走……
“当时日子非常艰难,但我没想过让孩子们放弃学业回来干活。只有学了知识,才能改变自己和这一方百姓的命运。”目不识丁的马殿文的这番话,令我们肃然起敬。如今他的大儿子马振东已由吴忠师范毕业在巴浪湖农场中学教书;二儿子马振中由郑州粮食学院毕业后分在自治区粮油工业公司工作;三女儿马凤琴高中毕业后参加吴忠市招干通考,被选聘为少数民族干部,现已担任金积镇妇联主任;小女儿马凤萍去年考入宁夏电大汉语言专业,在中卫就读;三儿子马振新去年考入陕西师大历史系;小儿子马振斌今年考中专落榜,这学期已开始复读,准备来年再试身手。
请再看看被选进我们采访本的另外几个事例:丁自仁,大院子村八队的回族农民,一位中年汉子,家有4子,生活维艰,然而,他一直咬着牙支持孩子们念书,去年他的三个孩子同时考上了中专和高中,成为乡里的美谈。
丁占寿,塔湾五队的一名普通庄户人,儿子去年由吴忠参加高考落榜后,要求复读,学校不收,他便鼓励孩子在教室外站着听课。8天后,感动了老师,终于如愿以偿。
郝渠乡小学校舍紧张而破旧,支书和村长一合计:让,便将村部好房腾给了娃娃们,他们则搬到破旧的房子里办公。
穷则思变。此话当不为错。何文斌,这位回族工农兵大学生,自1984年调到这个乡任书记以来,为托起这块土地,使尽了浑身解数。但他深知,一个人的力量是十分微薄的,“变”的条件是知识,是大批有用之才。所以,在秦渠乡教育被摆在了一切工作的首位。乡里为学校和教师大开绿灯:学校缺操场,马上给几亩地;教师吃菜困难,每人划三分菜地;教师的房地、化肥、木材等需要均优先满足。正因此,这里师资虽差,但教学质量却在全市声名显赫。乡中学连续3年荣获吴忠市教育系统先进单位,还是全市乡级中学里第一个由三类晋升为二类的学校。
采访结束后,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马殿文、丁自仁等所经历的艰辛明天将不会再现,因为这块土地尽管贫瘠,但却充满了活力和希望。
雨后泥泞的乡间小路,三步一滑,七折八拐,把我们引进了板桥村。
没有苇塘的板桥村,8月里到处可见芦柴的踪迹:越过墙头看农家的院内,依墙而立的是一捆捆芦柴;从虚掩的院门向里窥视,院内横放着一卷卷码好的芦苇;院后路旁,横七竖八地堆放着编席所剩的下脚料;一个院门开了,一头小毛驴探出头来,驴车上装的还是席子,赶集的主人尾随其后。
刘风英,一位精瘦的回族妇女,50多岁。她嘴里一边忙着“答记者问”,手下一边忙着编席的活计。“您一天编几个小时?”“我们庄户人看的是‘大表’,从日头出来到日头落,太阳转上大半圈,就算是下班了。有时活催得紧,连夜也得赶。”言语间透着回族妇女特有的诙谐与干练。不难看出板桥编席的妇女惜时如金。刘风英苦干一天能挣两张大团结。在另一家,女主人牛玉彩刚上小学的老儿子堵着后门在剥芦柴秆,牛玉彩自己带着两个大孩子在东屋编席。三人联手编,一条生产流水线,高速度高效益。我们采访组的老李打开照相机镜头,牛玉彩刚考上中专的大女儿一反姑娘爱留影的常态,极不情愿在报上再现她俊美的形象,看来人们观念中的织席女和中专生仍有着不小的差距。
板桥乡有苇编的传统。昔日的板桥湖泊较多,不算湖湾沟汊,光是叫上名的湖就有18个,芦苇砍不尽用不完,苇编是农民祖辈传下来的营生。后来湖填了,席也不许编了。一位干部歉疚地回忆道:“我曾提着锹到农民家里巡视,见到农民偷着编席子,举锹就砍。我前头走了,农民后边戳着我的脊梁骂。”
大包干后,要广开致富门路。板桥的湖没了,板桥农民编席的手艺还在,终于有人看准了这个优势,干了起来。
丁学禄,大集体时曾被永宁、贺兰聘为织席师傅,到处带徒传艺。大包干后他利用原来的师徒关系,到各地为板桥组织苇编的原料,现在,每到初冬时节,丁学禄雇的十几辆手扶车队,浩浩荡荡,从黑泉湖、魏家湖运回了成千上万捆芦柴,分发给板桥的100多个苇编户,席子编好再由他统一经销。乡上帮他解决堆放芦柴的场地,帮助他贷款。丁学禄每年经销芦柴数十万公斤,占全乡的四分之一。现在的丁学禄腰缠万贯,他感谢现行政策,他感谢为他跑腿的乡干部———就是那位大集体时曾用锹砍芦席的乡干部。
我们顺着七折八拐的乡间小路离开了板桥。我们突然产生了一种联想,我们的农村经济,有的时期就如同这七折八拐的小路,一波一折,富有戏剧性的变化——当然有喜剧也有悲剧。而我们的农村干部的功与过,就像编席那样,被时间这位毫不留情的太史公一件一件清清楚楚地编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