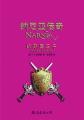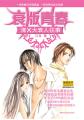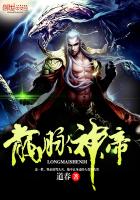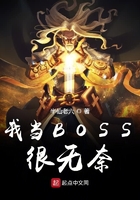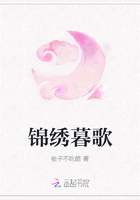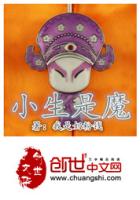鲁迅先生有一篇著名的散文《社戏》名闻遐迩。而在北方农村,看戏也是人们冬闲后的业余文化活动之一,宛若北方农村中一幅幅浓郁的风俗画。
在北京平谷农村,记得小时候,一进农闲,准有戏团送戏上门。一来活跃一下气氛,二来剧团也挣点盘缠。戏台多搭在场边,人们站在干涸的稻地里看。最忙乱的要数孩子们,一听说要演大戏,头好几天就慌慌的不得了,个个兴高采烈,奔走相告,于是,喜信儿不胫而走。到了这天,四邻八庄的人顾不上一天的劳累,拖家带口地奔来。家里勤快的,早早就炒了瓜子,预备晚上嗑;没炒的,奔到村口小贩那去买。小贩跟前摆一粗布口袋,用一只没把儿的白瓷缸往里一灌,缸子冒尖冒尖的,没等你高兴,手指一抹,又平了,一毛钱。日头还没下山,孩子们便早早吃罢饭,扛着长条凳,拎着马扎,仨一群俩一伙去占地方,省得看不见。孩子们是最没耐性的,不等大人们来到站稳,便撒腿就跑,在人群中钻来钻去,一直钻到后台去看稀罕。看演员咋化妆,那些锣鼓家伙如何敲得震耳欲聋、惊天动地。那天演京剧《杨门女将》,我们看到台上被照得如同白昼,再探头探脑往台下看,只见台下黑压压一片,神态各异的父老乡亲随着剧情的发展,喜怒哀乐,唏嘘不已。剧情松弛时,台下便响起一片“喀哧喀哧”嘈杂的嗑瓜子的声音,像有千百只耗子在啮咬东西。
“文革”开始了,古装戏禁演,便放电影。各村都有电影队,不管农忙农闲,只要跑来片子就放。那时,人们的精神生活十分贫乏,闲着也是闲着,《地道战》、《地雷战》之类的电影看了少说也有十多遍也不腻,关键不在看,在于凑一堆儿说会儿话。四邻八庄以外演,也去。成帮结伙,说说笑笑,十几里地打着闹着就到了。荒唐的年代时常出现滑稽的笑话,看电影也要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那次演纪录片《刘少奇访问印尼》,当放到印尼空军做飞行表演不幸失事时,刘少奇同志安慰印尼领导人:“请别难过……”这时一个男声画外音高亢起来:“刘少奇竟然污蔑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空军。往我们祖国脸上抹黑,让我们振臂高呼:打倒刘少奇!”
观众正津津有味地欣赏电影中那豪华的服饰和宏大的场面,和者寥寥无几。
令人记忆犹新的是:那时,样板戏当是最受推崇的舞台艺术,人们多是看电影里演的样板戏。那天,《沙家浜》剧组的演出为小小的县城平添了几分热闹,演出地点设在县中学操场上。公社所辖十几个大队被提前指定在操场上,必须保证人数,否则按政治态度不端正论处。那可真是人山人海,盛况空前。谁都想看看郭建光到底是什么模样。还没到傍晚,大路小路上骑车的、赶车的、步撵的纷纷朝中学操场汇合,比开公判大会时人还多。我们这些孩子像泥鳅—样钻来钻去。终于又钻到了戏台边,扒着台子,着实也开了一回眼界。 随着剧情的发展,只见一个人在幕后双手攥着一块偌大的薄铁板,用力一抖,便发出了轰隆隆的雷声;另—个人趁机将探照灯弄得一明一灭,变幻几次,便成了耀眼的闪电。知道了这一秘密,很让我得意了好几天。那天,人们回家心切,散场时你推我挤,大呼小叫,乱成一团,广场上挤掉的各种鞋子就收了足有—马车。
北方农村的看戏,是那个特定年代的产物,是北方农村六七十年代无意创作的一幅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风俗画,随着时光的推移,将永远定格在人们的记忆中。
1995.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