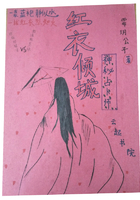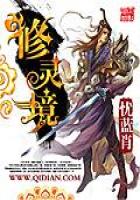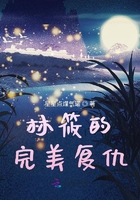精简整编方案实施前一天,真的就发生了一件事。老谭负责审阅的烈士传记方案出现了严重错误,居然将张烈士和李烈士的照片搞颠倒了,成了典型的“张冠李戴”。
其中一位烈士是市委分管领导的舅爷,当时这位领导非常恼火,当即就打电话把史志办主任臭骂一顿。
这是一起严重的责任事故。
第一稿出自陆战之手,老谭复审,最后交由分管的副主任终审。
实事求是地说,以往在文字上也出现过差错,但都没有这次严重。陆战一脸沉重,心想:方案先后看过三遍,照片和人物经过反复对照,特别是张烈士和李烈士的照片,都是拿本人档案里的照片翻拍的。不可能出问题呀?
陆战正想着,老谭对他说:“赶紧找主任承认错误吧,再作个深刻检查,早主动早解脱。”
陆战看看老谭,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
对这起责任事故,主任非常重视,他首先在一个小型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之后亲自作了调查。
正待研究对责任人进行处理时,又出事了。
老谭晚上加完班,准备回家时,头一晕,摔倒在办公室,右脚骨折,右胳膊被桌角玻璃板划了三寸长的一个口子。
老谭在医院住了半个月,这期间,史志办内部网不断出现帖子,开始是柔和的、探讨性的,后来就有了些火药味和战斗性。一篇篇檄文在网上轮番轰炸——
精简整编为什么不涉及领导层?!
老谭的鲜血不能白流!
血债要用血来偿!
有人还画了一幅漫画贴到网上,取名叫《吃人的魔鬼》。画中的魔鬼张着血盆大口,狰狞而凶残,随时都会吃人。
接下来,单位的人纷纷到医院看望老谭。他微闭着眼睛和大家打着招呼,有的向他说起了网上的檄文,他笑着说:“看来引起共鸣了。”
老谭出院前,陆战和姜晴也去看望了他。他面色红润,眼睛炯炯,精神很好。他简单问了一下办公室的情况,便说:“别指望什么精简整编,还是想法调进来靠谱。”
陆战和姜晴都笑着点头。
老谭是在一个下午出院的,本来他是可以多住些日子的,伤筋动骨一百天嘛。当人们看到他拄着拐杖、挎着胳膊走进办公室的时候,都很惊讶,他的样子很悲壮,有些轻伤不下火线、视死如归的味道。
这期间,主任对“张冠李戴”事件又进行过调查。他查看了陆战起草的初稿,没有发现差错,可经了老谭的手以后,就有了“张冠李戴”。这说明,问题就出在老谭身上,不论是主观故意,还是客观马虎,责任都不可推卸。
老谭回到办公室的时候,陆战和姜晴都是一惊。
姜晴挂断聊天的电话,走过去扶老谭坐下,又给他到了杯水,尔后靠在办公桌旁说:“我看这次精简整编恐怕寿终正寝了吧?”
老谭没吱声,右手拿支铅笔,在手里转着。
闻听老谭出院了,不少人过来嘘寒问暖。大家都觉得沾了老谭的光,说不定精简整编会因此泡汤。
陆战和老谭寒暄几句后出了办公室,他走到楼道顶头,透过玻璃窗,紧紧盯着楼下草坪里工人们忙碌的身影。
陆战在楼道里呆了很久,下班前才返回到办公室。这时人事科打来电话,说找老谭。老谭接完电话,脸有些阴沉,就收拾东西要走。当时还有几位问候他的人正在说话,见此情景,有人一边扶他起身,一边宽慰他说:“没什么了不起,挺住!”
陆战扶老谭送了一程,他不想老谭有麻烦,也不想自己有麻烦。
看着老谭精瘦的背影又轻又薄,他走路一瘸一拐地,没有一脚是踩踏实的,仿佛飘着一样,陆战心生怜悯。
陆战再回到办公室时,人们已经散去。
很快,大家都知道老谭被人事科叫去了,却不知是福是祸。有人猜测,精简整编已经开始了,第一个挨刀的就是老谭。
老谭走进人事科,分管副主任和人事科领导已经等他了,在座的还有两位人事科的工作人员,气氛多少有些严肃。领导首先肯定了老谭这些年的工作业绩。说他经验丰富,善于组织领导,业务能力强,勤奋敬业,德才兼备,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老谭越听越觉得不对劲,一般领导对即将受偏的部下谈话,都要首先赞扬一番,尔后才抛出实质性话题。
老谭听着有些心急,说:“你想说什么,照直说吧。”
领导只好进入正题,吩咐工作人员拿出了“张冠李戴”事件的有关材料,说:“经过反复核实,问题出在你手里。”
老谭觉得冤枉,说:“肯定有人陷害我。”
领导说:“在没有证据证明他人陷害你之前,只能委屈你了。”分管业务的副主任也因此被取消了一年的奖金,事后还要在全体人员大会上作检查。之前,主任已经在党委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领导看看老谭,顿顿又说:“经过组织研究,考虑你的身体状况,决定让你暂时回家休养。休养期限不定,期间每月发1000元生活补贴,医疗费全额报销。”
老谭不解,问:“1000元生活补贴是怎么回事?”
领导说:“精简整编后的底薪,按说不工作是没有的,考虑你为史志办做出的重大贡献,特例特办。”
老谭听领导的意思,好像单位已经仁至义尽了。他没有再吱声,起身拄拐就往外走……
其实,以“张冠李戴”事件为由头辞掉老谭,只是个借口。领导认为:老谭虽然表面上嘻嘻哈哈,但经常在背后搞小动作。不仅发牢骚、讲怪话,暮气沉沉、不思进取,还是影响精简整编的绊脚石,是散布流言蜚语的源头。老谭在史志办虽然不算个什么人物,却能蛊惑人心,起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所以首先拿他开了刀。
老谭走了,像只被逐出雁群的老雁。
从这一刻起,河池州史志办精简整编正式开始。
精简整编终于开始了,只不过比原计划推迟了半个月。
史志办的不平静,引起上级很大关注。告状信满天飞,出现“张冠李戴”事件,网上热炒,负面影响不小。头三脚没踢开,主任感到很没面子,上级对是否继续使用他,也有了不同声音。
精简整编冲击最大的,就是中层领导。这个层次的人要想继续担任相应职务,就得脱胎换骨地重新竞争上岗,和血气方刚、有才有识的年轻人同场竞技,要想胜出谈何容易?
姜晴问陆战:“你还不报名?”
陆战很干脆地说:“我没资格!”
姜晴忙说:“报得人很多,其他见习人员也报了。”
陆战犹豫了,他开始对这份工作有些不感兴趣了,至于当领导压根就没想过,那么他在这里耗着究竟图什么呢?整编不整编与他有关吗?
陆战沉默了好久,他觉得眼下还需要有个落脚吃饭的地方。想到自己的标准已经降到维持生存的地步,不由有些心酸。
这期间,梅林又给他打过电话,说特别需要一个写手合作。其实,他和梅林上大学时,就有过合作的基础。那时的梅林虽然学习成绩一般,但有音乐特长,她会弹钢琴,声乐也很入门,每次学校文艺演出,她既是组织者,又是当然的参与者,陆战那时就与她合作过一个话剧,受到一致好评。可每次梅林提出与他合作,陆战都是犹犹豫豫的,他从心里舍不得史志办这个位置。总寻思:等纳了编,用业余时间也是可以写作的。
精简整编如火如荼地进行,但这时上级对主任的信任程度已经大大降低。原因是又出现了一封匿名信。此信措辞严谨、逻辑缜密、论据充分、文采飞扬,看了这封信的人都为之一振。
这封匿名信到处开花,从中央到省、市领导和有关部门都有投递。
匿名信对这次精简整编的初衷提出质疑,批评精简整编负责人不遵守客观规律,急于出政绩,搞得怨声载道、人人自危,谴责主任生活作风不检点,花边绯闻频出,败坏了风气,这样的人岂能担当重任?
单位有人猜疑,这封匿名信出自老谭之手。不少人认为,老谭的头不好剃,第一任主任就尝尽了他的苦头。那次在中层干部会上讨论精简整编的话题,老谭持不同意见,虽然没有与主任当场争执,但事后把观点发到了史志办内部网,鼓动大家讨论。大家措辞犀利,咄咄逼人,在强大的舆论攻势下,让主任很难堪。事后,主任想拔掉他这个“刺头”,可老谭像块橡胶,看着软软的,咬却咬不动。以后老谭天天到主任办公室讲理,且坐下来就不走,直到主任又因别的事悻悻离开这个单位。
如今,老谭又出新招,在大刀阔斧的精简整编浪潮中,处处设阻,暗暗分流。
陆战看着老谭的空座位,有些发呆。桌上的物件虽然堆积如山,但摆得整齐有序,像是主人刚刚下班,上班时还会到位。
据说,那封匿名信从中央到省市领导层层都有批示,市领导还亲自到史志办进行调查了解。
不久,召开全体人员大会。会前人们普遍猜测,主任挺不住了,精简整编有可能偃旗息鼓。
坐在主席台上的主任,脑袋低垂,眼睛微闭,与宣布精简整编方案时的气宇轩昂已不可同日而语。轮到主任讲话时,掌声四起,且一直持续,主任刚要开口,就会被一阵更加猛烈的掌声压住,这显然是在鼓倒掌。主持会议的领导不得不起身,挥手将掌声止住。
主任的讲话言简意赅,但无疑又给人以震撼。他说:“我知道大家对我有成见,但开弓没有回头箭,精简整编势在必行,只要我在位一天,精简整编就要进行到底。”
会场上立时混乱起来,有的高声叫喊,大有群起而攻之的态势。见此状况,主持人立即宣布会议结束,说有问题单独找领导说明。
接下来发生的事更加离奇。第二天一早,主任发现有人从他办公室的门缝里塞进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你女儿在美国被硫酸毁容。”
主任犹如当头挨了一闷棍,立时就蒙了。他只有一个女孩,美貌如天仙,在美国留学已四年,研究生就要毕业了。女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等于要他的命啊!他好半天才想起给女儿打电话,可电话一直无法接通,这下他可真慌了,立即报了警。
警察了解了情况后,通过美驻华大使馆与中国驻美大使馆联系,很快获取了主任女儿的信息:她安然无恙,正在教室上晚自习。
主任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久,主任的手机收到一条短信,内容是:“你家的饮水管道投掷了剧毒农药。”
这次,主任没有像上次那么慌张,但也及时报了警。经过有关部门检测,又是虚惊一场。但他心有余悸,一直在单位与大家共餐,还让家里人回乡下老家躲避了一段时间。
这两起案子至今也没有告破。纸条是打印的,上面没有留下指纹,那天恰逢监控录像检修,没有资料可查。发短信的手机号码无名无姓,是网络虚拟,没有固定地可供查阅。
姜晴在办公室边摇头边笑,说:“太别出心裁了,真难以置信!”
有人猜想这事会不会与老谭有关?但也有人却持不同看法,说这里比老谭有道行的人不在少数。
陆战猜测:“张冠李戴”事件倒像是老谭自编自导自演的苦肉计,因为,按他的脾气性格,如果与他无关,早就闹翻天了,看来他还是默认了。
陆战又不解地问自己:他这是何苦来呢?
想想,陆战又自答:可能为给新主任上眼药,好让市里领导早日换掉他,精简整编搞不成,老谭的既得利益也就保住了。没想到,偷鸡不成蚀把米。
很快,史志办组成调查小组,对每个人进行了询问。尽管陆战有些心里准备,调查小组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老熟人,但轮到他时还是有些紧张。调查人很会调节气氛,一阵寒暄过后,陆战便松弛下来。他们先是称赞陆战是个老实人,并以一种同情的口吻感叹陆战见习几年纳不了编的窘境,最后才把话题转到匿名信、纸条和短信上。说有人对新主任精简整编有意见,但又不摆到桌面上,出此下策发泄抵触情绪,为党纪国法所不容,史志办的人都有责任和义务维护精简整编这个大局。
陆战点点头。
接着,调查人便直截了当地问陆战是否清楚何人所为?
不清楚。调查人员看看陆战,那个准备作记录的年轻人眼神里透出诧异。
发现你周围的人有什么异常吗?
没有。
你在办公室听到有人议论过此事吗?
没有。
调查人沉思片刻,说有些事你不说,别人也会说,谁说谁主动。如果陆战能够提供可靠线索,帮助查出嫌疑人,组织上将即刻着手考虑他纳编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