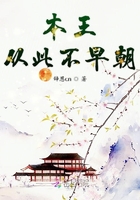清白人家的姑娘谁又肯嫁我?世子的好意阿夏心领了。”
此话一完,俞夏拉起祁礼的手,就要往外走。
潘清霂又急又气,踢飞了脚边的凳子,吼道:“你是我潘家的家奴,我说你不许成亲,就是不许,否则家法处置。”
俞夏理也不理他,拖着祁礼径直出了门。
匆匆走出了老远,俞夏扭头对祁礼笑道:“礼,莫忧!潘清霂就是那样,被我惹毛了,就会拿身份压我,说什么家法惩治,实际上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家的家法是什么。”
祁礼回他了个安心的笑,却待他一扭转回头,那笑即刻僵在了脸上。祁礼若有所思地盯着他的背影,眼不回睛出了神。
而屋子里的文之墨见惯了潘清霂发飙的情景,每次都是如此的莫名其妙,而且每次都是来的突然,去的也快。这样的戏码上演的多了,看的人也疲倦了,反正过不了两天,气该消的也消了,两人又会和好如初。文之墨索性闭了眼睛,不在搭理独自狂怒中的潘清霂。
而全不知也闷声不语,似乎他以前忽略了很多东西,现在需要从头理起,或许为时不晚。
五天。事态似乎比以往严重的多,已经过去了五天,潘清霂和俞夏没有丝毫想要和好的迹象。恢复了生龙活虎的文之墨坐不住了,决定要做些什么,是分个击破,还是一齐攻破?
五天。祁礼已经住进俞夏的房里五天了。在别人眼中,这是一对儿不合礼法,甚至不知羞耻的男女。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在这五天里,俞夏尤其的心安,他正大光明的洗上了阔别已久的热水澡,还是带花瓣的,想泡多久泡多久,清清淡淡的香气熏了满身、满屋,谁又会在意呢?他的房间俨然成了半个闺房,铜镜、胭脂水粉、金银首饰,甚至绣工精致的亵衣,还有可躺可卧的香妃榻,琳琅满目占满了屋内所有的空间。
这些都是祁礼的,准确地说是祁礼为俞夏准备的,同样也是为了掩人耳目。就像俞夏说要娶亲的目的一样,只是想更好地扮演一个男人,而他则是在做一个女人应该做的事情。
意外的是,俞夏对着这些脂脂纷纷瓶瓶罐罐却尤其的钟爱,他怎能不喜欢呢?明明就是还没有及笄的小姑娘,爱美乃是天性,这个年纪放在平常人家,要不是童心未眠,就是情窦初开,而他却悲哀到连自己想要的东西都偏偏要不得。
祁礼一股脑儿买回了好多女儿家喜欢的东西,他对俞夏说:“不能穿,不能用,咱们就先看着,总有一天能够用的上。”
俞夏抿嘴一笑,笑的眼睛弯弯,眼神清亮,笑的犹如夏日的凉风,吹走了祁礼心中的焦躁和不安。
五天。潘清霂在城楼上窝了五天了,度日如年。他不是不想回去,而是不敢。他怕看见俞夏对着那个女人的笑意,那些笑意可以轻轻松松撩拨起他的怒意,还有妒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