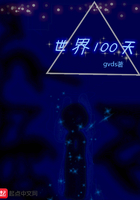这是周莞昭才临政不久,尚未登基时发生的事情了。
佛寺庄严,钟声沉鸣悠然而去,寺庙朱红大门缓缓打开,带起轻风,卷动满地金黄银杏飘起,又慢慢地打着转儿落下去。僧人手持佛珠举于面前,闭眼念佛。
而他面前一道铺满银杏落叶的长阶向山下延伸而去,佛门净地,一时只有庙内隐隐传来念诵经文的声音,僧人因闭眼的缘故,听觉教平常灵敏许多,他听见有人踩着满地落叶一步一步慢慢走上来,最终在距大门十阶的位置停下了。
“侯爷。”那僧人恭敬道。
宋川白眼下有轻微的青色,看上去十分疲乏,两人所站的姿势使宋川白要仰起头看他,然而即便如此,僧人也能感到压迫感。
那是宋川白已经感到极度不悦的情况下,懒于掩饰表现出的情绪。
他道:“民间只说家国危难时道士下山,没想到你们这些成天说着六根清净的僧人,也来掺和龙椅上面的事。”
僧人并未多言,也没有表明自己立场和态度的意思,低眉顺眼地行罢礼,侧身将宋川白让了进去。
此庙主持始终未曾露面,只有这个沉默的僧人带着宋川白绕过正殿佛堂,过了一道极狭窄的,木干搭成的小桥。宋川白往脚下溪水望了一眼,清澈的水面上浮着小圆荷,有根有茎的真花已经谢了,一只纸折的莲花里搁着一盏灯,缓缓地顺着溪水漂流到宋川白脚下,又顺着水流向前飘去。
宋川白看了一眼,突然命令道:“把莲花灯捡回来!”
他语气十分强硬,以至于僧人先是愣了一下,随即转头去看越飘越远的莲花灯。
“捡回来!”
僧人不知他为何突然发难,沉默地领命而去,几步追上莲花灯,涉水将它捡了回来。
宋川白捏着那盏灯,沉着脸跟随僧人到了偏厢房,一个年纪较大,两鬓灰白的男子便急切地迎了上来,道:“侯爷......”
宋川白将手中的花灯往他面前一摔,那人被吓了一跳,道:“侯爷这是何故?”
“阁老,”宋川白冷冷道:“我还叫您一句阁老,您是看着太子长大的,这么多年来可谓是鞠躬尽瘁尽心尽力,可是终归是老了,蠢得要带着太子唯一的子嗣来送死了!”
郭阁老干瘪的嘴唇颤抖片刻,呐呐道:“侯爷年纪小时,太子也十分疼爱侯爷的。常在我们这些臣子面前谈起侯爷的聪慧,只恨不能教侯爷多在东宫呆些日子。”
这感情牌打得简直要把宋川白气笑了,他没理这老人的感慨,指着地上摔坏了的莲花灯道:“这是我在这寺中溪水里看到的,你可知这水最终会汇入何处?”
“护城河!”宋川白只差没有指着他的鼻子了:“其中还会经过多少河道,水渠。太子黄口之年举办的河灯会,满城皆知,当年整个京都的人,都在河水中找太子折的那盏花灯。当时全京都的人都在放河灯,各式各样的河灯铺满了水面,可太子的那一盏还是被找了出来。那是因为他折的特别!因为那是小太子殿下独创的折法,没有人敢去学他!为了找他那盏灯,民间甚至专门绘制了他那盏灯的制式,当时几乎是人手一张,站在河岸边找莲花灯。”
“我问你,这盏只有太子才会叠的灯倘若是漂了出去,百姓中有谁发现了呢?弥天司暗部中哪怕有一个暗卫认出来了呢?成批的暗卫立即就会顺着水流搜查到这里!”宋川白厉声道:“这里面的僧人,也一个都不用活了!”
郭阁老明白过来里面的玄机,当即冷汗就出了一层,低低地说:“皇太子近来心情低落地很,老臣只想着叫他叠着玩玩散心罢了,没看住叫皇太子给放了,是老臣的不是,老臣糊涂了!”
宋川白揉了揉眉头,问:“只有你在这里?”
郭阁老应了一声,道:“人多眼杂,目前知道的人不多,佛门清净地,来的人还是越少越好。”
“佛门清净地,”宋川白冷笑了一声,讲:“郭阁老门下一位谋士,难道不是在此庙中剃度为僧?”
“是,不过那都是很早年的事了,侯爷是如何得知此事的?”
厢房外长着一株躯干粗壮而低矮的古木,云一样散开了自己的枝桠,叶子团团地长在一起,样子竟然也比平常的树木要好看。风一吹,这地上的云就窣窣作响,黄叶随风而出,落入树下的水井中。宋川白也没再看阁老,望着那棵树,半响才说:“我以前入宫的时候,太子会给我讲故事。哄小孩儿的神话传说我不听,他便只好说些自己身边的趣闻了。我与太子见面次数不多,所以仅有的那么几次,会记得特别清楚。”
阳和侯还未封候,其父军功也未曾如此显赫之时,宋川白还是常常出入东宫的,只是那时候太小了,太子两只手就能轻轻松松把他拎起来。之后大将军威震西北,回宫受了一次宴赏后,宋川白就不再常去。再见面,太子还把他当小孩子哄,但宋川白其实早就已经不再是能单纯安心听故事的人了。
“可见侯爷还是念着太子啊!”老人说着眼眶就要红。
宋川白眼神一扫,冷淡答:“记性好罢了,我记忆好不是出了名的么?”
“郭阁老今日将我喊来,难道只为叙旧不成?”
“当然不是,如今牝鸡......”
宋川白举手做了一个阻挡的姿势,道:“牝鸡司晨,有辱纲常,愧对先祖,好了,我已经听过无数遍这样的废话,有什么事直接说罢。”
郭阁老面上讪讪一阵,自己也摇了摇头,然后直接道:“这周莞昭之所以能肆无忌惮地执掌政事,除去这城中越来越多的暗卫,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将军的支持......”
骠骑将军在这个节骨眼上率营归京,大部队就驻扎在京都外。
“这是我父亲的意思,”宋川白打断了他:“找我无用。”
当年太子并不是单纯地就把才到手几天的皇位传给了周莞昭,里面清楚地说明了,倘若他有子嗣尚存的话,仍还是传位于子。太子一直有个未接回京都的侧妃,此令一出,当时没能进殿在眼前服侍的心腹老臣立即就想法子要出城去找人,最终抢先在周莞昭之前,将太子侧妃,还有那个被父亲在辞世前,颁布的口谕中封了皇太子的孩子带离了居所。
彼时周莞昭对这个孩子意味不明,但郭阁老等人是万万不可能拿孩子放到她眼前去冒险的。
他们甚至怀疑最后太子将皇位传给她,而非自己的儿子,是在病危之际受了周莞昭胁迫的缘故。
这个与父亲见面比臣子还少的孩子,就因为一纸诏书,被卷入了明争暗斗之中。
这时厢房的窗子忽然吱呀一声,被人从里面掀开了,露出一张稚嫩的,白生生的小脸蛋儿。小孩儿好奇地打量着宋川白,接着被人呵斥了一声:“明则!”便被人拉了回去。
宋川白似有所感,问郭阁老:“皇太子多大了?”
郭阁老能听到他承认皇太子这个身份就已经是激动不已,连忙道:“才八岁呢,可是聪明得很,与太子......”
“有多聪明?”宋川白毫不留情道:“能聪明到治国驭臣,与周莞昭分庭抗礼吗?”
郭阁老一窒。
要八岁的黄口小儿去跟手握弥天司的周莞昭相抗衡,这说出来简直就跟笑话似的。
然而宋川白没笑,他道:“莫要再做无用之功了,他坐不上那个位置,未必也就是坏事。”
郭阁老急道:“周莞昭那妖女难道会放过皇太子不成!太子遗诏已立,话已出口,只要明则还活着一天,周莞昭就会惦念他一天!满朝臣子就会记他一天!难道明则也要同前朝的太子一样,被年纪轻轻锁在深宫中,乞月为饼,一辈子孤零零地靠着残羹剩饭,看着别人的脸色活下去么!”
宋川白脸色一僵。
前朝废太子被关出了毛病,叫宫人亏待出了毛病,有一日对着圆月乞求哭嚎,以为那是宫人端来的饼。
“你少在这儿给我翻典故,”他很快就恢复了原本的表情:“皇太子不会被锁入深宫,也不可能落到乞月为饼的地步去,你们只要给我打消了争权的念头,老老实实地呆着,周莞昭不会赶尽杀绝。”
“郭阁老,”他最后说:“我知道你是不甘心,可这不甘心,值多少条人命呢?”
他转身欲走,身后的门被人用力推开,一妇人跑出来对着宋川白就是一跪,道:“明则是年幼,但帝王年幼之际,摄政王监国,辅佐幼帝,难道也是没有先例的吗?!”
宋川白愕然转回身去,只见一个衣容素雅的女子对着自己深深拜下,她身后跟着一个锦袍男孩子,犹犹豫豫地走过去要牵母亲的衣角,但看见地上摔坏了的花灯,眼眶中立马溢满了泪水。
“你们真是......”宋川白叹息着说:“真是太大胆了。”
“明则,”他蹲下来问:“你想当皇帝吗?”
周明则看着他,竟然没有哭出来,小孩子眼神惊惶无措,声音很软地,轻轻地说:“我想......我想见我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