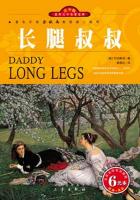穷困英雄涸困龙,一朝奋翔便乘风。
海水可量人乘量,方信天机造化功。
当时李义笑道“张二哥,今日既为手足,何分彼此?好鸟尚且同巢,何况我们义气之交?狄哥哥遭了水难,亲人巳稀,此地访寻,又不知果否得遇亲人。莫若三人同居,岂不胜于各分两地张忠听罢,说道“贤弟之言有理狄青听了二人之言,不觉叹嗟一声,说道“二位贤弟,提起我离乡别井,不觉触动吾满腹愁烦。”张、李道“不知哥哥有何不安?”狄青道“吾单身漂泊,好比水面浮萍。倘不相逢二位贤弟,如此义气相投,寻亲不遇,必然流荡无依了。”张、李齐呼道“哥哥,你既为大丈夫英雄汉,何必为此担忧。古言‘钱财如粪千金义。’我三人须效管、鲍分金,勿似孙、庞结怨。”狄青听了道难得二位如此重义,吾见疏识浅,有负高怀,抱愧良多。”谈论之际,不觉日落西山,一宵晚景休提。
次日,李义取了几匹缎子,与狄青做了几套衣裳更换。张忠又对行主周成说“狄哥哥要用银子多少,只管与他,即在我货物账扣回可也。”周成应允。从此三人日日往外边顽耍,或是饥渴,即进酒肆茶坊歇叙,顽水游山,好生有兴。当时张忠对李义私议道“吾们且待货物销完,收起银子,与狄大哥回山受用,岂不妙哉!今且不与他说明。”
不表二人之言,原来狄青又是别样心思,要试看二人力量武艺如何。有一天,顽耍到一座关公庙宇,庭中两旁有石狮一对,高约三尺,长约四尺。狄青道“二位贤弟,当日楚项王举鼎百钧,能服八千英雄,此石狮贤弟可提得动否?”张忠道“看此物有六百斤上下,且试试提举罢。”当下张,忠将袍袖一摆,身躯一低,右手挽住狮腿,一提拿得半高,只得加上左手,方才高高擎起。只走了七八步,觉得沉重,轻轻放下,头一摇,说声“来不得了,只因此物重得很。”李义道“待吾来。”只见他低躯一坐,一手提起,亦拿不高,双手高持,在殿前走了一圈,力巳尽了,只得放将下来笑道“大哥,小弟力量不济,休得见笑。”狄青道?“二位贤弟力气很强,真是英雄!”李义道?“大哥你也提与小弟一观。”狄青道?“只恐吾一些也拿不动。”张忠道?“哥哥且请一试。”狄青微笑,走上前,身躯一低,脚分八字,伸出猿臂,一手插在狮腿上,早已高高擎起,向周围走了三四转。张忠、李义见了,吐舌摇头道“不想哥哥如此怯之弱躯,力量如此强狠,我们真不能及。”当下狄青提着狮子连转几回,面不改色,气不速喘,将狮子一高一低连举数次,然后轻轻放下,安于原处。张忠笑道“哥哥,你果然勇力无双!安邦定国,意中事耳,功名富贵何难唾手而得。”狄青道“二位贤弟休得过誉!愚兄的力量武艺有甚希罕。”又见庙左個有青龙偃月刀一把,拿来演舞!上镌着重二百四十斤。张忠、李义虽然舞动,仍及不得狄青演得如龙取水!燕子穿梭一般。张、李实在深服。
顽耍一番,三人一同出了庙门,向热闹街道而去。李义道“二位哥哥,如今天色尚早,顽得有些饿了,须寻片酒肆坐坐才好。”张忠、狄青皆言有理。一路言谈,不觉来到十字街头。只见一座高楼,十分幽雅,三人步进内楼,呼唤拿进上好美酒佳馔来。酒保一见三人,吓了一惊,说“不好了!蜀中刘、关、张三人出现了,走罢!”张忠道“酒保不须害怕,我三人生就面庞凶恶,心中却是善良的。”酒保道“原来客官不是本省人声音,休得见怪,且清少坐片时,即有佳酒馔送来。”只见阁子上有几桌人饮酒。那楼中不甚宽大,可望到里厢,对面有座高楼,雕画工巧,花气芳香,远远喷出外厢,阵阵扑鼻。张忠呼酒保,要换个好座头。酒保道“客官,此位便是好了。”张忠道“这个所在,我们不坐,须要对面这座高楼。”酒保说“三位客官要坐这高楼,断难从命。”张忠道“这是何故?”酒保说“休要多问,你且在此饮酒。”张忠听了,问道“到底为甚么登不得此楼?快些说来丨如果实在坐不得的,我们就不坐了,你也何妨直言。”酒保说“三位客官,不是吾本省人,怪不得你们不知。隔楼有个大势力的官家,本省胡坤胡大人,官居制台之职。有位凶蛮公子,强占此地,赶去一坊居民,将吾阁子后厢,起建此间画楼。多栽奇花异草,古玩名画,无一不备,改号此楼为万花楼。”张忠道“他既是官家公子,如何这样凶蛮呢?”酒保道“客官不知其故,只因孙兵部就是庞太币女婿,胡制台是孙兵部知交党羽,倚势作恶,人人害怕。这公子名教胡伦,日日带领十余个家丁,倘愚民有些小关犯,他即时拿回府中打死,谁人敢去讨命?如今公子建造此楼,时常到来赏花游花,饮酒开心,并禁止一众军民人等,不许到他楼上闲顽。如有违命者,立刻拿回重处。故吾劝客官休问此楼,又恐惹出灾祸,不是顽的。”
当时不独张忠、李义听了大怒,即狄青也觉气忿不平。张忠早巳大喝一声道休得多说!我三人今日必要登楼饮酒,岂惧胡伦这小畜生!”说罢,三人正要跑上楼去,吓得酒保大惊,额汗交流,跪下磕头恳求道“客官千祈毋上楼去,饶我性命罢!”狄公子道“酒保,吾三人上楼饮酒,倘若胡伦到来放肆,自有我们与他理论,与你甚么相干,弄得女卩此光景。”酒保道“客官有所不知,胡公子谕条上面写着‘本店若纵放闲人上楼者,捆打一百。’客官呵,我岂经得起打一百么?岂非一命无辜,送在你三人手里!恳祈三位客官,不要登楼,只算是买物放生,存些阴骘罢。”张忠冷笑道“二位兄弟,胡伦这狗才如此凶狠,恃着数十个蠢汉,横行无忌,顺者生,逆者死,不矢卩陷害过多少良民呢!”狄青道“我们不上楼去,显然怕惧这狗乌龟了,不是好汉!”李义也答道有理当下三人执意不允,吓得酒保心头突突乱跳,叩头犹如捣蒜一般。张忠一手拉起,呼道?“酒保且起来,吾有个主张了。如今赏你十两银子,我三人且上楼暂坐片时就下来,难道那胡伦有此凑巧就到么?”李义又接言道?“酒保,你真呆了,一刻间得了十两银子,还不好么!”酒保见了十两银子,转念想道:“这紫脸客官的话,倒也不差。难道胡公子真有此凑巧,此时就来不成?罢了,且大着胆子,受用了银子罢。”即呼道?“三位呵,既然欲登楼,一刻就要下来的。”三人说道?“这个自然,决不累着你淘气的。且拿进上上品好酒肴送上楼来,还有重赏。”酒保应诺。三人登楼,但见前后纱窗多巳闭着,先推开前面纱窗一看,街衢上多少人来往,铺户居民,屋宇重重;又推开后面窗扇,果见一座芳园,芳草名花,珍禽异兽,不可名状,亭台院阁,犹如画图一般。三人同声称妙,说道?“真真别有一天,怪不得胡公子要赶逐居民,只图一己快乐,不顾他人性命了。”
谈论间,酒肴送到,有_开案桌,弟兄放开大量畅饮,又闻阵阵花香喷鼻,更觉称心。原来这三位少年英雄,包大胆量,况且张忠、李义乃是天盖山的强盗,放火伤人,不知见过多少,那里畏惧甚么胡制台的儿子。他不登楼则巳,到了此楼,总要吃个爽快的。酒保送酒不迭,未及下楼,又高声喧闹,几次催取好酒。酒保一闻喊声,即忙跑到楼上说道客官,小店里实在没酒了,且请往别处去用罢。”张忠喊道?“狗囊!你言没了酒,欺着我们么!”一把将酒保揪住,圆睁环眼,擎起左拳,吓得酒保变色发抖,蹲做一堆求饶。李义在旁道:“酒保,到底有酒没有酒?”狄青言道?“酒是有的,无非厌烦我们在此,只恐胡伦到来,连累于他罢了。酒保,如若胡伦到来,你只言我们强抢上楼的,决然不连累于你。”酒保道?“既:卩此,请这位红脸客官放手,吾拿酒来罢。”当下张忠放手,酒保下楼来,吐舌伸唇道?“不好了!这三人吃了两缸酒,还要添起来。这也罢了!只怕公子到来,就不妥当的。”酒保正在心头着急,恰巧胡伦到了。
却说胡伦年方二十开外,生得面貌丑陋。他并非胡坤亲生,乃是继养义子,只贪游荡,不喜攻书,胡坤并不拘束,听其所为,把胡伦放纵得品行不端,平素凌虐良善,百姓一闻他到,便远远躲避,所以送他一个混名胡狼虎。这一天,乘了一匹白马,带了八个家丁,各处去顽耍而回。本来不是要到酒肆中,只因狄青三人未登楼之先,巳有一个无赖汉混名徐二在里面饮酒,后来看见酒保得了张忠十两银子,私放三人在万花楼饮酒。徐二暗言道?“我前日吃他的酒肴,未有钱钞,仰,恳他记挂数日账,他却偏偏不肯,要我身上衣衫抵折了。如今破绽落我眼内,我不免报禀与公子得知,搬弄些唇舌,料想恶公子必不肯干休,将这狗囊混闹一场,方出我的怨气。正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想罢,完了酒钞,出门而去。事有凑巧,胡公子正在那路回府,徐二急赶上跪下道?“小人迎接胡大爷。”胡伦道?“你是何人,有甚事情?”徐二道?“无事不敢惊动大爷,只因方才酒保故违大爷之命,贪得财帛,擅敢容放三人在万花楼饮酒,特来禀矢卩大爷。”胡伦听了,问道?“如今还在么?”徐二道?“如今还在楼中。”胡伦道你且去罢,明天到来领赏。”徐二道谢而去,暗喜道“搬弄口舌,还有赏领,这场买卖真算得好。”
不谈徐二喜悦,却说胡伦怒气冲7中,带了家丁,如狼似虎,一直来至酒肆中,喝问酒保,何人登楼饮酒?当时店中阁内的饮酒人,一见公子到来,一哄都走散了。酒家吓得魄散魂飞,连忙跪下叩头不止。八个家丁跑进楼台,大喝道这里甚么所在,你们胆敢在此吃酒么?”弟兄三人听了大怒,立起言道:“酒楼是留客之所,人人可进。你莫非就是胡家几个狗奴,来阻扰吾们吃酒,好生大胆!”八人齐喝道“我家胡府大爷要登楼来,你们快些走下还好,只算不知者不罪。”三人喝道“放屁!胡伦有甚大来头,不许吾们在此么?快教他来认认我桃园三弟兄,立着侍酒,方恕他简慢之罪!”家丁大怒,喝道“大胆奴才,好生无礼!”早有胡兴、胡霸抢上,挥起双拳就打,被张忠一手格住一人,乘势一撂,二人东西跌去丈远,又有胡福、胡祥飞步抢来。
不知如何争持,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