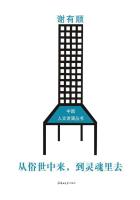话说邢夫人哀嚎不绝,贾琏出入无时,主子气色不是个气色,底下人看在眼里,也都猜疑开来。那说主子力不从心的,趁乱便要捞好处,说末世将至的,更要趁早下手。
李婶从侄女口中得知内情,心说不好,道:“小女婿家要败,大女婿心要变。”见着林之孝家的,因笑道:“你们大奶奶忙的不进家,我们一家三口他屋里白住着,也不是个事。府上虽不撵,我心里也是过意不去的。少不得还要回去。”
林之孝家的会意,说与赖大娘,赖大家的笑道:“我们小子把妹子看的比自个还重,必得妹子出阁,才敢娶亲。想是从薛二爷那里学的。薛二爷顾惜妹子之心,传为美谈,我们便不愿强他。”
林之孝家的道:“听说仇家来求,许了么?”赖大家的道:“想是嫂子听错了,是李家。李家家道丰富,李绪生的也是一表人才,只是他死了前妻,我们小子不愿妹子去填房。”
林之孝家的听了,不好去回李婶。见过王夫人,从夹道往西,走过西花墙,方出西角门,老祝妈拿着一沓子小冷布口袋,看见管家娘子林之孝家的在前头和人宋妈说话儿,飞跑上来,笑道:“林大娘,你这忙里忙外的,也不歇歇,累坏了身子骨,可不是官中的!这又忙什么来?”
林之孝家的道:“凭心罢,太太一时照料不到,我检点检点,也是报答主子。都怕得罪人不管事,乱的更不知怎么样呢!王善保家的眼红田妈,也要在紫菱洲围田养鸭呢!稻香村的呆头鹅偶然到了他的地界,叫他赶的舞天飞,满院子乱跑不归家,还打死了几只,田妈心疼的淌眼睛水。李大奶奶和太太都不愿得罪大太太,唤我进去,把这拆鱼头的事叫我做!”
宋妈笑道:“主子还不能,大娘能做甚么?”林之孝家的笑道:“主子吩咐了,不能不做,少不得还替大奶奶做一趟和事佬。遇上仗着主子不省事的,劝和也是白劝,除非把园子里的田地出产收拢了从新分派!若真那样,你们这些现得了好处的,也要生事!都是只顾碗里,不管锅里的!”
祝妈听了,埋怨宋妈,道:“大娘站着说了这一会,也不请坐,也不请吃茶!”宋妈不忿,道:“你还歪派我,杌子叫你拿去葡萄架下看人看鸟,这里就剩下三只脚的一把破椅子,难道叫大娘坐上去跌一跤不成?叫大娘站着吃我那老树叶子的茶么!”
林之孝家的笑道:“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我去紫菱洲说和,不是挑拨,王善保家的就是不发事,我张口讨茶,还能不给一钟吃?”说了,起步便走,老祝妈跟了一段,在葡萄架前立柱,笑道:“大娘慢走,我就不送了。”说了,拿小口袋一嘟噜套上一挂葡萄。
林之孝家的回头瞧着,笑道:“你这巧宗儿从那里学的?”说时,转身过来,只听祝妈笑道:“袭人上年见我拿笨法子不住手的赶,不离身的累死累活也赶不了多少。如今这法子又透风,又一个儿也不叫鸟儿遭塌。”
说时,伸头一瞧,见着内里架下落了一地葡萄,不知是谁伸进棍子来捣烂捣下的,口里“哎呀”一声,一屁股瘫坐在地下,蹬着脚儿,拍手骂道:“天打五雷轰的!我这葡萄挡着你的坟向了?你这们断子绝孙的暗害我!”
一行骂,一行拟人,心猜是费婆子那皮笑肉不笑的剜心虫干的,便骂道:“你这没廉耻的老草狗,兴时兴过了头,主子也不待见,失势你就暗害人,作恶作多了报应,生个杂种儿子痨病鬼,叫你给他养老送终!从前你偷人窝汉,如今媳妇穿寺入观,养和尚,送去把道士肏,明儿红口白牙生下杂种,你就有孙子了!”
费婆子听见这话,句句扎在肺上,要去拼命,儿媳一把拉住劝阻,他却迎面啐了,反唇相骂:“你做的那些好事,还有脸劝我!我费家几辈子的老脸都叫你这**给丢尽了!”
儿子媳妇狗急跳墙,回嘴道:“人家骂我你就记住了,怎么骂你,如何不说把你儿子听听!”费势卧床已久,黄鼠狼喝了血一般,见生母发妻闹得不可开交,又气又急,喘了半日,作揖道:“罢咧,罢咧,家丑不可外扬,人家骂没法儿,你们倒自报自现的起来!”
他娘见他这个模样,骂道:“不是你吃喝嫖赌得了痨病现世,现在人家眼里,人家就有的骂了?我去和那老狗拼了命,眼不见为净!”
媳妇子冷笑道:“你死了,我一包袱卷了偷人去,看谁给你收尸?瞧瞧你儿子,也该娶媳妇害人?我是**,给我休书,我转背就走!”
费势笑道:“走的日子有呢,我也活不久了。休书叫人都写好了,就在枕头下。白耽误了你这些年,也该与你想一想后路。”婆媳二人,一听这话,戛然住了口,心酸难过,各自出去,不忍再瞧床上之人。
费势安心调理了几日,身子好些,半夜住着扁担,出门摸进荣国府,轻车熟路,都是从前打更常走的。听见祝福儿打锣吆喝着进了荣禧堂后面抱厦东边的鹿顶,知他规矩是在那里吃酒,便转过来,靠着荣禧堂大门坐下歇息。
堂内大紫檀雕螭案上点着长明灯,设着青绿古铜鼎,悬着待漏随朝墨龙大画,一边是錾金彝,一边是玻璃做的一个宝器,不知其名若何。
费势惯是侥幸行险之徒,见财起意,心说:“我死之后,无儿无女,媳妇必定离家,当留老母无依无靠,年轻守寡白养了我一场。”说了,原路回去。次日找到天意,与他一说,天意呆了半日,发恨道:“不做狠心人,难为自在汉。府上抄家灭门的日子也不远了,不如盗了宝逃走,免得株连九族,叫官府发卖。”
说了,便和费势去了几个锁匠铺,找见荣禧堂门上一样的大锁。回头接了王信的重利银子,买了一个来,捣鼓几日,把那锁还真捣鼓开了。
入夜,带了开锁的家伙溜进来,等到祝福儿鼾声如雷,便去悄悄开了锁,拽下大画包裹了金彝,再扯对联来包玻璃宝盆时,慌忙当中,失手把那滑溜溜的宝物掉在地下,哗啦一声碎了满地。
二人慌忙吹灭长明灯,黑中正屏息静听,忽听祝福儿在外喝道:“谁吹的灯?给我出来,别说掖着不动我就不知道!”说时,满身酒气的进来,道:“再不出来,我就嚷了!赵天意,我知道是你,乖乖儿出去,我只当没这事。”
费势又惊又气,气的是他娘祝妈揭人短处,咒人香火,心说:“他咒我家绝户,不如我先绝了他的户!”说时,照着黑影,当头打了一扁担,回手又是一下,打的祝福面条子一般,坐在地下。
费势心说扁担不如搭杵,拼力又盖了不知多少下。天意呆了半晌,道:“只怕出了人命了!”费势道:“下面再和他做兄弟去。才他猜出你了,我不替你杀他灭口,你就死了。我死之后,求你看在我的面上,看顾看顾我老母。这宝贝你转卖了来,就把我那一份与家母养老罢。”
轻诺必寡信,天意儿一口应承下来,抱着金彝随费势出来,各自归去。藏好宝贝,天意次日闻知贾府报官,装个没事人,照常吃赌。
察院司员万丰领着军牢仵作来,验尸拿凶,有条不紊。查得彩霞丈夫官哥儿日不归家,夜不归宿,问得他鸡鸣狗盗,劣迹斑斑,便拿他当了第一个的疑凶,图画海捕,明正典刑,断不容潜藏漏网。
来旺家的哭死过去,彩霞陪着婆婆,欲哭却无泪,只陪着瞽目的婆婆,来至凤姐帘外,搀婆婆在老祝头一边跪下。
凤姐盘坐炕榻,捻珠念佛,抄手锁目,喃喃称念《观世音菩萨平安经》,老祝头听他道:“设入大火,火不能烧,由是菩萨威神力故;若为大水所漂,称其名号,即得浅处。”
忽见来旺家的拜伏在地,老祝头眼中喷火,恨不能喝口水生吞了凶犯生母去,道:“你生儿子谋财害命,害我做老孤老,还有脸来,往我边上贴!来的正好,告诉主子,你把儿子藏在那里!”
彩霞跪下,道:“我男人小偷小摸是有的,害命他却不敢。他那贼胆还没鸽子蛋大,杀个鸡都哆嗦。”来旺家的道:“见官府来拿他父亲,唬的父亲也不要了,就躲到南边去了,并不曾回来,不信去问卜大舅女儿去。”
老祝头道:“你们婆媳一班腔,我不和你们对嘴!我只知杀人偿命,官府怎不说别人,只断定你儿子杀人潜逃?几时出逃,回没回来,你们说的,我全不信!”
来旺家的哭诉道:“二奶奶,我们小子这是跳进潢海也洗不清了,杀头便是冤死鬼,求奶奶作主,设法保我们小子一命,祖宗香火都靠奶奶慈悲为怀。”
凤姐念毕经文,七称“南无阿弥陀佛”,一句紧似一句,疾风骤雨一般。称罢,睁眼开言,道:“我也在求菩萨。”
来旺家的的道:“奶奶就是我的菩萨,不求奶奶,我这眼睛一抹黑,求谁去?他父亲还在牢里,不知是死是活,这儿子又叫人冤枉了一个死罪,迟早拿回来替了死,他们便宜,我这心往那处搁。老祝头老年丧子,人心都是肉长的,说甚么我都不计较。官哥是我肠子里爬出来的,宁可我去顶死,也不能见死不救。求奶奶和官府讨情说——就把我拿去,开刀问斩。反正我也是将死的人了,别叫我白发人送黑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