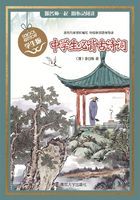刚才,我带着深深的忧虑久久凝视了霍尔拜因画中的农夫,尔后,我漫步在田间,沉思着乡村生活和庄稼人的命运。他耗尽力气和时光去耕犁这片被人们争夺其丰富宝藏的惶惶不安的土地,一块最黑最粗糙的面包便是他一天含辛茹苦劳动的唯一报酬和收益,这无疑是可悲的。这些铺满地面的财富,这些庄稼、果实,这些在旺盛的草地养得肥壮、值得骄傲的牲畜,是某几个人的财产及大多数人劳累、受奴役的工具。享乐者通常不喜欢田野、草场、自然景观,也不喜爱膘肥的牲口,宁可把它们兑换成金币来用。他们来乡间小居,不过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调养一会儿身体而已,然后又回到大城市去消受他的奴臣们的劳动果实。
至于劳动者,他太辛劳、太不幸了,对未来过于担忧,哪有心思去领略乡村的美和农村生活的可爱?对他来说,金色的田野、美丽的草原、漂亮的牲口就是一袋袋埃居[8],而他只拥有其中的微小部分,难以维持生计,可是,他每年还得装满这些可恶的钱袋去满足主人的需要,去购买在他的领地阮囊羞涩、悲惨生活的权力。
然而,大自然永远是年轻、美丽和仁慈的。它向所有生灵、所有植物倾泻诗意和魅力,让它们在那儿如愿地成长。它掌握着幸福的秘密,谁也无法从它那儿夺走这秘密。最幸福的人也许就是这样的人:掌握劳动技能,用自己的双手劳动,运用智力获取安逸和自由,这样他就会有时间用心灵和头脑去生活,去理解自己的使命,热爱上帝的事业。艺术家在凝视、表现大自然的美时就有这种享受;但是,当看到生活在这人间天堂的人类的痛苦时,正直仁慈的艺术家于快乐中也感到不安。幸福也许就在这里:在上帝的瞩目下,人们的才智、心灵和双臂通力合作,那么,在上帝的慷慨和人类精神的愉悦之间就会出现一种神圣的和谐。这样,寓意画家就应该在画的旁边画上一位快乐的天使,将祝福的麦粒大把地播撒在散发着热气的田畴中,而不是那手执皮鞭,走在犁沟中的可悲又可恶的死神。
对于庄稼人来说,梦想过上一种温馨、自由、富有诗意、勤劳而简朴的生活,并不是一件很难实现、非得把它看成是异想天开的事。维吉尔这忧伤、甜美的名言:“啊,庄稼人要是了解自己的幸福,那他是多幸福啊!”是一声叹息;然而,正如所有的叹息,这也是一句预言。这一天将会来到:农夫也会成为一名艺术家,即便无法表现美(那时这并不很重要),至少可以感受美。难道我们相信这种对诗意的神秘直觉在他的身上已不是处于一种本能的、朦胧的幻觉状态?在那些如今才有一点生活保障的人身上——极度的不幸并没有完全抑制其精神和智力的发育——能感受到、欣赏到的纯粹幸福是处于原始状态的;此外,那痛苦和劳累的肺腑,已经发出了诗人的声音,可为什么还有人说双臂的劳动与内心感受机能是相互排斥的呢?也许这一排斥性是过度的劳动和深重的苦难造成的普遍结果;但是我们不能说,如果人们适当地进行有益的劳动,就只有糟糕的工人和蹩脚的诗人了。在感受诗意中获取高尚情趣的人才是一位真正的诗人,哪怕他一生没作过一句诗。
我的思绪就这样奔腾着,我甚至没意识到在我身上,人的可教育性这一信心由于受外界的影响而增加了。我走在田边,农民们为即将到来的播种期正忙着整地。田野如霍尔拜因画中描绘的一样广袤。景色也很开阔,一排排葱翠的树木在秋天临近时稍泛红色,环绕着这片不太肥沃的土地,刚下的雨在几道犁沟留下积水,阳光下像一条条细银丝在闪耀。这一天晴朗温和,土地刚被犁刀翻松,散发着淡薄的热气。地的最高处,一位老人——他那宽阔的背和严肃的面孔使人想起霍尔拜因笔下的那位农夫,但衣着不显出穷相——认真地推着他那老式的、由两头浅黄色皮毛的牛拖着的犁,它们是牧场真正的主人,身材高大,但略瘦,牛角长长地耷拉着,长期的耕作使这两个老伙计结成了“兄弟”,我们乡下就是这么称呼的,如果其中的一头牛失去对方,那它便会拒绝与新伙伴合作,直到让自己忧郁而死。不熟悉农村的人会把这头牛对与它套在一起的伙伴的友情看成寓言。还是让他到牛棚里来看一头可怜的牛吧:它瘦骨嶙峋,精疲力竭,用它那不安的尾巴拍打着干瘪的胁部,惶恐地对送来的饲料吼叫,不屑一顾,眼睛始终转向门口,蹄子扒着身边的空地,它嗅它的伙伴曾套过的牛轭和锁链,一声接一声哞哞地为自己的伙伴惨叫。放牛人会说:“这等于损失了两头牛;它的兄弟死了;它就不再干活了。得把它喂肥了宰掉;可是它又不肯吃东西,过不了多久它就会饿死。”
老农夫沉着地默默耕着地,不浪费一点力气。那头顺从的牛更是从容不迫;但是,由于他专心致志、始终如一地干活,且用力得当,毫不懈怠,所以他那块地同他儿子的一样就快犁好了,儿子就在不远处的一片更坚硬的石子地里驱赶着四头不太强壮的牛。
然而随即引起我注意的确实是一片优美的景色、画家极好的主题。在宽广的可耕地的另一端,一位容光焕发的小伙子驾着一辆出色的套犁:四对小牲口,夹杂着褐斑的深色皮毛反射出火红的光泽,粗壮的颈脖上满是鬈毛,还散发着野牛的气味,它们目光凶狠,动作粗暴,被牛轭和刺棒激怒,烦躁而胡乱耕着地,直到气得发抖才肯服从刚才强加于身的牛套。这就是人们说的新套的牛。驾牛的小伙子得开垦一块不久前弃为牧场、布满百年树桩的地,这是彪形汉干的活,而他年少力薄,加上那八头几乎尚未驯服的牲口,勉强能胜任下来。
一个六七岁的孩子,像天使般美丽,穿着罩衫,披着一块羔羊皮,打扮得像文艺复兴时期画家笔下施洗礼的小约翰,他走在与犁刀平行的犁沟中,拿着一根又长又轻、不太尖锐的刺棒戳牛的胁部。凶暴的牲口在孩子的小手下战栗着,使得犁辕剧烈震动起来,套在它们头上的牛轭和皮带也嘎吱作响。如遇着一个树根绊住犁铧,农夫就用强有力的声音叫唤每个牲口的名字,与其说是鼓励它们,不如说是安抚它们;因为牛被这突如其来的障碍激怒,暴跳起来,用宽大的叉蹄在地上刨坑,要是小伙子用喊叫声和刺棒都控制不住前四头牛,这时孩子在驾驭另四头牛,那它们就会将犁刀横插过地而猛摔向一旁。可怜的小家伙,他也在吆喝,他想让声音变得可怕,然而那声音依然如他那天使般的面容一样温柔。这一切给人以刚柔相济的美:景色,年轻人,孩子,轭下的牛;尽管出现了征服土地这一激烈的搏斗,依然有一种甜蜜的、极其祥和的爱笼罩着万物。待到障碍被克服,牲口重又迈起均匀、庄重的步伐的当儿,农夫一改刚才假装的粗暴行为——当然这于他不过是锻炼一下体魄,消耗一点力气罢了——忽然又恢复了纯朴人所具有的安详神态,朝孩子投去慈父般满意的眼光,孩子也掉转头来向他微笑。接着,这位年轻父亲用雄劲的声音唱起了庄严而又忧郁的歌曲,这是当地古时流传下来的,当然并不是所有农民统统会唱,只有那些懂得如何激发且保持耕牛干劲的窍门的最有经验的农夫才会唱。这首歌,它的起源可能被认为是神圣的,过去曾赋予它神秘的效果,如今却以具有保持耕牛干劲、平息它们的不满情绪、减轻它们长期耕作所产生的厌烦心理之功效而闻名。善于驾驭牲口耕出一条笔直的犁沟,恰到好处地将犁刀抬起或插进土里以减轻牛的疲劳,这是不够的:假如他不会对牛唱歌,那他就算不上一位出色的农夫,而这正是一门特殊的学问,需要特别的鉴赏力和方法。
说实在的,这首歌只是一种可随意中断,之后接着唱的宣叙调。它那不规则的形式和不合乎音乐艺术规律的错误音准使得它无法演奏。但这仍不失为一首优美的曲子,它与那伴唱同步的劳动性质、耕牛的步伐、乡间的静谧气氛、歌唱者的纯朴性格是如此协调,任何一个天才,如果对耕地一窍不通,决创造不出这首歌,除了精明的农夫,本地任何别的歌手都唱不出。在农村除了耕种没有别的活计和活动的季节,这首如此轻柔而又刚劲的歌像萧萧的风吹来,它那特殊的音调与风声有些相似。每一乐句的最后一个音是延长颤音,持续之久,运气之强,令人难以置信,而且还升高了四分之一音,整首曲子都走了调。这是不合乎乐理的,但其魅力是无法形容的,如果你听惯了它,你就想象不出在这种季节、这种场合还能响起什么别的歌声而不破坏其和谐的氛围。
因此,我眼前所展现的是一幅与霍尔拜因版画截然不同的画面,尽管这是同一场景。我见到的不是一个愁苦的老人,而是一位精神焕发的年轻人;不是一套皮包骨头、有气无力的马,而是四对强壮的烈牛;不是死神,而是一个漂亮的孩子;不是一幅绝望的画面,一种破灭的意念,而是一幅充满活力的情景和一种对幸福的向往。
就在这时,那首古法语四行诗“你辛勤耕作……”和维吉尔的“啊,庄稼人要是了解自己的幸福,那他是多幸福啊!”同时在我的脑海中浮现,这时,当我看到年轻人和孩子这一对如此英俊的人,在这么富有诗意的情景中刚柔相济地在完成一件伟大而庄严的任务,我深深地感动了,同时不由自主地感到惋惜。农夫是多幸福啊!是的,假如我的手臂一下子变得有力,胸脯也强壮起来,可以使大自然富饶并歌唱它,毫无疑问,我也会幸福的。这样,我的眼睛能一直不停地看,我的大脑也始终可以领悟色彩与声音的和谐,色调的微妙和轮廓的柔和,总之,万物的神秘的美!尤其是我的心永远和主宰着崇高不灭的大自然那神圣的爱相连。
可是,唉!这个年轻人从来都不懂美的奥秘,这孩子也永远不会明白的……上帝不允许我这样认为:他们不比自己所支配的牲口高出一等,他们不会常常在冥思中有所顿悟,以减轻他们的劳累,消除他们的忧虑!我从他们庄严的面容上看到了上帝,因为他们生来就是土地之王,比起那些用钱购买而拥有土地的人要高贵得多。他们之所以有这种优越感,那是因为如果谁使他们远离家园,谁必定受到报应,因为他们热爱这片用自己的汗水浇灌的土地,并且,一个真正的农民如果弃田从军,远离目睹他出生的这块田地,那他会因乡思而死去的。然而,这年轻人还缺乏一些我所拥有的乐趣,即非物质的享受,这些本该是属于他的,属于这只有浩瀚的宇宙才能容纳的巨大神殿的创造者。他还缺乏对自己感情的认识。那些判定他打从娘肚子起就得受苦役的人虽然没能剥夺他的想象力,却使他丧失了思考能力。
唉!尽管他是这样,既不完美且命中注定永远处于孩童时代,比起那被学识抑制了其情感的人却要好得多。不要凌驾于他之上,你们这些自以为享有支配他而不受时效约束的合法权利的人!因为你们正陷入这一可怕的谬误中:你们的才能扼杀了你们内心的情感,你们才是最无知、最没头脑的人!……同你们脑中虚假的知识相比,我还是更爱他心灵的纯朴;假如要我叙述他的生活,我更乐意突出他平淡而动人的方面,可你们的功劳则是描述他的卑贱,却不知他是被你们的社会格言那严厉、轻蔑的言辞所抨击而陷入这种惨状的。
我了解这个年轻人和这漂亮的孩子,我知道他们的故事。因为他们有一个故事,人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无论谁,如果他理解自己生活的经历,他会对它感兴趣的……热尔曼虽然是位农民,一个普通庄稼汉,但他了解自己的职责和情感。他曾真切、清楚地向我叙述过这些,我也曾兴致勃勃地听他讲。当我久久注视着他,看他耕完地后,我想,为什么不把他的故事写下来呢,尽管这是一个如同他用犁刀耕出来的田沟一样简单、平直而又很少雕饰的故事。
明年,这田沟将被一条新的填平、覆盖。大多数人的足迹就是这样深印在人生这块田地上,继而又消逝的。一点儿泥土就能将它擦去,可我们耕出的垄沟却像墓地的坟头一个接一个出现。农夫的犁沟难道就没有悠闲者的犁沟好吗?这种人只不过由于某种奇特或荒唐的行为在世上小有名气而拥有一个称号,一个流传后世的称号罢了……
好吧!假如可能的话,我们就把热尔曼这个出色的农夫从田沟卑微的境地中拯救出来吧。他对此将一无所知,也不会感到不安;可我还是乐意一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