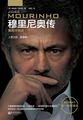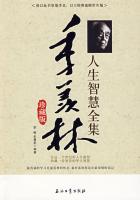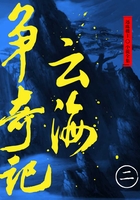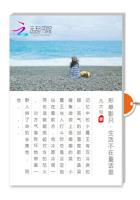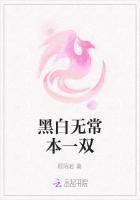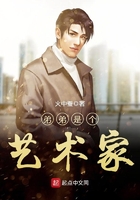初恋,对于每个人都是难以忘怀的,老舍的初恋更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
17岁那年,由于生活所迫,母亲曾到刘大人的宅内帮工。少年老舍跟母亲到刘家的大院去过几次。刘大人有个女儿,恬静、庄重、性格温柔,老舍一见钟情。
她父母在家时,老舍只能呆呆地望着她住的那间窗上、门上都挡着牙白帘的小屋,而她只能隔着窗儿脉脉含情地望着外面的老舍,羞涩地嫣然一笑。
老舍后来在《微神》中这样描绘那段恋情:
“没有像那一回那么美了。我说‘那一回’,因为在那一天那一会儿的一切都是美。她家中的那株海棠花正开成一个大粉白雪球,沿墙的细竹刚发出新笋,天上一片娇晴,她父母都没在家,大白猫在花下酣睡。听见我来了,她像燕儿似地从帘下飞出来;没顾得换鞋,脚下一双小绿拖鞋像两片嫩绿的叶儿。她喜欢得像清早的阳光,两腮像苹果比往常红了许多倍,似乎有两颗香红的心在脸上开了两个小井,溢着红润的胭脂像。那里她还梳着长黑辫。这一次,她就像一个小猫遇上了个好玩的伴儿;我一向不晓得她能这样活泼。在一同往屋中走的工夫,她的肩挨上了我的。我们都才17岁。我们都没说什么,可是4只眼彼此告诉我们是欣喜万分。我最爱看她家壁上那张工笔百鸟朝凤。这次,我的眼匀不出工夫来,我看着那双小绿拖鞋,她往后收了收脚,连耳根都有点红了,可是仍然笑着。我想问她的功课,没问;想问新生的小猫有全白的没有,没问;心中的问题多了,只是口被一种什么力量给封起来。我知道她也是如此,因为看见她的白润的脖儿直微微地动,似乎要将些不相干的言语咽下去,而真值得一说的又不好意思说。”
“她在临窗的一个小木凳上坐着,海棠花影在她半个脸上微动。她脸上的花影都被喜悦给浸渍得红艳了。她的两手交换着轻轻地摸小凳的沿,显着不耐烦,可是欢喜得不耐烦。最后,她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极不愿意而又不得不说,‘走吧!’我自己忘了自己,只看见,不是听见,两个什么字由她的口中出来?可是在心的深处猜对那两个字的意思,因为我也有点那样的关切。我的心不愿动,我的脑知道非走不可,我的眼相住了她的。她要低头,便又勇敢地抬起来,故意地,不怕地,羞而不肯低着,迎着我的眼,直到不约而同地垂下头去,又不约而同地抬起来,又那么看,心似乎已碰着心。”
“我走,极慢地,她送我到帘外,眼上蒙了一层露水,我走到二门,回了回头,她已赶到海棠花下。我像一个羽毛似的飘荡出去。”
这是老舍在回忆纯洁的初恋写在《微神》中的一段恋情。他曾经在心灵中燃起过爱情之火,犹如大海的波澜撞击着的爱恋心扉。然而,这初恋之火却以悲剧而告终。
因为那位姑娘是世家望族的千金,而老舍当时是女佣的儿子,地位悬殊。在那个社会,两人很难超越等级的界限以及世俗的偏见,只能把爱埋藏心里。后来,老舍在17岁当小学校长时,她曾经给他寄去一封贺信。信笺末尾印着一枝梅花,她无奈地注了一行字:不要回信。当时的老舍也没敢回信。可这封贺信,给老舍以爱的力量,他全身心地投入办学事业,企盼以最好的成绩作为给她的回信。
还有足以使他自慰的是,他始终没有听到她订婚的消息,而且老天爷又安排了一个和她能见面的机会。那年,老舍兼任了一个平民学校的校长,她担任着一点功课,这样老舍又可以天天见到她。她已经是个20多岁的大姑娘,天真活泼中又多了份稳重与尊严。每当老舍和她见面时,她似见不见地躲闪着。
以后,老舍当上了劝学员,那年政局不稳定,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人心浮动,危机四伏,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准备兴师北伐统一中国。早有野心的广东军阀陈炯明,趁孙中山立足广东未稳,突然发动政变,包围了广东革命政府所在地总统府,孙中山仓促登舰,出走上海。
此时,学务局里腐化、堕落、专靠吃老百姓的老爷们,以及尔虞我诈的复杂纠葛的人际关系,使老舍感到报国无门,理想破灭,困惑、消沉使他萎靡不振。
做母亲的总在为儿女操心。她看见儿子长大了,又有较体面的工作,按年龄也是该找媳妇的时候了。母亲看儿子整日情绪低落,又了解儿子的性格,不好意思把心思说出来,母亲就托人给老舍找起媳妇。正巧遇上一位容貌、品行都不错的姑娘,母亲当时定下这门亲事,还私下里给了定礼钱,只等和老儿子商量了。
老舍虽不住在家里,但经常回家探望母亲。每次回来,都买些点心,给母亲点钱生活用,才返回宿舍。那天老舍刚回到家,母亲着急地把儿子拉到身边说:“我给你找了姑娘,人不错,定礼钱也要了,约定下了这门亲事。”老舍一听急了,说:“娘,我不是小孩子,自己的事还是让我自己做主,这事我不能同意。”母亲想,一向孝顺的儿子,这次为什么不听她的话呢?是外面有人了,还是……母亲百思不解。于是,她说:“我这么大岁数,东跑西颠地张罗,好容易找到了可心的人家,定礼钱也交了,我怎么再去回绝人家。”母亲说着,便伤心地落下眼泪来。
老舍犯难起来,母亲是上岁数的人,一切都老眼光,老规矩,不知道年月不同了,婚姻观也变了。民国之年剪了辫子,五四运动又放了妇女的小脚。西洋人那套自由恋爱、婚姻自主的态度,也逐渐成了中国青年的“救世福音”。现代的青年不甘受“指腹为婚”、家长包办的婚姻,而是自由恋爱,反对旧式婚姻。一种新的伦理观念,一种新的意识正在向旧的传统观念冲击着。
后来,巴金写《家》、《春》、《秋》,曹禺写的《雷雨》、《北京人》等这些作品把当时青年的烦恼、痛苦、反抗、无畏、希望都反映出来,这些作品正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
老舍心中埋着爱的火焰,等待有朝一日,点燃那爱情之火。尽管他们之间有一堵不可逾越的高墙,然而老舍心里只有她。可是他怎么能和母亲去说呢,母亲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理解的。他痛苦极了,最后决定向三姐求援。三姐虽说是嫁出去的人,但在母亲眼里,三姐是她的好参谋,家里大事小情,母亲总是找三姐帮助处理。三姐是能人,手一份,嘴一份,既能干,又能说。给老舍说亲的事三姐听母亲提过,还知道那姑娘虽说是文盲,但长得很标致,但她没有想到让兄弟犯这么大难。还是三姐开通,在老舍的央求下,她答应去说服母亲。
过了两天,三姐回来了。一进屋,母亲说:“正好,有件事正想找你帮忙。”母亲将给老舍找媳妇,以及老舍如何不同意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向女儿诉着苦衷。三姐先是把弟弟教训一番说:“娘是好意,为了你操心,你不该辜负娘的一片心意。”然后,话锋一转说:“娘,庆春也不小了,在外面做事的人,什么能不明白,成家的事还是让他自己拿主意。强扭的瓜不甜,你也不能和人家过一辈子,人家相中的,一辈子幸福,人家不相中的,即使成了以后也过不好,你老还受埋怨。改日我和你去姑娘家赔个不是,把这事圆下来。”经三姐能言善辩的巧嘴一番进言,母亲点头退婚。老舍真是感谢三姐的善解人意,巧嘴灵舌。此后,母亲没有再提起让老舍娶亲的事。
老舍退掉了这桩亲事,那位刘小姐的倩影时刻在困扰着他。
后来,直到老舍从天津南开中学回到北京后,仍心事重重。
一天好朋友罗常培来看望老舍,看见他愁眉不展,就问他怎么了。老舍和常培是至交,无话不说,老舍就将心事告诉他。
原来,在没去南开教书前,他还敢经常去刘小姐处走动,可这次回来,他有些不敢冒昧前去,怕不成,再砸了锅。但见不到刘小姐心又七上八下,初恋的烈火燃烧着那滚烫的心。这时他借助于笔墨,倾吐内心的惆怅。他把自己的烦恼和苦闷写成词“春如旧,人空瘦……”准备寄给好友常培。正巧,没等寄走,常培来了。看见这悲悲切切的词,常培知道老舍已“病入膏肓”了。他决心自己替好友前去探路。
罗常培叩动了大门上的门环,没有动静,等了好一会,门开了,一个老妈子模样的人探出头来问:“您找谁?”“我找这房子里的主人,主人姓刘”。老妈子说:“他们不在了。”“不在了?”常培不解地问。老妈子垂下脸去说:“老爷出家了,小姐也跟着去修行了。”常培一听愣了,他真是想不通,为什么好好的日子不过,偏要去当和尚修行,真是不可思议。
老妈子把头偏回去,门关上了。常培慢慢地往回走,他真不知道怎样去告诉坐立不安、面容憔悴的老舍,怕他经受不了这个打击。但他心里想,瞒了一时,瞒不了一世,早晚也要知道,他硬着头皮把这不幸的消息告诉了老舍。
老舍听了,脑袋“嗡”地一下子大起来,他没有说话,默默地走出门。伤痛的心,使他回忆起那初恋的情景,竟不知不觉中走到了曾经初恋的地方。那院子里长着半人高的荒草,那株海棠树已经枯死了,墙上爬了许多蛛网。房子仍在,但旧了许多。
他痴痴地站在那儿许久许久,他留恋那曾经使他产生初恋的院落,他思念那院落里有位梳着长辫子的心爱的姑娘。
老舍很苦恼,后来朋友们曾善意地给他介绍女友,都被老舍一一谢绝了。初恋是青春的第一朵花,老舍很珍惜她。
1924年,老舍回国后,还始终想着那位刘小姐。他无从再打听到她的消息,但他常常在梦中忆起那小圆脸,眉清中带着媚意,身材不高,处处都那么柔软、轻巧,那一条又长又黑的发辫……她常常留在老舍的梦中。
老舍的初恋就像一场梦,梦曾经使他激动、狂喜,也曾给他遗憾与悲哀。他想,是什么值得那么痴情、留恋,是什么使他那样悲愤与遗憾。愤然中他拿起笔来写下了《微神》。
虽然老舍的初恋之梦破灭了,然而,他是幸运的,几年后,一位才女闯进了他的生活。她是著名画家胡洁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