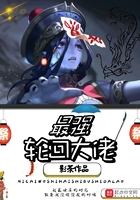无穷无尽的杏花,白的粉的,仿佛融成一大团粉白色的云朵,从白雾之中伸了出来。
点点杏花花瓣,像是细雨,又像是玉屑,又像是碎雪,一点点落到了符西和老七身上。
符西屏息,仔细盯着戏台子。宋季图、徐兄还有那个程侍郎,全部消失在那扇禁闭的门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符西也没有再听到他们的声响。
“怎么冒出这个东西来?”符西抬头看了看那粉白花团,说道。
“杏花和金榜有关系吗?”老七拍飞浮在半空的杏花花瓣,似乎很讨厌这东西。
“杏花,金榜?”符西回想了一下,摇了摇头,说道:“印象中,它们之间没什么关系啊,也没有这两个相关的典故?”
“不过……”符西咬了咬唇,突然想到了什么。
杏花、金榜、会试……对了,会试通常是在二月进行,而杏花也在这个时候开花的!
那这杏花,说不定和宋季图他们的会试有关系?
老七听了符西对于杏花的猜测,看了看四周,似乎也没有更多的线索了,就说道:“那走吧,咱们跟着花走。”
“好……”符西话音未落,她只感到一阵撼天动地的震动,猛地从脚下传来,她一时没站稳,差点直接坐到了地上。
想象中的疼痛并没有发生,她只觉得自己身体被稳稳地扶住了,她回头,是老七在旁边扶住了她。她能听到老七有点急促的呼吸声,他低声问:“没事吧?”
“没事……”符西连忙借着老七的力,自己站稳了,但她只感觉自己脚下的地面,仿佛变成了一张薄纸,随时可能会破损下沉,又可能被揉成其他难以站立的形状。她微微抬头,就看黑白巨石,如同一颗颗陨石,不断地从高空落下,直直地砸向地面,带起了地震一般的震动。
符西心里只觉得不对劲,这些黑白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它们再这样砸下去,这个空间会不会崩裂倒塌?要是真的倒塌了会怎么样?她和老七会被埋在这里吗,还是掉出这个空间,能顺利回去?之前在夜宴图里,要是没有魏紫来救人,说不准她和甄老板就被关在那化境里一辈子了。她也从来没想过要是一个化境崩塌了,被困在里面的外人,到底会是怎样的结果。
一切都是未知数。
符西握了握拳,感觉到自己手心里都是冷汗,指尖磕到了手心,痛觉和不适感反而让她清醒了些。她抬头,看着那仿佛渐渐飘远的杏花树枝,对老七说道:“我们要快点了。”
符西和老七穿过了白色烟雾,在那棵巨大无比的杏花树前停了下来。
但奇怪的是,这次没有出现戏台,而是出现了一排排平房一般的建筑。
老七让符西留在他身后,自己则轻轻一跃,如同一只白鸟,悄无声息地划过夜幕,潇洒又干净利落地落到了那排建筑顶上。
他快速查看完每排建筑,就回来找符西了。
“里面有人。”老七说。
“有人?什么人?”符西不由有点紧张。
“哪认得出来,”老七回头看了一眼,“但都在写东西,好像是考生。”
“考生?”符西又看了一眼那些建筑。她发现那一长条状的房子,被隔成一个个小的隔间,那隔间也就只能容纳一人,看起来就跟轿子一样大小。有模糊的人影坐在里面,确实好像在写着什么。
符西恍然大悟,开口说道,“哦,我懂了。”
这些建筑,其实就是明朝会试时的考试场所,叫做号舍。
考生看了号舍之后,就要住在里面了。号舍两侧的墙壁,各有上下两道凹槽,可以搁两块木板在上面。考生答题、饮食时,就把两块木板,一高一低地放着,当做简易的桌子和板凳。到了晚上考生想要休息,则可以把两块木板放平,这就有了简易的床铺。
而号舍里的规矩非常多。比如考生的饮食喝水,是由官府的号军来提供,一天两次。考生不能随便离开这里,如今正是二月,天寒地冻的,号舍根本没办法遮风避雨,对于那些考生来说,答题本来就是一件极其煎熬的事情。
符西看了一圈,找寻着一个人的身影。
这一路以来,符西和老七看到的,都是和宋季图有关的故事,那宋季图应该就在这里面才对。
这里大概就是宋季图那年的会试现场吧,弘治十二年的那场会试……
符西和老七顺着一排排号舍找着,看到一个个面目模糊的考生。他们都停下了笔,搔首挠腮,似乎都被考题给难住了。
这时候老七吹了声口哨,示意符西过去,符西连忙跟了过去,探头一看,终于最里面的一个号舍里,找到了宋季图。
符西和老七躲在墙角,观察着他。此时宋季图一身儒生打扮,他一手拿着考卷,一手提着笔,眉头紧锁,似乎也被这会试的题目给难住了。
“又是个写不出题的。”老七嘲道。
“……”符西哭笑不得,说道,“说不定这次考试就是特别难呢。”
“一个字都没写,”老七瞥了眼,淡淡说,“看你们把他吹上天了,不懂的人还以为文曲星又投胎了。”
符西差点被老七逗得破了功,心想怎么以前就没发现,这只猫还挺会损人的呢。
但符西转念一想……如果宋季图答不出题,那不正是说明了,在这场弘治十二年的会试里,宋季图并没有拿到泄露的试题吗?
历史上的那个舞弊案,会不会藏着什么隐情?
符西盯着宋季图,宋季图又看向试题别的地方,似乎在看另一道题。
宋季图将试题都看了一边,又将试题和笔放了下来。他举目远望,无意识地盯着茫茫夜色。他脸上没有半分喜色,倒有着几分怅然若失。
一点亮光闪过他的眼睛,符西这才注意到,他的眼角有了一点泪意。
符西不由困惑起来,难道宋季图真的被这些题难住了,而历史上的那桩舞弊案,实际上错怪他了?
这时,宋季图抬手抹掉了眼里的泪意,那点泪水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他对着自己的手哈了哈气,重新拿起了笔。
他低下头,露出了淡淡的、不屑的微笑。
宋季图嘴巴动了动,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要将自己的雄心壮志说给这严寒的天地听。
“娘亲,这次我不会空空而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