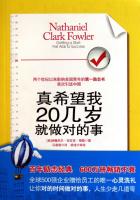女人推开了王世贵,“滚你娘的,我可没这个兴致,娃儿还在家里,等着吃奶呢。”
女人扭着蛇一样的腰,急匆匆走了。
王世贵拿起大草帽,扣在头上,哼了一声说:“别看你们闹得欢,老子才是如来佛!”
天还未亮,草根张骑上车子,往村外走。
到了村口,正碰上刘婆子,挎了一大筐子豆角,往村里走。
“刘奶奶,起这么早,又没睡好啊?”
“哎哟,友根,吃了你那个药,早早就睡着了。”
刘婆子抓了一捆豆角,放进了他的车筐里。
“我要去乡里,不能拿这个。”
草根张把豆角拿出来,放回到了筐子里。
他看到筐子里,有几个老丝瓜,“刘奶奶,这个给我吧?”
“这个有什么用,老得不能吃了,你愿要,都拿着吧。”
拿上了老丝瓜,草根张骑车子要走。
刘婆子拉住了他,“友根啊,你给我的什么药啊?真管用,就是又腥又臭的。”
“刘奶奶,你先放开手,”草根张蹬起了车子,扭回头来说:“那是夜猫子,拉的屎!”
“你个小王八羔子,竟然让我吃屎!”
刘婆子对着草根张的背影,跳着脚的骂了半天。
骂累了,自己又笑了,“吃屎就吃屎吧,反正是真好使。”
一大早,李德才开着车,去他的工程队上班。
他忽然看到草根张,在大门口来回溜达,像在等什么人。
他把车停到了他跟前,“小兄弟,你来找谁啊?”
“找你啊!”
“找我好,我正要去找你,你自己送上门来了。”
李德才把他让进了办公室,“你先说,找我什么事?”
“李叔,我想在你这里,找个活儿干。”
李德才吃惊地瞪大了眼,“我这儿,全是些粗老笨重的活儿!”
“有个活儿干就行,”草根张咬咬牙,“他们不让我给人看病了。”
李德才听草根张说完,长叹了一声,“他们这些人,什么手续都有,合理合法,就是治不了人的病!”
草根张低下了头,“我离会治病,也还远着呢。”
“那也比他们强多了,”他递给草根张一杯茶“我家娘们儿,不听你的,现在后悔了,你跟我去看看吧。”
李德才老婆说,现在又添了个新毛病,热得心烦,却不出汗。
草根张说:“你补成实症了,必须用大黄。”
“大黄就大黄吧,我听你的。”
草根张打开背来的包,拿出了一个袋子,里面装的,全是老丝瓜。
“用完大黄,再用这个煮水喝,搓澡也用它,身上的疙瘩,就会消下去。”
“真的?”
李德才不耐烦了,“什么真的假的,信这小兄弟的,肯定没有错!”
李德才承包的工地上,草根张推着小车,往吊车上运水泥浆。
李德才走过来说:“干不了,别硬撑,你在这里,管管材料就行。”
草根张正正安全帽,“李叔,我可不是来吃闲饭的。”
李德才拍拍他的肩,默默走开了。
上面的人,又嗷嗷喊着催了。草根张架起小车,往一个小土坡上冲。
一个穿长裙的姑娘,走了过来,正好挡在了小土坡中间。
“闪开,”草根张喊着,脚步却没有停下来。
姑娘躲到了一边,惊喜地叫道:“张友根,你怎么在这里?”
草根张没有停,把小车推进了铁笼里,才回过头来。
竟然是李春萍,在笑吟吟地看着他。
“你怎么跑这里来了?”草根张抺了把脸上的汗。
“我来找我叔,家里出了点事,”她用探询的目光,上下打量着他,“你这是……”
草根张又擦了一把脸上的汗,“我到这里来干活了。”
“你不是在村里当医生吗?”
“不让干了,说我无证,是非法行医,”草根张苦笑了下。
“萍萍,你怎么在这里?”李德才从里面走了出来。
“我爸受伤了,我妈不在家,”李春萍焦急地看着李德才。
李春萍她爸,从锅炉房往里提开水,暖瓶突然炸了,一壶开水,全部洒到了脚面上。
鞋袜没及时脱下来,烫了个结结实实。
去医院一查,说是三度烫伤,得做个大手术,把死皮坏肉都切掉,以后还得植皮。
“医生还说了,要是感染了,就得截肢,”李春萍看着她叔,眼泪涌了出来。
“他们治不了病,就会吓唬人!”李德才拍了下桌子,“还得找草根张,他肯定有办法。”
李德才走出工棚,叫住了草根张。
草根张正架着小车,“上面催着要呢,我先把这车送上去。”
李德才招招手,把施工员叫了过来,“你先顶会班,友根,你跟我来。”
听李德才说完,草根张笑了,“怎么这么巧,我在家时,刚配好了这种药,来找你时,还带了一瓶。”
“用了你的药,不用动手术了吧?”李春萍问。
“什么都不用,”草根张很自信地说。
李春萍高兴地说:“那可太好了,我爸还担心截肢呢。”
李德才开着车,拉着草根张和李春萍,直奔县城。
李春萍她爸叫李德勤,原先在乡里工作,现在调到了县里。
看着土里土气的草根张,拿着个玻璃瓶子,李德勤眉头拧成了疙瘩。
“老三,叫你来,是和我去住院的,你领这么个毛头小子,来干什么?”
烫伤的巨烈疼痛,让他不时地吸凉气,头上直冒冷汗。
李德才说:“二哥,先让这位小兄弟,给你抹点药,试试嘛。”
李春萍也帮着说:“就是啊,爸,你不试,怎么知道,人家的药好不好用。”
草根张蘸了点药膏,抹在了李德勤的脚面上。
他的眉头,立即舒展开了,“凉嗖嗖的,感觉挺好。”
草根张忍住笑,继续抹药。
整个脚面上的皮,都烫熟了,露着里面的肉。
他小心地涂抹着,用药膏覆盖了整个脚面。
李德勤绷紧的脸,舒谖下来,“真是神了,怎么一抹上,就不疼了呢?”
李春萍笑着说:“人家可是大名鼎鼎,神医草根张呢!”
“你不会加了止疼药吧?”李德勤问。
草根张拿了些纸,垫在了李德勤脚跟下,“李叔,这药好不好,你明天就知道了。”
“如果你能给我治好了,我给你送个大匾,题上我的字。”
李德勤的书法,在县里很有些名气。
草根张却笑着说:“我不想要匾,要是给我发个行医执照,就太好了。”
李德勤大吃一惊,“怎么,你还是无李德才发火了,“二哥,你们这些人,真是迂腐透顶!”
“老三,你在瞎胡闹,怎么还振振有词?”
李春萍赶紧打圆场,“反正我同学说了,明天就会见效果,你们不要吵了。”
“见什么效果,如果他给我治坏了,怎么办?”李德勤恼怒地问。
草根张说:“李叔,你这脚,包在我身上。”
李德才叹口气,“这给人治病,还得豁出身家性命!”
李春萍也说:“就是啊,爸,总不能让我同学,赔你一只脚吧?”
李德勤心怀忐忑,到了后半夜,才迷迷糊糊睡去。
前两天,伤口特别疼,像在剜肉,他已经两天没有睡觉了。
现在不疼了,李德勤睡得特别沉,天光大亮时,他才睁开了眼。
他坐了起来,掀开了脚上的纱布,吓得浑身一哆嗦。
脚背上的死皮烂肉,一古脑儿地拱了出来,似掉非掉的样子。
“萍萍,你快来看,我的脚,是不是要烂掉了?”
李春萍跑过来,,心里也“咯噔”一下子。
“爸,你觉得疼吗?”
“一点不疼啊……”
“要是烂了的话,应该会很疼吧?”
“那小子,给我上过止疼药啊!”
李春萍捂着嘴笑了,“再厉害的止疼药,也撑不了这么久啊!”
外面传来了敲门声。李春萍跑过去,打开了门。
李德才领着草根张,急匆匆走了进来。
“友根,你快来看看,我爸的脚,这是怎么了?”
草根张掀起纱布,高兴地说:“这样就好了,不用动手术了。”
草根张拿起镊子,要清理掉死皮烂肉,重新上药。
李德勤伸手拦住了他,“你不要动了,咱们先去医院吧,让医生看看,再说。”
县医院烧烫伤科门诊里,坐诊医生看着李德勤的脚,吃惊的问:“你用了什么药,这么厉害?”
李德勤一脸紧张,“怎么了,大夫,是不是要截肢啊?”
“截什么肢啊,连手术都不用做了!”医生把手里的笔,扔在了桌子上。
李德勤面如土色,“啊?难道我得了败血症,无药可救了?”
医生笑了,“领导啊,您懂得还挺多,”他拿起镊子,把死皮烂肉夹了下来,“做手术,就是为了清理这些,现在自己都出来了。”
李德勤长长舒了口气,掏出纸巾,擦了擦脸上的汗。
医生说:“动手术清这些死皮烂肉,不能麻醉,只这一关,就够您受的。”
“我还用住院吗?”李德勤问医生。
“您愿住也行,就是打打消炎针,预防感染,”医生用棉球蘸了点药,看了看说,“不过,说句良心话,我劝您,还是继续用这种药。”
李德勤家里,草根张正在上药,李德勤忽然问:“我这脚要是好了,得留个坑一样的疤吗?”
“用了我这药,皮肉都会重新长出来,不会留下任何疤痕。”
李德勤瞪着眼,下巴都快掉下来了。
“你小小年纪,还真敢吹牛!”
县医院的医生告诉李德勤,伤口恢复后,需要植皮。
植皮为保证成活,也是不能上麻药的,他正为过这关发愁呢。
草根张笑了,“连个行医执照,我也没有呢,还敢吹什么牛?”
李春萍说:“爸,卫校里开了个乡医培训班,毕业后,就是正式的乡村医生了。”
李德勤犹犹豫豫地说:“那个……要乡里和村里,推荐才行。”
草根张说:“那我肯定没戏,我们村里,肯定推荐王富强。”
“王富强是谁?”李德勤问。
“村长的儿子,一个不学无术的无赖,”李春萍翘着小鼻子说。
李德才沉不住气了,“二哥,我这小兄弟,给你治好了脚,你必须把他送进卫校。”
“我要是办不了呢?”李德勤皱着眉头问。
草根张正上看药,李德才拉住了他,“咱们走,不和这粘糊人打交道!”
李春萍推了李德勤一把,“爸,你这人,真死板!”
李德勤笑了,“其实,我给校长写个纸条,这事儿就办了。”
李德才撒开了草根张的手,“你早说啊,二哥,你这文化人,就是拐孤。”
“我写了纸条,就算我推荐的,可不能打了我的脸,”李德勤顿了下,“还有一样,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毕业后,必须回乡村工作。”
李春萍高兴地说:“友根,咱们又是同学了。”
草根张拿起纱布,盖住了李德勤的脚。
他看了眼李春萍说:“只是同校,不是同班了。”
李春萍对她爸说:“我也转到乡医培训班吧,当个赤脚医生,也不错。”
李德勤训斥她:“你别瞎胡闹,等你毕业了,要去县医院上班呢。”
草根张骑着车子,进了村。他拐了个弯,先去了王世贵家。
王世贵歪在躺椅里,正和儿媳妇,有一搭没一搭地闲扯。
“哟,你小子干啥去了,这么些日子了,连个影儿也不见,”王世贵坐直了身子,转过头来问。
草根张从怀里掏出张纸,展开后,递给了王世贵,“村长,给盖个章。”
王世贵接过来,看了看,诧异地问:“你小子也上乡医班了,不会把富强顶了吧?”
王富强正在看武侠剧,闻言也跑了过来。
他从他爹手里拿过来,反来覆去地看,“假的吧?”王富强酸溜溜地说。
他把自己的通知书,拿了出来,对了对,除了被录取者姓名,其它的都一样。
“怎么我到哪里,都甩不掉你这丧门星啊?”王富强不满地说。
王世贵阴阳怪气地问:“张友根,你两个膀子扛着个头,就这么空着手,这个章,我怎么盖?”
草根张抱着膀说:“村长,你以后再不能动了,千万别找我。”
王世贵“呲”地一声笑了,“我逗你玩呢,你小子还拿棒槌当针了。”
他拧开了锁,拉开抽屉,拿出印章,重重盖在了通知书上。
王世贵心想:“不拿住这小子点把柄,以后还真治不了他了。”
王富强媳妇瞪着一双杏核眼,上下打量着草根张,“你就是神医草根张啊,长得还挺帅。”
“他帅个屁,在乡中学时,就数他长得丑,”王富强不屑地说。
“富强,卫校可不是乡中学了,”草根张瞅了眼王富强,“咱们骑驴看唱本……”
王富强点上了一支烟,“走到哪里,老子都姓王。”
王世贵乐呵呵地点着头,心说:“这才是我儿子!”
“玉皇大帝还姓张呢!”草根张收起了通知书,转身就往外走。
迎头碰上了王世禄,他一把拉住了草根张,惊喜地说:“兄弟,你可回来了,我有个事儿,正想找你呢!”
证行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