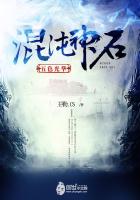草根张从车上下来,校长就在楼上看到了,但他不知道,汪满金把他叫住了,更不知道,两人在一起,嘀咕了些什么。
本来只想把汪满金稳住,现在叫上草根张,一箭双睢,岂不更好。
汪满金先进去了,草根张等了一会,才进了七号房间。
校长说:“这么巧啊,友根,你也到这里来,正好我和你们汪老师,要说些你们乡医班的事,你也来听听。”
“我只能听听吗,校长?”草根张笑着问。
“你给学校捐了钱,还做了那么多好事,当然也有发言权,”校长说。
汪满金接过话去,“咱们这期乡医班,学员很优秀。学校里决定,友根你留校任教。另外呢,还要保送两个学员,去省医学院进修。”
校长清清嗓子,“友根啊,你都留校任教了,就不用再去医学院进修了。”
“校长,我非常想上大学呀,”草根张很坚定的说。
“友根啊,你现在的水平,可远远超过大学生了,给个博士都不过分,”校长夸张地说。
“有水平,也得有文凭啊,”汪满金低头吃着菜,不忘补一句。
“对有真本事的人来说,文凭一文不值,”校长瞪一眼汪满金。但汪满金低着头,根本不看他。
草根张想起了吴运昌,为啥没收他的草药,“校长,没有文凭,水平再高,人家不让发挥啊,我还是先上大学吧。”
校长又看汪满金,“汪老师,学校里现在就能给友根下聘书。”
汪满金提醒草根张,“聘书不符合规定,随时可以收回来。”
校长的胖脸上,马上下了霜,“汪老师,这顿饭你请吧。”
汪满金摸摸口袋,“今天我带着钱了。”
草根张在乡医班里,学习成绩第一名,综合测评第一名。这是梆梆硬的硬指标,他只要不说让,谁也不敢抢他的保送名额。
而第二名呢,被高雅牢牢霸占了,而且他爹还是乡长,这个乡长,和县长还很铁,更没人敢打他的歪主意。
结账的时候,草根张要替汪满金付,被汪满金坚决拒绝了。他说今天这顿饭,吃得心情特别舒畅,不让他付账,会影响他的好心情。
送走了校长和汪满金,草根张去找他们三个。
三个人已经吃完了饭,正在喝茶等他。高雄已打坐入定,开始练功了。
草根张把云中李跑到青峰观的事儿,告诉了吴大和吴二。
吴大皱起了眉,“他肯定还会去捣乱。”
吴二说:“我们不能等着他去。”
“难道我们还要去请他?”草根张笑着问。
吴大和吴二对视一眼,“咱得主动出击,现在就去收拾他。”
“怎么收拾啊,总得找个茬吧?”高雅定不住了,睁开了眼问。
“咱们现在就去,先下手为强,找什么茬儿,路上寻思,”吴二说着,站起来就往外走。
几个人跟着吴二,上了车,直奔柳林苑去。
到了护城河边上,后面追上来一辆车,在后面一个劲儿摁喇叭。
“他娘的,急着去医院嘛,”吴二把车,往边上靠了靠。
后面上来的车,却不急着超过去,与他们的车,并行起来。车窗里还伸出一只手,示意他们停下。
吴二扭头看了眼,竟然是活阎王,“老阎,你想干啥?”
“你先停下车,”活阎王冲吴二喊,他的车超了过去,在前边停了下来。
吴二把车停了下来,但没有下车。活阎王跳下车,走了过来,“你们干啥去啊?”
吴二凶巴巴瞪了眼活阎王,“老阎,别以为你有俩臭钱,就能管天管地管空气!”
活阎王却嘿嘿笑了,“兄弟,我老远就瞅见你的车了,觉得亲切,才叫住你了。”
“我有急事,没空和你扯咸淡,”吴二打着了火。
活阎王却把手伸进来,拧了下车钥匙,熄了火,“你们急啦啦跑这儿来,是找云大师吧?”
吴二冷笑,“狗屁大师,他就是坨屎!”
吴大早不耐烦了,冷冷地看着活阎王,“你还有事吗?”
“你们要找云大师,我可以领你们进去,”活阎王看看吴二,“你撞坏的大门,我刚给他修好。”
草根张在后面说:“你请前边带路吧。”
吴二却说:“老阎,你不带路,我今天还要把门撞开。”
活阎王拍拍吴二的肩,“兄弟,咱都是文明人,不能老想着动粗。”
草根张再也忍不住,哈哈笑起来,“老阎,你天天前呼后拥,手底下那些人,都是耍笔杆子的?”
到了柳林苑大门外,大家下了车。
活阎王今天就带了一个司机来,还没有下车。他拿出个卡,在大门上刷了下,大门就开了。
他把四个人,领到了讲堂,“你们在这里等一下,我去请大师过来。”
活阎王的面子果然大,时间不长,云中李穿着个肥大的袍子,像个游魂一样,飘了进来。
高雅注意到,他走路的时候,没有一点声音。
云中李坐在了讲台上,居高临下,看着他们,“我潜心修炼,不问世间俗事,你们来找我,要干什么?”
吴大跳起来,一把揪住了他的胡子,“那你跑到青峰观,去耍什么流氓?”
“手还不干净呢,”草根张在旁边说。
活阎王跑上来,拉开了吴大的手,“别动武把抄啊,我人可比你们多。”
云中李故作沉稳,坐着没动,手脚却都在哆嗦。
高雅小声跟草根张说:“这是什么大师,怎么看着,像个僵尸啊。”他装作小声,却故意让云中李都听见。
云中李腮帮子哆嗦几下,眼里冒出了小火苗。
“阎先生,你怎么让我来,见这些恶俗的人?”云中李站了起来,往门口走去。
草根张抓住了他的大袍子,“李云中,你给我坐下。”
云中李一脸厌恶的表情,“拿开你的脏手。”他手轻轻一抬,看似甩袖子,两个手指头,却戳向草根张肩部。
草根张用力扯他的袍子,手指头戳偏了,袍子也被撕裂了。
云中李另一只手跟上来,戳向草根张咽喉。
草根张手一抬,两个人的手,缠在了一起。
云中李的手,像枯树枝,却带着很沉的力道。草根张想推开,却推不动。云中李要往前进,也是进不了。
两个人僵持了几秒钟,立即分开了。云中李垂下了手,看看撕裂的袍子,“你这成什么体统?”
草根张松开了袍子,呵呵一笑,“我想看看里面,是什么货色。”
“粗鲁,”云中李整理下袍子,重新坐下了。
活阎王看傻了眼,两个人看似极平常的动作,似乎有不少门道。他想:“这两个人,我谁也不能得罪,哪个都得利用。”
“说吧,你们到底想干啥?”云中李捋了捋胡子。
“你说井水不犯河水,却到处兴风作浪,”草根张说,“我想和你比试比试,你要输了,就别到处去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