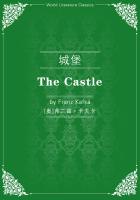观音懒懒地舒展着身体,摊在床上不愿起身,可今日还没有沐浴呢,淋了雨的头发总是有股怪味儿,要不是白天太累,早就应该洗干净。观音越想越恶心,只得爬起来沐浴。
阿嬷和春榭一起准备着浴桶,兰亭带着铜雀台一起更换枕席,打整床铺。新近服侍观音的四个大婢女,除了春榭,都是契丹人。观音觉得春榭的名字很好听,就依着她的名字,给剩下的三个婢女取了汉名。兰亭和朱楼倒还好,铜雀台出自舅帐,是真的人如其名,身量高大,能挑能扛,骑马射箭不在话下,做婢女可惜了了,应该做个侍从才不算大材小用。
观音除去衣衫,跨进桶里,她深吸一口气,把头浸入水中,在水下尝试睁开眼来吐泡泡。突然一种奇怪的感觉袭来,她好像又回到了那个梦里,那个在水中挣扎的梦。观音一时慌了神儿,急忙从水里伸出头,扶住桶沿连连咳嗽。
在旁伺候的春榭和阿嬷连忙察看,观音摆了摆手,边咳嗽边道“没事儿”。
“娘娘怎么样?!春榭快请汉医过来!”
“别别别!”观音急忙叫住了春榭,“我没事儿,就是不小心呛了一下。”
阿嬷用毛巾摩挲着观音的后背,帮她顺着气,渐渐地,观音的呼吸回复平稳,春榭奉上一盏热水,观音便慢慢喝起来。
“如果不是邢氏占了金汤,娘娘用得着在房里沐浴吗?”春榭愤愤不平道。
阿嬷警告地剜了她一眼,随后审慎地观察观音的表情。幸运的是,观音并未受春榭影响,她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手中的热水上,仿佛那是最珍贵的葡萄美酒一样。
春榭不敢再抱怨,将玻璃碗里的澡豆倒进浴桶,又拿出香宫皂帮观音洗头发。
“桂花香气,金秋十月一样。”观音一边闭着眼睛,一边用手搓洗发梢,“阿榭,你退下歇着去吧,我自己能行。”
“娘娘,我……”
“听话,你先退下。”阿嬷说着,将春榭推着出去了,“娘娘,您还好吧?春榭这孩子就是太冒失了。”
“年轻,自然气盛。”观音轻轻笑了笑:“您下去也不要责备她了。”
“娘娘放心,只是,如果娘娘心里有什么话,只管说给我听。”
“是,您放心。”观音说着,自己抓着头皮,把头发抓得像一团打湿的抹布,阿嬷赶忙上前服侍着,才让这个澡有条不紊地洗完。
春榭被连赶带哄地轰出来,心里对邢念念更添了一分怒气。
她溜达到营地外的无人之处,怒火中烧地嘀咕道:“明明是个有夫之妇,行寡廉鲜耻之事,上了龙床就蹬鼻子上脸,一味地嚣张跋扈,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我呸!”
骂人还不能放声,春榭真觉得憋屈。
连我都觉得憋屈,真不知娘娘得是个什么样子!
春榭孤零零地坐在草地上,呆呆地看着月亮。
雨后皓月当空,皎洁的光芒洒遍山谷和旷野。
忽然一个影子越过春榭的头顶,投射在她的面前。
春榭转过头,来人是福鲁,洪基的侍从,殿前都点检司右卫将军,负责捺钵的护卫工作。
福鲁温和地笑向她道:“你就这么坐在地上啊,不怕雨水和露水沾湿衣裙吗?”
春榭瞧见他气就不打一处来,懒得理他,便随口胡诌:“那不正好?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这才舒坦。”
“姑娘倒有雅趣,只不过兴致不高啊!”福鲁笑眯眯地打趣道。
“婢子闲人一个,不比福将军,不过今日将军怎么得闲,不用随侍陛下和那艳绝六宫的邢娘子吗?”
福鲁听出了话里夹的枪带的棒,无奈地笑了:“春榭姑娘可是皇后娘娘眼前最得力的,哪里就是闲人了。”随即正了正神色,认真地说:“姑娘若有烦心事,我愿意倾听并尽力相助。”
这句话说得诚意十足,春榭也不好再摆脸色了,斗鸡一样的火力顿时没了八成,败下阵来:
“其实,我说了也没什么意义。”
“总比憋在心里强。”
“这倒是……”春榭顿了顿:“将军大概也知道了吧,陛下和皇后娘娘日渐疏离,大约都是因为那邢娘子。”
福鲁欲言又止,轻轻点了点头。
“近日陛下又传了口谕,除邢娘子以外,其他人一律不许再踏足金汤。听闻陛下三不五时便携了邢娘子去金汤沐浴,将军知道的,金汤养颜解乏,从前皇后娘娘最喜欢了,如今夫君被人抢去,一应衣食供应也要大打折扣,邢娘子倒是人面桃花,春风得意。现下她连个名分都没有,就已经时常踩估娘娘了,若有朝一日蒙获圣恩,抬举了她,皇后娘娘可该如何自处呢?”
春榭说着,便因着急生气掉下泪来。
福鲁看到她落泪,一时间慌了手脚,束手无策,想帮她拭泪,可他一介武夫,身上连个帕子也没有,只得结结巴巴地哄她。
春榭看着他慌慌张张的样子,又忍不住笑出声来,赶忙说道:
“不好意思,吓到你了。今日娘娘沐浴,不小心呛了水,我一时生气,才这样情绪化的。”
“没事儿没事儿。”福鲁边说着,边不易察觉地舒了一口气,随即打趣道:“若刚才恰巧经过个人,肯定以为我欺负你了。”
春榭本来要掏出帕子擦眼泪,听到这话,便改用帕子捂着嘴,好控制住自己不要笑得太夸张。
“你笑了我可就放心了。”福鲁说着,咧开嘴也笑了起来,憨态可掬:“刚才想帮你擦擦眼泪,可惜我身上没有手帕。”话音刚落,便把眼神转移到春榭的手帕上。
春榭有些害羞:“我这条脏了,赶明儿我绣一条新的给你。”
“那怎么好意思呀。”
“你别多想,没别的意思,就当谢谢你今晚听我唠叨。”
“哈哈,姑娘真是客气了,那我也回敬你一份礼物,咱们礼尚往来。”
春榭好奇地睁大了眼睛,急忙追问什么礼物。
福鲁却不肯直说,只说道:“必定解你燃眉之急。”
洪基到皇后帐的时候,观音主仆已经全然睡下了。穿越几层戍卫,他眼都不眨一下,可真的到了寝帐门口,他却踌躇了。
守夜的侍婢不知洪基是何意思,面面相觑,这门帘是掀还是不掀?
尽管福鲁向他描述得要多严重有多严重,洪基心里还是有数,观音必定无碍,否则上上下下早就乱了阵脚。他暗自把福鲁的夸大其词当作了过来探望的理由,可当他站在寝帐门口,无名火却再度涌上心头。
洪基挣扎了半天,终于下定决心,箭已离弦,就长驱直入吧。
他吩咐下人不必叫醒观音,自个儿踱了进去,却在月光映照下的雪青色床帐前再度停下了脚步。
他爱着的那个家伙,就在一步之遥的地方,在那帐子里,浑然不知地睡着,他却百爪挠心,不得安宁。洪基按下心头的怒火,万般无奈地苦笑了一下。
他缓缓伸出手,拨开帐子,借着四角的夜光珠,望向观音熟睡的面容。
二十多年了,岁月如飞刀,刀刀催人老。观音不似从前那样年轻,熟睡的面容也添了几分安逸慈和。
洪基甚至不记得上一次看着她这样安睡是何时了,似乎每一次见面,两人必定剑拔弩张。
还是睡着了好,他心想,睡着了就不会说伤人的话,也不必看伤心的人。
洪基将落寞的视线游移到象牙床的其他部分,夜光珠的辉光里,他突然留意到,自己的枕衾已然消失不见,好不容易平复下来的心情,又腾地一下燃起怒火。
洪基拂袖而去,随着他的离开吹起的一阵风,掀开了床帐。
观音睁开眼睛,半抬起头望向他消失的门口,所幸再无眼泪划过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