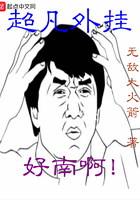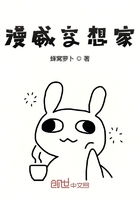打人事件后,郭德纲将此事编成段子,对记者破口大骂,明确表示:“所以说啊,有时候,这记者啊,还不如妓女。我一直在想,这妓女在红灯区活动,记者呢在绿灯区,想去哪儿就去哪儿。”郭德纲又在其博客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有药也不给你吃》的文章,用充满火药味的言辞首次正面回应了此次事件,力挺徒弟为“民族英雄”,这无疑是一种护犊子行为。
艺人与媒体斗,尤其是在自己的小辫子被媒体攥在手中时,大多都结局惨淡。一方面,媒体人多势众,得罪不起。媒体的威力不可小视,可以在一夜之间捧红一个人,也可以在一夜之间毁了一个人。与媒体结仇,最终吃亏的还是自己;另一方面,有的时候自己也不完完全全清白。
郭德纲的这个教训,也值得企业借鉴。
2006年,沸沸扬扬的富士康“血汗工厂”事件,也让富士康实实在在尝到了得罪媒体要吃亏的滋味。
2006年6月14日,向来被鲜花和掌声包围的富士康,突然深陷传媒风暴。英国《星期日邮报》惊爆内幕:深圳富士康——苹果的代工厂为“血汗工厂”。
《星期日邮报》的犀利报道,引起国内媒体的连锁反应。《第一财经日报》嗅觉最为灵敏,首先抓住这个题材,顺藤摸瓜进入iPod之城。2006年6月15日,《第一财经日报》刊发记者王佑的文章《员工揭富士康血汗工厂内幕:机器罚你站12小时》再一次掀起国内关注“富士康”的热浪,富士康被牢牢打上“血汗工厂”的烙印。而让该记者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样一篇揭露内幕的文章让他惹上了一桩天大的官司。
对于国内舆论,《星期日邮报》只是导火线,《第一财经日报》则是瞬间引爆的本土炸弹。公众和媒体对富士康的关注不断升级,网上热议不断,不少网民跟风叫嚷,甚至已经开始用脚投票,富士康的危机在聊天室内、QQ群里、口耳相传中迅速蔓延。面对突如其来的负面报道,富士康公司统一口径。富士康子公司深圳龙华基地外联部对外宣称:“富士康完全按照深圳劳动监管部门要求用工,深圳市劳动监管局可以到工厂去检查。”富士康母公司台湾鸿海集团召开记者发布会,矢口否认其子公司富士康有“血汗”嫌疑,而鸿海集团更是一向合法经营的“良民”。
但是“良民”所言无人相信。没有权威调查依据的保驾护航,富士康强硬的言论只能被关注这件事情的媒体和公众视为强出头,是向他们的知情权叫板。这种危机处理模式强硬而幼稚,显然不可取。
危机管理界有种说法,“坏消息在你的手中握得越久,情况就越糟糕”。富士康不提供信息,中国的媒体只能自力更生,发现真相。6月22日,《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王佑二进iPod之城,“血汗工厂”在一名离职女工的讲述中,再次浮出水面,使公众一览富士康员工的艰辛与无奈,公众对此气愤不已。
在媒体的进一步描述中,富士康强词夺理的嘴脸深入人心,企业形象一败涂地。依然保持强硬态度的富士康为了维护自身形象,只能南辕北辙地一步步走向媒体和公众的对立面。
在整个“血汗工厂”事件中,富士康这个危机主角更像是一个盲目的冲锋者,尽显幼稚粗鲁。它不但气势汹汹、目中无人,继而还发展到漠视公众感受,恃强凌弱。
2007年7月10日,台湾鸿海集团的旗下公司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以名誉侵权纠纷为由,向《第一财经日报》编委翁宝、记者王佑提出总额为人民币3000万元的索赔。
富士康仗着自己身躯庞大,一下子压到小虾米的身上,殊不知正好将自己一丝不挂地暴露在放大镜前,原先脚下踩着的事实薄冰,瞬间化成舆论的汪洋大海。
富士康起诉记者案一经爆出,全国各大媒体纷纷挺身而出,全力支持《第一财经日报》的被告编委和记者。首先,《第一财经日报》发函谴责富士康,其公函中称:“记者报道属于职务行为,报社将动用资源支持两人全力应对诉讼针对贵公司采取诉讼保全措施,查封两人个人财产的做法,本报表示强烈谴责。我们相信贵公司这种以公司组织行为针对记者个人的做法,将为整个中国新闻界所唾弃。”
其他媒体也以种种方式,或谴责或控诉或动员来表达对富士康的不满及对被告人员的支持:《21世纪经济报道》主编刘洲伟认为,新闻报道是记者的职务,富士康起诉个人使媒体的报道权受到威胁,这种威胁同时意味着公众的知情权会受到限制;《京华时报》社长吴海民认为,记者是代表报社发表观点和报道,现在把记者推上被告席是欺负人的做法,大家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抵制这种行为,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中国经营报》总编李佩钰称这是一个典型的反面危机公关的案例,企业的做法极为不明智;《经济观察报》总编辑何力认为:“这一举动明显是别有用心的与其说是企业起诉的一起法律行为,不如说是对记者正常新闻报道的一个威胁。”
富士康公司的一纸诉讼,并没有如预想的那样压制住“血汗工厂”的舆论,反而将自己推上与社会抗衡的不利局面,“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社会舆论的负面导向让富士康在民众心中臭名远昭,而且媒体旧事再提,使得富士康骑虎难下,在中国更难做“人”。
舆论的口诛笔伐、民众的愤怒让富士康这个不可一世的大鲸鱼感到了压力和恐慌,它开始明白杀鸡儆猴这步棋走得不仅不奇,反而将自己拉入漩涡中。识时务者为俊杰,富士康开始学乖了,正式撤销了对《第一财经日报》的诉讼,与《第一财经日报》和解,干戈终化玉帛。
当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对风险的深刻洞察让“媒体为王”顺理成章地成为当代常识。从19世纪末以来人们就都能感受到科技的巨大威力,其中信息处理和传播技术的一日千里,更是让媒体猛虎添翼,成为跨越国界的力量。媒体让“疯牛病”横冲欧洲、亚洲、美洲,导致人人自危;媒体让电磁辐射致癌的消息给摩托罗拉当头一棒,一把将其股票拉下水;媒体,让安然、爱尔兰银行、安达信的财务问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对此,具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认为,是媒体帮助企业防范更大的危机;而深陷危机漩涡的企业高管认为,是媒体导致危机。
套用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的名言,媒体真正想赢得的,不是一般的掌声,不是压倒被曝光者的快感,而是通过“善良和公正”以及“专业的尊严”,得到外界真正的尊重。媒体扮演的是信息传播者的角色,与媒体为敌,就是变相地与不知情的公众和社会为敌,企业怒发冲冠,只能瞬间陷入“一个人战争”的孤立无援中。
中国大多数陷入危机的企业管理者属于后者,视媒体为洪水猛兽,决定以力相搏,低调者是“无可奉告”,高调者则要将媒体“绳之以法”。这是非常不可取的舆论处理方式。
还是以富士康为例。富士康这一招,大不合世界发展规律,小不合中国国情。即使从人之常情来看,也是欺软怕硬,道理全无。点燃富士康“血汗工厂”事件导火线的是《星期日邮报》,而《第一财经日报》只是借势深入报道而已。鸿海集团也数次在媒体面前表示保留对《星期日邮报》的诉讼,到头来,将焦点放到《第一财经日报》的编委翁宝、记者王佑这两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所谓“小虾米”身上,而《星期日邮报》以及两位被告的庄家《第一次财经日报》被一一放过了。可见富士康的用心良苦:翁宝、王佑是整个事件危机化解中最为薄弱的环节,起诉他们只是针对个人,并非向媒体发难。难道大鲸鱼还摆不平这两个不起眼的小虾米?
然而,企业大鲸鱼是单枪匹马盲目而动,染上官司的新闻记者小虾米却是连动天下,引发舆论群起而攻之。围魏救赵的打官司攻略,只是让它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脚踏进两个危机当中。
当富士康出现危机时,它不仅不急于对媒体的曝光进行证伪,还蛮横地加以否定。否定后仍意犹未尽,杀鸡儆猴,挑战小记者,给中国媒体一个下马威,社会开始愤怒了,力求封杀这个没有自知之明的“疯子”。
当媒体曝光企业的问题时,不管问题是真是假,企业应该先别着急,耐心提供证据,解决问题,才是明智的做法。花钱堵不住舆论洪流
真正的舆论洪流,仅靠花钱是堵不住的。
20世纪90年代,在北京梅地亚中心,秦池集团以6666万元天价在央视黄金段广告招标会中一举夺魁,“标王”秦池因表现出的无比冲动和激进气质,其知名度一夜暴涨。“标王”过响的名号以及媒体鞍前马后的报道使秦池一度成为中国最畅销的白酒。
1996年,秦池集团的老总姬长孔被安排在梅地亚最醒目的主桌主位上,作为企业家代表发言,称:“1995年,我们每天向中央电视台开进一辆桑塔纳,开出的则是一辆豪华奥迪。今年,我们要争取每天开进一辆豪华奔驰,开出一辆加长林肯。”这一年,秦池以3.212118亿元蝉联“标王”,而这个数字简单得没道理——竟是姬长孔的手机号码。
1997年1月,《经济参考报》刊出一条新闻,称秦池山东基地的年产量是3000吨原酒,难以满足市场源源不断的需求,秦池便从四川的一些酒厂收购原酒进行勾兑。此时,姬长孔正志满意得地赶赴北京领“中国企业形象最佳单位”的奖。《经济参考报》的爆料,很快在媒体中引发连锁反应,那些曾经将秦池的形象描述得无比高大的报刊,又以迅雷之势转载和报道秦池的勾兑行为。
已经习惯站在神坛上的姬长孔,根本不知道如何体面地从神坛上走下来。不知所措的他,除了花钱收购报道,想不出更多更好的办法。然而,包裹真相的纸已经很薄了,包不住更猛烈的火势,大部分媒体更愿意乐此不疲地揭露“标王”背后隐藏的血腥。秦池销售额连续走跌,到了2000年,秦池连300万元的贷款都还不起了。
花钱封堵不成,反而弄巧成拙的案例,不止秦池一家。
2004年,石家庄的春天阳光明媚,生机盎然,三鹿却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打击——被列入了阜阳市劣质奶粉黑名单。危机乍现,三鹿长袖善舞,在刀尖上自由旋转,演绎了一段精彩的危机公关剧然而,四年后,物是人非。在“三聚氰胺”事件之后,迫于社会的巨大压力,这家由街道妇女为骨干,以32头奶牛和170只奶羊白手起家的乳品企业,在经过半个世纪的由默默无名到脱颖而出的创业历程之后,最终折戟沉沙,以死谢罪。
三聚氰胺毒奶粉吃出结石宝宝的事件被媒体披露之后,三鹿危机管理还是在按常规操作:试图大手笔买通媒体掩盖真相。当各地消费者陆续反映三鹿奶粉有问题时,三鹿动用权力、金钱公关,使多家报纸封了口。后来,还出现了三鹿拿出300万元广告费收买国内某知名网络媒体的说法。
可是,这次事件的影响和冲击远远超出三鹿的设想。事态并未得到想象中的控制,反而愈演愈烈。最终,在道德的谴责和企业信誉的崩溃下,三鹿终于还是破产了。
促使三鹿走向“不归路”的根源首先还是在于中国有一批类似三鹿这样的企业,他们为了追求企业利润的最大化,不断游走于灰色地带。
中国制造被他们当做“江湖制造”,办企业被认为是“跑江湖”和“赌人生”。责任、信誉、质量与安全,只是他们口头作秀和自我包装的工具。他们把提高舆商当做一门浅显的学问,认为舆商的本质就是买通媒体,掩盖真相。也许,这样的危机处理偶尔也能成功。但是,只要忽略了企业生存的根本——质量和信誉,一旦背弃了道德与良心,就会应了那句话“出来混,终究是要还的”。
买通媒体虽为掩耳盗铃、用来应急的缓兵之计,但也可能会成为部分媒体“要挟企业”永远的把柄。一旦企业的小辫子被揪出来,大部分媒体会扮演不依不饶的角色。企业试图花钱堵住记者的“嘴”,只能堵一时。哪天这位记者或这家媒体不高兴了,照样会将企业的问题公布天下。哪怕是陈谷子烂芝麻,只要是企业尤其是品牌企业的瑕疵,总会引来不少不明真相的围观者。
其次,并不是所有的媒体都会在企业打出的“糖衣炮弹”中沦陷,媒体也有良知和责任。
再次,社会舆论的边界远远超出了媒体。除了媒体,还有日渐开放、相对自由的社会化舆论。以前有一句笑话,说的是以前在网上,不知道对面是人是狗。而现在,“别说你是条狗,就是外星人也照样能被搜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