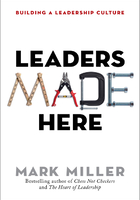我望着他,泪痕湿透眉间心上。
无以褪相思。
他在彼岸那畔,盈盈一望。
洛水三千,不及君之笑颜。
白衣如玉,身姿如画。
影态翩翩,故是惊鸿。
我吹着笛子,一袭浅色衣裳。
在桃红柳绿江南烟雨处,静望公子。
背影在,碧玉簪子映霞君。
他在那高台之上抚着瑶琴。
我望着他的笑靥。
心上点点相思意。
烨君……
桃之夭夭
灼灼其华
……
宜其家室。
我们就差一点就能在一起。
终究遥不可及。
他渐行渐远,终不见丝毫影迹。
我蓦然醒来,于书案上观画。
血猛地涌出。
我捂住开裂的心,骤痛袭来。
执起蜡烛将那幅画焚烧殆尽。
就好像我的心,早已死却。不会醒来……
烨君。
我已经很累了,终于缓缓陷入沉睡。
期待来年再遇、重逢。
多年以后,云初消失无迹。中原乱,夏国亡。
其人不知所踪。
谁人在画舫上弹着琵琶。
此间无期,与会,共巫山。
远方的那人与我思慕的那人很像。
白衣翩跹,醉影惊鸿。
月下来相守。
我猛然一惊,却是南柯一梦,醒悟不矣。多少前尘往事一瞬来……
我从深山内惊醒。
魂魄已俱。
躯体早已化灰。
无奈矣。
只得飘往人世处,寻觅归宿。
――――――分割线――――
我在思慕著她。
這山河,你可喜歡?
是我無能,未能護好江夏國。
于一桃源處隐居弗出。可好?
天青色的嫩柳青草,碧波池旁。
拂過瑤琴,匆匆三两下,意亂且無心。
我來到她的廂房。
依如故舊。
嘆息,而飲濁酒。
喃喃低語,顾怀远人。
窗外花開無限濃
而我卻在想你想斷腸。
莫能低語,徘徊而低下。
舞低歌臺嫩楊柳
花開無限柔情濃。
我緩緩地思慕著她。
為她譜了琴曲。
那是曾聽她時常唱的碧袖罗烟曲。
還有她寫下的广袖云烟曲。期以来日花下,能靜靜吟唱給她聽。
玉娘……
宴會上,他們投壺盛行,不亦樂乎。
我匆匆而過。
停下,俯身施一禮道:“你們於此間作何?”
他們停下,回禮。
其有一人向我道:“父君,你也來加入我們。可好?”
這些都是幼子。
他們的父親都在当职,而母親亦無閑著之。
所以,他們都還小。
纔有這麽多大把的時光浪費。
“……不了。你們先頑吧。我于一旁看著即可……”
一旁有些喧囂。
是一群孩子在弄百戲。
我走過去。
他們一見我來,就过來撒嬌。
我安撫好他們。
遂繼續行走,但见
――
有鬥草的。
亦有折柳的。
還有隨父母學术的。
我呵呵一笑,碧色蓝天下,無比歡暢痛快。
遂提筆寫了一封信。
邀請她來到此間玩耍。
卻不知能否收到。
我用的秘朮加血與記憶,化灵蝶,前去找尋。
這些日子,越來越想她了。
我在那高臺之上仰望蒼天。
此間的書畫題字倒是繁多。
思起那人的一舞,我總是良久莫能抑下心跳。
玉娘,當真世无双也!
有小童在舟揖上與人比拼激浪。
我望著他們那笑個不停地容顏覺得分外欣羨。
那明朗的目光微望這山河。
我來道他的身前。
道:“你叫什麽?”
“小字昌意”
“此字尚可!”
我又道:“汝可願拜我門下,我收你為徒?”
“徒兒願意!”他哐哐哐地磕了三下头。
拜我為師。
我遂帶著他,行了拜師禮。
傳信以告之父母。
他笑道:“不、不用了……”
我說,“怎麼?”
“阿妹降生,他們忙不過來。我一時出來玩耍才遇到师傅。你若和他们说,又要接我回去了。”他憤憤地說道。
我撫了額頭。
這孩子是如此的可愛。
纯潔無比而又十分的柔雅端莊,淑態怡然。
於是,我收下他,每日傳授些通天之教,他倒也學的樂甚。
後來,他的皮膚越來越亮白,容顏越發精緻而瑰麗。
我有些懷疑,这是不是假小子?
於是我旁敲側擊地打聽他的身世。
她不肯說,我也不問。就這樣當著女兒養挺好的。
不過後來有一天,她长大成人后離開我了。
不知去了哪裡。
我也沒有找。
且隨她。
這裏,還是很安全的。
不合禮法已驅逐出境。
是以民心還是很不錯。
我對他們有信心。
亦對自己這個培養了多年的徒弟深具信心。
對她來說,自然一切都不是問題。
忽有一日,有人從外間前來,道:“父君,有人求見!”
我彼時睜開打坐的眼睛。
問道:“誰?”
“自號明玉公子……”
我頓時起身。
一瞬來到那人眼前。
她還是和以前一樣的美麗。
不過,這是怎麽回事?
我以眼神示意,問道。
她身後牽著一個女子。
很小弱的一個。
“阿若,叫父親……”
“……”我,莫能語。
衹是收養了她。
我們一家幾口。生活也倒好。
只在此間,不復然也。
末章――就這樣,度過了餘生。
晚亦遲
翩然歸來
花開還
緩緩歸矣
與君相守夢幻,已然不復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