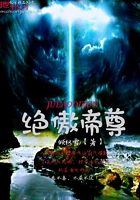廉州,一届弹丸之地,左制北羌,右扼大胡,南邻中原,居于六国之间,以不可撼动之姿长存两百年之久。其势斑杂犹如乱世,其人悍勇有如阵前猛将,以四大家为首,兼制七十世家,百姓安居乐业。
其中,东方南宫,西门北冥,两两联姻,其一势颓,则借以亲家之力稍作缓之,细心经营,如此以来,四大家战无可战,退无可退,一时间天下以廉州为锁,互不征伐三十年。
廉州北川县忘远山,虽其山名不显,可若是说起山中居住之人,到算得上脍炙人口。
廉州难得的的读书人,姓司,名礼,字伯恭,早年便有人来请,要以国相之位,俸禄千金,良田百顷,米粟万石为引,要请他去。
可是被咱们先生一口回绝:“如今天下安定,我所学学问,百家之术,无所谓博览,只偏偏读了一个‘兵’字,如何敢在这太平盛世,出山去做一个祸国殃民之人?”当时说这话,那咱们可都是在的,倒不是生怕先生跟着走了。
我们知道先生不会走,怕那些人恼羞成怒,到时候先生凶多吉少啊。
年近半百的老人得了司礼的恩惠,强忍着一颗不断打颤的良心,说出来一番司礼早就安排好的话。可是在临末了,怕自己露出来马脚,又给加上了一句。
这一加是好心,可是却反而露出马脚。
司礼有大本事不假,这咱们都知道的,陆陆续续一直都有人来请,只不过到底说了什么咱不知道罢了。
看他收的徒弟,两个大眼睛咕溜溜的转,那股子聪明伶俐的劲儿,绝了!和他师傅早些年一摸一样,都叫人看着瘆得慌。
“伯伯,暂且不论其他,便说离咱这最近的,草蛮北羌,尚且与我们有一川之隔,相差千里,此路前来,即是以国相来请,便少不了保驾护航的。怎么着,国之栋梁,千骑为伴,不过分吧。更何况,他们得骑着马,那一千人马,咱们的人别说挤进去了,连离近点的胆子都没有,怎么听的跟您这般绘声绘色啊?”
说着,年纪不大的孩子笑了起来,踱过来跺过去的,水灵灵的大眼睛滴溜溜的转,纵然平日里长不大的司先生如何擅长躲藏,也没能躲过自家弟子的眼睛。
在感觉到自己肩膀被人轻轻的拍了两下之后,司礼笑着说:“那边不能是我将给他们听的吗?”
“你讲的,能有几句真话?”少年笑了起来,摸了摸鼻尖,忽然发觉自己流鼻血了,赶紧仰着头,师傅看了笑话自家土地:“说不定啊,你把头低下来,血流干净了就不流了。”
三人都笑了起来,司礼从老人手里接过锄头,埋着头吭哧吭哧的做了起来,说是恩惠,实际上只不过是司礼住在老人家,实在是心里过意不去。
约莫着过了两个时辰,司礼身体是不怎么样,读书的,没几个有力气的。
“阿爹,司先生,小兰子,回家吃饭吧。”老人有个好女儿,长得漂亮,读过书,吃得了苦,又孝顺,这样的女孩,想提亲的多了去了,不过她却总是推推掩掩,就是不愿嫁人,时间久了,也就没人再去给自己孩子,说一个三十岁的女人了。
听到声音,锄头落在了地上。
“好~。”
“好嘞!”
“好嘞!”
说完,两师徒撒腿狂奔,没有一点拿自己当外人的意思。
仿佛……他们就是一家人一样。老人说完,语重心长的嘱咐自家女儿,要快点把地翻一遍,不然庄稼容易死。也别太吃劲了,匀着来,等我们吃完饭回来,你在接着干。
语重心长的嘱咐了半天,老人终归还是放心不下:“罢了罢了,你也回去吃吧,等你们吃完了,过来接替我,我就在家,一口气睡到明天晌午。”
抬起头看一眼自家女儿,两个大眼睛看向两人离开的方向,向来和颜悦色的笑脸老头,难得的流露出一副恨其不争的神色。双手背后,摇头晃脑的回了家。
在陶瓦筑里面,有一间屋子总是显眼,别人家的土房蓬瓦,唯独这一家,是别人高攀不起的红璃檐角。白县令坐在家里,看着自家儿子,已经十三岁有余,司礼早些年是有多少本事,他虽然不清楚,可却是知道比自己这个九流末节的小山村里的县令要强太多了。
村里面那个读书先生,自己都不能知文断句,把儿子交给他怎么放心。可要是送到外面去读书,真当几块破砖烂瓦,在这小山沟里和外面一样?
“怎么又回家了?”白塱瞪大双眼,看着白辂敲着腿,坐在窗户上,一副自己了不得的样子:“你说他司礼有本事,我可从没听过他说过什么了不得话,更何况,三天两头下地去了,难不成我要跟着去不成?”
“人生于黄土之中,溪水之下,天精地灵,所种疏植皆为生之所需,下地做农活怎么了?难不成,你不是个人不成?”白塱越看越气,抄起手边的扫帚作势就要打在白辂的身上,被白夫人赶紧拦下来。
“老爷,我觉得辂儿说的也不错,下地干活,你是知道的,他做不来。”听了娘亲的话,白辂装模做样的捂住头,在地上滚了几圈,咳嗽了两声,又捂住肚子,过了一会儿,见爹没反应,又站起来抱着脚,一蹦一跳的落在白塱脚下,抱着腿笑嘻嘻的。
终归是我的儿子,总是打,确实不是个办法,唉,罢了吧。白塱大袖一挥,朗声说道:“孩他娘,取些酒,我把他领回去。再过个几年,就送到镇上读书吧。”
嘿,小鬼精没说错啊,爹提酒过去了,又能吃上一顿好的了。
白塱前脚踏出门,白辂后脚跟上,白塱停,白辂走,如此反复,白夫人捂着嘴看着这爷俩,摇摇头往酒窖里面走。
说是酒窖,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大坑,有半人多高,一人多宽,里面的酒都是好酒,只不过……糟蹋了呀。
到了大堂那边,看着那爷俩,还是大眼瞪小眼的样子,知道俩人都得有个台阶下,白夫人开口说道:“辂儿,叫你爹先过去跟人赔礼道歉,你在家吃过饭再过去吧。”
“那哪行啊娘,孩子犯的错,怎么能叫爹去低头,我去,大丈夫能屈能伸嘛。”看着白塱一张拉的老长的脸突然笑起来,白夫人捂着嘴,咯咯的笑了起来,一家三口,和睦的很。
当娘的不就是这样吗?在家里,总要有个说好话的。
走在村里面的小道上,冷冷清清,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就要开始征兵,年满十五岁的青年壮汉都要上战场,廉州这种小地方,骨头硬,是没人愿意打的,可却总有些不得不挨打的时候。绝不能让大端的兵打到北羌。
绝不能让大胡的兵越过大端,至于为何,白塱是真的不知道。
一家在东头,一家在南头,在小山沟里,很快也就到了,看着房门紧闭,白塱敲了敲门,朗声说道:“司先生,在家吗?我提酒来了。”如此反复三四遍,没有人回声,白塱皱了眉头,手脚轻快的爬上树,看着院子里面安静的很。
又看见灶房那边有烟,快步赶过去,幸好火势不大,拿起水瓢赶紧灭火。奇了怪,平常一到饭点,孙家不会没人的。
莫不是……出了事?掀开铁锅,里面早就快烧干了,在锅盖上,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有个稻草,指着西山那边。
“快!出事了!”白塱也顾不上才十三岁,一脸无措的白辂,挨家挨户的叫,小山村里面上面的人不在意,根本没钱请衙役,平时出了事全靠邻里帮扶。
“怎的了是?”
“出了什么事嘛?”
“叫人喘口气!别急。”
“孙老爷子家里,灶火没熄,人也不见,要紧的事,司先生也不在。”白塱说着前半段,没人在意,可以听饭点到了,司先生不在家,众人就变了脸色。
白塱见大家都打起精神了,有人扛着锄头,有人拿着叉子,反正是拿了顺手的东西,问:“你说怎么找嘛?”
“去西山上,家里面,有人用稻草编了个标记,指着西山,去几个人,剩下的都散开着找,都是大老爷们,可不要害怕一个人走,尽量找的大一点,好不好?”
“说的什么话?怕我们在一块不做事啊?”
“就是啊,说的算是什么话。”
“对不住,对不住,说错了话。不过,还是要说的,千万别扎堆找。”白塱再三嘱咐,村里面大家终于是散着往周围走,两个年轻点的朝着白塱一点头,就朝山上跑。
在角落里,一个看上去就胆小如鼠的贴着墙角,试探的看着白塱,白塱朝他摆了摆手,他也不知道明白了什么,转头走了,打开家里的门,接着睡自己的大头觉。
第一次司礼丢的时候,村子里面的少壮都被抓走了。第二次司礼丢的时候,三千轻骑那场面能把人吓死。第三次司礼丢的时候,在山后面偷酒喝被人打了个半死,腰里面别着火折子,差点把自己给烧死。
除了这之外,还真没见司礼出过村,至多至多也就是在地里面除草,播种什么的。
“子和,别在外面打转了,你回家去,你犯的错,我们回家后再说。”白塱说完,把宽大官服的袖子一扎,随手抄起一直带着的尺子。
白辂看见这尺子就害怕,小时候没少挨板子。一般孩子都是在小时侯不怎么挨打,越大挨得越是狠,白辂这货倒是从小和别人不一样,小时候天天挨板子,长大之后不仅仅是越来越俊俏越来不像他爹,就连板子都挨得越来越少。
“小兰子也没和我说这一出啊。”白辂虽然是小声嘟哝,但还是传到了白塱的耳朵里面,眯着眼睛,不知道是不是司礼搞出来的名堂。
权当没听见,追上刚才去了西山的两个人,沉声吩咐道:“到了山上,走的轻慢一点,尽量走在树后面,别叫人看见。”
两个少壮,说是少壮,其实也有三十年岁,征兵的时候就当了几年的兵,身手还算的上不错,也算是有胆量,故意在战场上断了一条腿逃了回来。
听到白塱吩咐,知道牵扯到司先生的事情小不了,也沉声点了点头,乱世多贼,要是山贼流窜,下晌下的最晚的孙家五口人倒真有可能是被捉去了。若不是……那事情就大发了。
学着老爹的样子,白辂轻车熟路的爬上桃树,和司先生留下来的线索不一样,看着院子里面大大咧咧躺着的扫帚,指着西边,白辂就贼兮兮的顺着山路走,一路上都只有树墩,刚过了伐木的季节,也是村子最富裕的季节,所以村子里面,孙家五人才会这么显眼。
“小兰子,小兰子!你躲在哪了?”白辂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大大咧咧的叫喊,在小山丘上,借着树林隐蔽身型的两伙人同时追了上去,白塱看了一眼手中的铁戒尺,两只用力一划,尺子就开了刃,变得如剑一般锋利。
两个少壮看见县令的本事,倒是有点差异,却也算是见过世面的,没有过多的惊讶,只是脑袋越来越低,细心的查看森林里面留下的痕迹。就算是哨子,比起步卒还是要强上不少的。
“怎么回事儿?不是说好要骗酒喝,吃好吃的吗?”白辂走了相当长的一段山路,终于是走的双脚酸痛,就坐在了木墩子上休息。白塱理所当然的觉着自家儿子不会停下脚步,故意偏离了行经,去往山上走。
到了山顶折返下来,西山就算是一览无余,根本没有什么好的藏身之所。东边是一毛不拔的荒山,另外两边都是农田,根本用不着太多的搜查。
就这样,三位布衣农夫,撞上了素衣快马,腰间环玉的兰明,对方面白似玉,胯下一匹枣红小马,怎么看,都不会是小时候的那个人了……倒是奇怪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