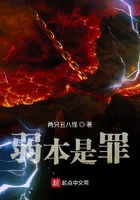这件事情对我震动太大了,晚上常常做恶梦。我就回家了。
在家待了大半年,就到了年关,二哥、二嫂和三哥也都回家了。这个年还算是过得热闹。过完年,点了元宵节的明心灯,我们兄弟几个又要外出打工,父亲就不让我再出去。他把一切心思和精力全部用在村子里的事情上。洋芋要实行芽栽,玉米要覆盖地膜,麦子要兑换优良品种,这在当时偏僻农村的人难以接受的情况下,是得一家一户上门做动员工作的。最头疼是计划生育,上面每年下达的节育(戴环、结扎)指标完不成,当干部的人便要挨家挨户讲政策,动员完成。实在有生育五六胎的还得采取一些非常措施,强制节育。这样就顾不上自家的事情。本来是要三哥留下来的,因为他一直挣不来钱,每次回家不是说工资还没有发,就是说工钱被骗了。或者说他遇急事花费了。当父亲要他留下来时,三哥却说他有一笔工钱还没有讨要回来,如果不去,工钱就找不到人讨要了,他就走了。这样,只能是我留下来照顾家中。
农村贫困家庭的环境氛围与城市截然不同。活儿零散、繁杂不说,饭食总是老生常谈,不是莜面饼子洋芋菜,就是白面浆水面,活儿忙时就煮一锅洋芋,锅里带几个蒸馍或者糜面砣砣,凑合几天。一年四季难得有肉吃,有酒喝。
进城务工,虽然有时也挨饿受气,但隔三差五总会有肉吃,有酒喝的,还会享受歌舞厅里的快活浪漫。尤其是近几年来,一搞“战利品”就是几百元、上千元的收入,吃喝由着自己。还能与脾味相投的朋友谈天说地。已经把心闯荡野了的我,随时都想着瞅机会外出。
白天倒也容易度过,晚上一个人的时候,就感到十分空虚。想到小强他们,我心中便生发一种想表现的冲动。我拿过铅笔,写下了一段心情日记:
经过一天的劳动,现在终于可以安静下来了。
拾起这笨拙的笔,记录人生。选择了一种生活,就要终身矢志不渝,为了达到某种境界,就需要忍受太多的寂寞与痛苦。多舛的命运撞击,以至贫穷的折磨,都时时困扰着我年轻的心。漫漫长夜,不知何时是黎明?有时候我觉得:生活往往让人不可捉摸,一些人的生与死都不轻松。也许没有人注意到我落魄的行踪,但我一直在寻找——寻找着能够安慰我心灵的那一块圣地,那一种意境。
我很想找一个圣明的人为我指点迷津,揭穿生命的奥秘。然而,我的身边全是一些和我一样带着伤痕在暗夜中徘徊的灵魂……
常言道“树欲静而风不止”,一点不假。想外出的意念虽然不时在我心头萦绕,但没有充分的理由,还是不好离家。大龙和小强的来信,促使我再次离家出走。
大龙和正林过年没有回家,他们来信说在过年期间,是最能捞钱的时间,发了工资和奖金的人们,年关前便突击花钱购物,过年后又带着礼物走亲访友,这时来往坐车的客人就特别多,这个时候也是社会秩序最混乱的时候。运气好时,还会浑水摸鱼,搞“战利品”也容易得手。从他们两家人的口中,也得知了他们邮寄了不少钱。
小强的来信其实是为我“宽心”的。我是他最小的兄弟,也是他的崇拜者,出于这个原因,他一向对我比较关心。他可能意识到那次事情后,对我神经有刺激,发现了我神情不带劲,受到了惊吓,就写信了。
小彭兄弟:
你好?家人都好吧?几个月没有你的音讯了,还真想念你。
按照咱们哥们的关系,你不会一走了之的,你会回来的。你之所以迟迟不来的原因,我想肯定是那次事情造成的。(或者家里有什么事吧)你年龄小,没有经过大事情,受到惊吓了是吧?其实,你用不着担心,哥都给你分析过许多原因了。要是他们报警了,我们肯定不会到现在这样逍遥法外的。你看吧,没有事吧?大半年过去了,我们仍然相安无事。你放心,这事他们只能打掉牙往肚里咽,我们四个人不说,谁也不会知道的。要说犯罪的话,我们四个人是共同犯罪,是一个绳子上拴的蚂蚱,要活都活,要死一同死,我想我们谁也不会是傻瓜。
我今天写信要说的,主要是为你宽心,给你吃定心丸。不要因为这事影响了情绪和身心健康。顺便告诉你,我也打算不干了。经过了那次事情,我的心愿也实现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安慰小杨母子的在天之灵了,钱也有了。我打算挪一个地方,做点小生意,我还希望你来加盟帮忙哩。
我最近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主意还是她出的,是她的话提醒了我。你猜这个人是谁?
小强接着说,他遇到的是本村的李大嫂,就是那个让他“顶账还债”的秦大姐。她的丈夫,也是小强的庄间堂哥李大哥,他原本就在这个城市里。他是偶然在一个饭馆吃时遇到她的,他们夫妇也来吃饭。
呵呵,这又是一处“无巧不成书”“千里有缘来相会”的境遇。
他说她猛然见到了他,在惊讶片刻之后,便是热情招呼。其实她的丈夫李大哥比她还热情。在如此遥远的千里之外,能遇到一个村子里的老乡,那是太不容易的事。何况他们原本是一个李姓哩。李大哥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快能给他们当儿子的小强兄弟会与他的妻子有什么瓜葛。更不会想到会有轰轰烈烈地“抵债还账”的荒唐事。他们不但给他开了饭钱,还硬是把他请到了他们家里作客。
至于他与她再度相会后还有什么事情,对中年女人有冲动的小强会不会与她再续“抵债还账”之事,小强没有说。
看来,他遇到了她,也不是一件坏事。最起码在她的影响下,他的思想有所转变。
原本在家不安分的我,看到这个消息,就想与小强一起做点生意。也是少年无知和好奇心在作怪,想看看那位与小强有过一晚七次活动的大嫂。就借口到兴隆赶集,坐上了开往银川的班车,进而转车到了我们在这里奋斗了好多年的熟悉的城市。
我还是重操旧业,进了永兴车行,这次租了一辆夏利小车。一天是五十元租金。
遇到了大龙、正林和昌子、利益他们,感觉他们身上有了很大变化。穿着打扮阔气了,不再是随便的衣服和鞋子,而是价值不低的高档物,有西服,有皮夹克,还有羊毛衫,脚上不是皮鞋,就是旅游鞋。抽的烟也不是原来的一盒子八角钱的“金驼”和一块钱的“龙泉”,而多是五块钱的“石林”“白沙”,还有十块钱的“红塔山”“一支笔”。偶尔还会掏出“中华”和“阿诗玛”。说话也时髦起来,“他妈的”便常常挂在嘴上,动不动就发出“操”“靠”或者“晕”口头语。昌子和大龙也换租了夏利小车。
我离开满打满算才大半年,他们就有如此大的变化,这让人不得不想起他们是如何连续行动搞“战利品”的。
小强他们呢?已经搬迁到了一个新地方,接近市郊了,离那位秦大姐家不远。是大龙他们领我找到的。不过现在他不是与兄弟同住宿在一起,而是一个人居住。他看上去神态平静,说话时会时不时咧嘴一笑,好像从来没有做过值得懊悔的事情似的。他的头发已经长了上来,有寸把长,胡子也刮了。这样的打扮还是秦大姐建议的,她说他经常出入她家,原来光头那样的打扮别人会笑话并怀疑的。他这样一打扮装束,显得老成规矩多了。
他也写了好多首诗歌。我拿过他递过来笔记本,翻开一看,果然写了密密麻麻的好多页。不知是他心情激动出手快,还是别的原因,他的字儿很潦草,歪歪斜斜的,不如给我信上写得好看。有一首《冬夜》这样写道:
冬夜,我像游魂,
在城市的一隅徜徉,
思绪乱飞,在新年的灯红酒绿中杯盏交觥,
在雪夜的霓虹灯里,寂寞起舞;
寒风吹走了憧憬,
魔爪一节节疯长;
电杆下的影子,在昏黄的路灯下扭曲变形,
今夜,我注定是一个失眠的人;
我承认世事无定,
也不相信会有天平,
怪只怪自己生不逢时。
我明白,这是他的心情写照,读着使人有一种淡淡的忧伤。他的诗又一次勾起了我写诗的意念。就说:“强哥,你教我写诗吧?”
他说:“我也是一知半解,怎么能教别人?”又说:“诗歌这东西,完全是写心境。用一种特别的意境来表达感情。当然了,写作要有一定的文学积淀,还要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唉,反正我也说不清楚,你还是多看别人写的东西,慢慢消化感悟吧?读得多了,写得多了,就会有进步的。”
我们聊了一个下午,当我表示晚上不回车行与他同宿时,他说:“晚上还有人来,不方便。”
他说着诡秘地一笑。我问是不是新的嫂子?
他摇了摇头说:“不是,是秦大姐。”
正是春节前后的疯狂行动刺激得大家的神经更加麻木了,忘记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古训,结果在一次比较大的联合行动时,被逮了个正着。我们一组和三组,由赵小虎和昌子带领,去扒拉火车,第二组由郑通带领,他们又分为两小组,在红果子打劫货车。
我们的两个组也是分开的,不然十几人在一起豁愣大阵的,目标太大,商量好的是分别扒窃两趟火车,因为这条铁道我们太熟悉了,大概几点有什么车经过,我们都掌握得差不离儿。昌子就带了我们五个人先扒拉一辆煤车,小虎他们随后扒拉一辆货车。煤车以前我们也扒拉过,目的主要不是偷煤炭,而是煤车上也带有其他货物。要是煤车上实在没有带什么货物,那些大块煤炭也还凑合。煤炭运送虽然比较麻烦,但销路很广,一麻包煤炭也可以卖几十块钱,总不能空手上一趟火车么?
后来,大家嫌麻烦,搞钱又不多,就很少扒拉煤车了。
不过。这一趟煤车是运往深圳的,车上往往带着一两车皮其他货物,多是皮革和羊绒制品,这些东西值钱哩。
经过了好多次扒拉火车,我们的胆子大了,行动也敏捷迅速了,上车和接货的地点也掌握得合理了。扒拉火车的人在“上游”蹲守,接货的人在“下游”等候。火车开来了,“上游”的昌子、大龙和傅军就顺势扒上了火车,他们上车后就寻找“战利品”,确定目标后,看到了下游接货的我们,就开始缷货。我和利益、正林三个人麻利地搬运着从火车上扔下来的“战利品”。这次是三大件东西,沉甸甸的,因为天黑,看不清包装上印着什么货名。不一会儿,他们三个人也就下火车来了。昌子很是兴奋,他说这是皮夹克,每件是二十套,一共是六十套,一件按一百元处理,最少也收入六千元,平均每人可得一千元。这次我们是开着三辆出租小车来的,自然比黄包车快速多了。当我们带着收获“战利品”的喜悦心情离开铁路,驶向市区时,发现前面设置了路障。当我们意识到有情况,试图调车逃跑时,发现后面有几辆警车开来。我们束手就擒,被拉进了附近的江城子派出所。我们被铐在楼道里的暖气片上。过了一会儿,一阵人声嘈杂,又有人被抓了,才知道是小虎他们。第二天,又得知郑通他们也被抓了。我们“铁鎯头队”的十八名成员,除了老大李小强之外,全部被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