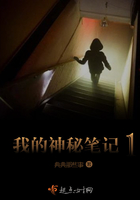“您知不知道,佩蒂塔,”史戴立欧突然问道,“您知不知道世界上有哪个地方会像威尼斯这样,在某个时刻能够激起人们的活力,并把所有的愿望提升到狂热的程度?您知不知道有比这更厉害的骗子?”
被他叫做佩蒂塔的女人侧着头,似乎在聚精会神,却没回答;但她的每根神经都感觉到那种难以形诸笔墨的震动,是她那位年轻朋友的声音在她心中所唤起的,就在她突然间揭开自己因为无尽的爱与无尽的恐惧而展露出的激情狂热的灵魂。
“平静!遗忘!当那些被您独特的演出吸引,疯狂欢呼鼓掌的观众,带着兴奋的情绪精疲力竭回家时,您难道不会在那些孤寂的运河旁发现到这些东西?我只要站在这些死水旁时,就会感到自己的生命随着一阵快速的晕眩而增生,某些时候,我觉得自己思绪仿佛着火一般,就跟神志不清一样。”
“史戴立欧,您是力量与火焰的化身。”这名女子几乎是自卑地说着,眼睛都没抬起。
这段在大运河一艘摇船上的简短激情对话,出自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的小说《火焰》。这个简短的交谈已让人意识到女演员佩蒂塔在这段刚萌发的爱情中会一无所有:自恋的诗人与作曲家史戴立欧·艾冯纳(Stelio Effrena)只把这位未来的情人当成情欲与诗意的毒品;等他见她人老珠黄时,便弃她不顾。
“我心内深深渴望着知识与名声,那往往让我感到一种阴沉恼人的忧郁,逼我痛哭;我无法忍受任何枷锁。”十六岁的邓南遮在一封信中即已描述着自己过于敏感的心绪,而这后来成了这位热情的作家、军人、收藏家与情人的典型特征。
一八六三年,邓南遮生于亚得里亚海旁的省城佩斯卡拉(Pescara),很早便视自己为一与众不同的人,并刻意标新立异。十五岁时,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受到文坛的注视。为了让自己尽快博得大名,这个学生匿名寄给佛罗伦萨的报刊一张明信片,表示“年轻的诗人邓南遮在骑马出游时,坠马而死”。许多报刊刊载了这则假消息,而年轻的作家则在家中庆祝自己的诗集再版。
其他的中篇小说与诗集很快也出版了,其中包括一小本,如诗人回顾之际写道:“歌咏着所有的情欲,配上相当生动的诗句……只在十六世纪与十七世纪那些放荡的诗人作品中见得到,例如阿雷提诺和马里诺(Marino)。”而不久前,在一八八三年六月,邓南遮娶了玛丽亚·哈都因·迪·贾列斯(Maria Hardouin di Gallese),跻身罗马贵族;二十一岁时,他已有一个儿子。不过这桩婚姻并不幸福,两人很快便分开。玛丽亚·邓南遮后来说道,她真该只买诗人的书,而不是嫁给他。
一八八九年,邓南遮出版自己第一本长篇小说《欲望》。这位情欲丰富的矮小男人生命中只有欲望和权力。从邓南遮难受约束的自恋、他那无数的恋情、他强烈的政治野心、豪奢的的生活方式,特别是他那种对今日读者而言往往过分优美的感性语言来看,可以见到一位自认为在他生命戏剧中扮演杰出主角的男人,其他配角不过只是提词人物而已。他所致力追求的超人观念的主要偶像,便是尼采和瓦格纳。
一八九五年,这位已经声名卓著的诗人在威尼斯认识了比他大五岁、早已大名鼎鼎的女演员爱蕾娜拉·杜瑟(Eleonora Duse)。她相当认真,气质忧郁,毫无保留投身戏剧,不只在意大利许多城市演出,也巡回欧洲、南北美、埃及与俄国等地。在她盛大的戏剧巡回演出中间,总不断在水都停留几个星期,住在大运河旁巴巴洛–沃可夫宫(Palazzo Barbaro-Wolkoff)中租来的小住处。这间宫殿属于俄国画家亚历山大·沃可夫(Alexander Wolkoff),他十分欣赏杜瑟。这位贵族画家让这名女星在圣彼得堡顺利演出,并在威尼斯帮她画肖像。
“我在一栋老宫殿最上层有间寓所,”爱蕾娜拉·杜瑟写信给一位女友,“就在顶楼,有扇大拱顶窗户,可以俯瞰全城。秋天安安静静的,空气清朗,我的心一派祥和。”
一八九五年,威尼斯第一届艺术双年展开始。十一月八日,邓南遮在“凤凰”剧院挤得水泄不通的大厅为这个活动致闭幕词。这是这位诗人首度在大众前致词,置身在这群虔诚聆听的群众前,他感到陶醉,特别是知道这些听众中有知名的爱蕾娜拉·杜瑟在场。邓南遮的讲演题目为“秋的寓意”,以热情的文字呼唤年轻的神祇和满怀期望的威尼斯结合在一起。
在邓南遮详细描述诗人与杜瑟爱情关系(且伤及这位女演员)的小说《火焰》中,可以查阅这份演讲。他把自己刻意提到保罗·维洛内瑟在总督府中的天花板壁画《威尼斯的神化》,视为即兴的天才之举。邓南遮的小说角色史戴立欧·艾冯纳,以他的语言魅力迷住了听众:
他靠着目光和手势,把众人的灵魂提升到那幅在大厅拱顶上洒下太阳光芒的杰作中……他们吃惊地看着那个奇迹,近乎仿佛他们第一次,或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光线中见到似的。那个戴着金色头盔的女子裸露的背脊,在云端中展现出光芒万丈的生动体态,对他而言,就像活色生香的肉体散发出诱人的魅力……
诗人在维洛内瑟那幅人物众多的壁画中,发现到“丰满的胸部”和“洋溢激情的脸孔”,而那原是以寓意手法呈现威尼斯统治下的和平盛世。但这种情色的观画方式只是一种神秘的爱情结合的前戏,浮现在这位打量着秋天、情绪高昂的作者心中。
“我昨天见到这样一种火焰,”史戴立欧对入迷的观众说道,“在不受抑制的暴力中熊熊燃烧,并在威尼斯的美艳中,倾注一股前所未见的力量。在我眼前,整座城市在欲望中燃烧,在恐惧中颤抖,被成千的绿色地带围绕,就像一名期待着至高快乐的情人一般。她张开大理石般的手臂,迎向冷淡的秋日,潮湿的气息向她袭来,带来远方和甜美的死亡搏斗的田野的香气……一片枯萎的叶子落在停泊摇船的斑驳石头上,像块宝石一般闪闪发光;在点缀着黄色地衣的高墙上,一株石榴树上熟透的果实像张美丽的嘴唇般绽开……”
心里已有准备的听众屏息等候着这出诗意的演出的高潮。演讲者并未让听众失望:他宣称见到一位年轻的神祇慢慢靠近。他坐在云端,宛如在一辆火战车上,紫色衣袍的衣摆拖曳在后,“既专断又温柔,在半张的嘴唇间,听得到森林的低语与沉默,长发在粗壮的脖子周遭像马鬃一般飘动,露出有若巨人般的赤裸胸膛”。年轻的神祇低头看着美丽的城市,脸庞散发着无法言喻的魔力,“带着些温柔又残酷的兽性,我们可以见到血液在他全身澎湃汹涌流动着,直到灵活的双脚脚尖,直到他强壮的双手的指尖……”
难怪这座美丽的城市无法抗拒这个十分野性的神祇。这位演讲者等着心中的激动逐渐消退后,提出一个反问,那同时也说明了他殚精竭虑的想像:
谁见不到这个对我来说无时无刻生动真实的幻象,我几乎可以触及——我的听众中谁见不到这种意义重大的象征性结合?
威尼斯与秋神相互的激情,让两者达到他们感性之美的高峰,而这源头便在一种内在深处的相似性:威尼斯的灵魂是秋日的,被以前的艺术家拿来装扮这座美丽的城市。
威尼斯和秋神——会是一种乱伦关系吗?至少邓南遮/史戴立欧的激情演说会让人这样想。但在今天读者看来像是反讽的演说,在十九世纪末的意大利是会引起轰动。而邓南遮令人迷醉的图像幻想,亦令爱蕾娜拉·杜瑟无法自拔。这两人在何时何地认识的,无法从现有的记载中清楚推测出。如果按邓南遮的说法,诗人是在某个晚上意外在丹尼艾里饭店遇见女演员的。
但在杜瑟女友奥尔嘉·雷斯奈维奇·辛诺雷里(Olga Resnevic Signorelli)清楚记得的一次对谈中,这桩伟大的爱情开始到时蛮浪漫的:“我们相遇时,正是威尼斯破晓时刻,”她突然慢慢说道,像是自言自语,“一夜未眠后,我四处乱走……突然间,我见到他在我面前下了摇船。我们聊着艺术,聊着今日剧院中可悲的艺术!我们没提到共同的工作,但在我们默不出声的时候,我们有了一种依存……”
爱蕾娜拉·杜瑟和邓南遮这段爱情开始时,在表演艺术上乐被视为“痛苦的唯美主义者”的杜瑟,已三十七岁。戏剧是她的生命。她生在一个演员世家,还是孩子的时候,便得常常代替她染有肺结核的母亲演出。十四岁时,同样也有肺病征兆的爱蕾娜拉便已入迷地扮演恋爱中的女人,例如莎士比亚的朱丽叶,在舞台上死过不知多少回。
早年的一段恋情中,她有名儿子,却在出生后不久去世。这位年轻的女演员哀伤不已,在戏剧中寻找安慰。一八八一年,二十三岁的她嫁给年纪大她许多的同事泰巴多·契奇(Tebaldo Checchi),生下一位女儿安丽契塔(Enricchetta)。这桩婚姻持续四年。杜瑟在一次南美巡回演出时爱上她的舞台伙伴弗拉维欧·安朵(Flavio Andò),她和他后来成立自己的表演团队,并和她丈夫分开。
年轻的爱蕾娜拉·杜瑟和正迈向演艺高峰、十四岁的莎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可说是她那个时代最佳的女演员。她甚至演出绝对属于“出神入化的莎拉”的典型角色,例如《茶花女》,获得偌大回响。
当时的人认为,和那位迷人自信的法国对手相比,杜瑟乍看之下并不起眼。相当崇拜她表演技艺的作家赫尔曼·巴尔(Hermann Bahr),把她描写成“矮小,有点臃肿”,“手势笨重迟缓”,但“没有其他艺术家拥有那种控制所有肌肉、所有神经与全身的力量,让一切不由自主听命,并任意呈现各种变化……”这位女演员偏爱剪裁大方的日常穿着,正如杜瑟的传记作家朵丽丝·毛尔(Doris Maurer)写道,“让人感到俭朴,但却用上最珍贵的布料”。尤其是在威尼斯工作的西班牙时尚设计师马里安诺·弗图尼(Mariano Fortuny),最能符合杜瑟的需求。
爱蕾娜拉·杜瑟和邓南遮一八九五年秋天在威尼斯展开的热恋,也在这两人的艺术创作上开花结果。杜瑟知道邓南遮的诗篇与小说,可以想见,她也会希望他创作她可以演出的剧作。她很想增加她的剧目,找着适合她多样才能的新剧。邓南遮自己正好有这意图。他视杜瑟为自己伟大计划的理想执行着,创建一种民族戏剧,效仿理查德·瓦格纳的拜罗特(Bayreuth)音乐节。
当爱蕾娜拉·杜瑟在北美巡回演出时,邓南遮写下他第一出戏剧《死城》,讲述一段发生在迈锡尼(Mykene)考古挖掘地点的激情热爱。等杜瑟回来后,便在意大利许多城市演出这部激情作品。女主角博得满堂彩,但这出夸张的戏剧却未获得重视。邓南遮为杜瑟所写的其他剧目,情况也差不多;这些作品不太适合舞台演出,但女演员投入精力与财产,按照她爱人的期望那样演出。
一八九九年三月,邓南遮为爱蕾娜拉·杜瑟撰写出第二部剧作《乔宫达》(Gioconda)。这出戏在各地都不受欢迎,不过杜瑟依然受到推崇。不留情面的批评家亚弗列德·凯尔(Alfred Kerr)写道,全然着迷的样子:“杜瑟昨天演出《乔宫达》,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她会从此离开,不得不如此。这个世界无法一直容纳这样的人物。”
邓南遮的悲剧《乔宫达》讲述一名热切渴望成为超人的雕塑家,爱上了年轻的模特儿乔宫达·迪安帝(Gioconda Dianti)。在他的妻子希薇雅(Silvia)努力想挽救自己的婚姻,乔宫达醋意大发,冲向一尊雕像,想毁掉雕像。那尊倒下的艺术品压碎了希薇雅美丽的双手,而雕塑家一起和情人离开了自己绝望的妻子。
邓南遮安排杜瑟演出被遗弃的妻子一角。由于他在这出戏中压制杜瑟特别美丽、充满表情的双手,而被批评家视为她表演力度的残废象征,是诗人私下所愿。朵丽丝·毛尔这位作者在她的杜瑟传中写道:
杜瑟在《乔宫达》最后一幕无法展现她美丽的双手,必须藏在衣袍宽大的袖子中……很难相信邓南遮剧作中这种虐待成分是出于偶然,反而更像他想剥夺掉杜瑟最出色的表达工具,逼使观众专注在他的作品,而非女主角身上。部分观众看穿这个意图,感到愤怒……
几乎在所有邓南遮的剧作中,杜瑟无法像以往那样施展。邓南遮这些感情丰富,但多半情节贫乏的作品,似乎并不适合剧场;杜瑟的表演能力找不到足够的挥洒空间。意大利的剧作家暨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路伊吉·皮兰德娄(Luigi Pirandello)便抱怨“她自然与天才洋溢的表演艺术受到致命的限制。邓南遮给她戴上许多杰出优雅的文学面具,而她自己不该添上其他细节,只能照单全收,就像将贵重合金注入模子做成雕像,姿态固定不变……”皮兰德娄说道,他“在剧院从未如此难受过”,全是因为观看邓南遮《法兰契斯卡·达·雷米尼》(Francesca da Rimini)的首演;他表示杜瑟被邓南遮“诱离”了她这辈子真正重要的戏剧时刻的发展高峰,例如演出易卜生(Henrik Ibsen)的作品。
从一八九七年到一九〇四年,几乎七年之久,甚至在诗人于他的小说《火焰》中揭露杜瑟最私密的感情后,杜瑟几乎完全致力于邓南遮的戏剧试验。这对情侣分开已有一段时间,又再复合,接着再度分开——对诗人来说,这种变换口味可能是种刺激,但对疲累的杜瑟而言,则是一种折磨。一九〇〇年初,她在接受维也纳一家报纸访问时,说道一段沮丧的日子:“解决所有生命谜题的最佳方式,便是早死,没有其他选择。女人不该变老,一名女演员不该错过自己退场的时刻。”
一九〇九年一月二十五日,这名五十岁的女演员抱病,心力交悴,在柏林告别演出,扮演易卜生《海之女》中的艾丽达(Ellida)。她给自己十年平静的生活,多半待在罗马的朋友处。
一九一二年夏天,爱蕾娜拉·杜瑟再次来到威尼斯,遇见在图恩(Thurn)与塔克西斯(Taxis)女爵玛丽(Marie)处作客的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诗人多年前就希望在柏林能见到这位女演员,并在一九〇四年把他的作品《白色女爵》献给她。
正如图恩与塔克西斯女爵在回忆录中写道,现在他“无比快乐,认识了杜瑟,还可帮她;他整天供她差遣,随时待命,但却慢慢愈来愈害怕。他不久后便得知,自己不但无法安抚她,还逐步落入她的痛苦中。有天,他完全手足无措……杜瑟不见了。没有人知道她跑到哪去……整个下午的搜寻毫无结果。大家不得不打道回府。里尔克非常不安。隔天早上,杜瑟出现。她一个人跑去了慕拉诺或乔基亚”。
六十三岁时,杜瑟又再开始演出。她生着病,自觉老迈,几乎没钱,不得不演出。一九二一年五月,她从杜林(Turin)开始在意大利巡回演出《海之女》,十分成功。来年夏天,她又遇见邓南遮,不过这回只是生意上的谈话,是关于《死城》这出戏,杜瑟想要略微删减,而作者表示同意。
这次会面的情况,只有一些传闻。女演员和诗人应该是意外在米兰的一间饭店相遇。关于邓南遮,有人说他在见到杜瑟时大喊:“您爱我多深!”杜瑟的女友奥尔嘉·辛诺雷里表示爱蕾娜拉之后对她说:“我自己私下想着:那个男人还有幻想。我们分开时,如果我真的像他所认为的那样爱他,那我早就死了,不过我却还能活下来。”
这次会面后不久,杜瑟得知邓南遮从他在加达湖(Gardasee)的别墅坠窗,有生命危险。她立刻赶去,见到情况并未像大家所担心那样严重,便放下心头大石。
这是这对过去的情侣最后一次会面。一九二三年六月,爱蕾娜拉·杜瑟展开伦敦、维也纳与北美的大型客座演出。这次巡回表演相当成功。杜瑟过度投入。一九二四年四月初,她感染了严重的肺炎,再也无法康复。
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一日,这名出色的女演员死于匹兹堡(Pittsburgh)的轩丽饭店(Schenley Hotel)。她的遗体被运回意大利。爱蕾娜拉·杜瑟安息在威尼斯附近的阿索罗(Asolo)墓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