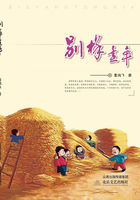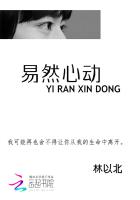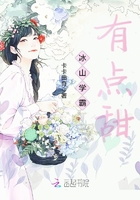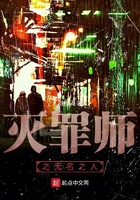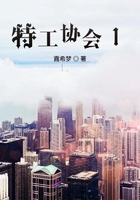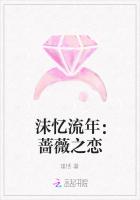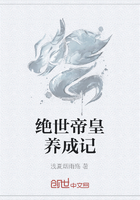《燕京百咏》,清咸丰二年(一八五二)刻本。这是潘挹奎(一七八四—一八二九)写于一百五十多年前的一部描述北京风物的竹枝词。时在道光六年。张次溪先生所著《辛亥以前纪述北京历史风物书录》,专收明清两代有关北京的书目,未载《燕京百咏》。一九六二年路工同志编选的《清代北京竹枝词》(十三种),也不见收录。
《燕京百咏》重在歌咏北京的文物名胜,诸如寺庙建筑,名园故宅,多有考据,富有掌故知识。但是作者很少直接抒写里巷的市井生活,对于一般吃食和民俗等等,亦少记载。因此这部竹枝词与同类书相比,似无显著的特色。作者对于先朝的人物深怀敬意,如写《于少保祠》,指出明代英雄于谦的祠,在崇文门内西裱褙胡同于的故宅内。堂中塑有于谦像,道光时祠已废,仅留下一座福德土地祠,即其原址。诗曰:“故宅崇门敞,荒初古木森,事同晋立围,谋黜宋和金。社稷还先帝,天人鉴此心,夺门功罪定,千载泪沾襟。”我在西裱褙胡同住过几年,只知近人齐如山居此,却始终也找不到于谦祠遗址在何处。
关于白云观,诗人是这样写的: “神仙燕九集,见道似师希,殿宇辉金碧,牲牢谢杀机。白云送来往,元庙认依稀,一钵容如许,何为贱羽衣。”从中可见当年香火之盛。
一首题为《丰台》的诗指出那里的居民多以艺花为业:“叶叶复花花,临风烂若霞,色香成世界,烟雨足生涯,小住春如梦,重游鬓欲华,田间臣独惯,岁岁念桑麻。”作者当官不如意,倒也羡慕起田园生活来。这在官场生活中是常见的老调。但有趣的是,他如实地记载了当年京郊丰台一带确是为京城人民生活服务的。
那里有着传统的养花手艺。《查楼》,即写今之广和剧场:“查氏楼名著,楼今署广和,管弦招胜侣,燕赵发悲歌。自昔环台榭,频年艳绮罗,登场看仔细,载酒漫经过。”这些更接近了一般市民的生活,写出当年“查楼”之盛,当然借此亦抒发了个人的感慨。
写风景名胜的,还有《响闸》和《四川营》等诗。前者写出当时北城风景区是相当宜人的。德胜门月桥东的响闸,道光时名澄清闸,这一带的风景,目前我们已经在注意恢复,但要达到“在城如在野”的境趣恐亦不易。《四川营》传为四川石硅女帅秦良玉屯兵之所,营在虎坊桥西迤北,诗曰: “纵横行万里,为一决雄雌,紫禁屯兵处,红颜转战时,男儿谁骥尾,将略此峨嵋,老树年年发,槎枒见义旗。”这当然为研究一代女杰提供了史料。
据清张澍在《养素堂文集》的介绍,潘挹奎字石生,甘肃武威人,嘉庆十四年进士,官吏部考功司主事。著述颇多。潘的友人牛鉴为《燕京百咏》写序时说,潘为乡先贤立传颇得司马迁、班固的三昧,“往往以极琐细事,传其人之生平精神,跃然于楮墨间”。《燕京百咏》是潘挹奎闻父病辞官回到西北以后而写的。后来他在故乡生活困难,应一位新任监督山海关税的朋友的邀请重来北方谋生,不数月抱病移至北京,死时才四十五岁。一生当中似乎只留下这部与官场生活无涉的《燕京百咏》。
一九八四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