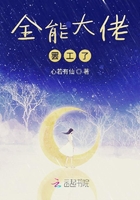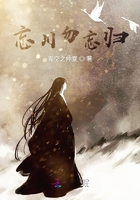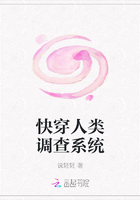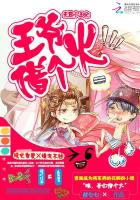光看书名,显然这是一本国外游记之类的书。封面上还印着卢森堡公园内女作家乔治桑的雕像。作者署名“野渠”,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野渠”这名字现在是很陌生了,它是女作家陈学昭的笔名。
一九五六年作者还用这笔名发表过散文。
作者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到了法国,一九二八年秋天到一九二九年一月曾经回国一次,这本《忆巴黎》正是她回到故国后写成的。时间这么短就完成一本散文集的写作,证明当时她创作力的旺盛,也说明她的感触之多。当然,它也为我们提供了写国外游记散文的另一样式,这既不同于朱自清的《欧游杂记》,也不同于徐霞村的《巴黎鳞爪》,更不同于郑振铎的《欧行日记》,尽管都写到了巴黎。散文本来就没有固定的框式,写游记也没有一定之规,从这个意义上讲,写散文可以不必过分相信那些分析和讲解散文格式的宏论。只要确有所感,作者不是可以结合自己的生活随意而书吗?凡是模式,多少总会妨害自由地表达思想的。依我看,陈学昭同志的《忆巴黎》是不顾什么模式而在寻找自己所喜爱的表达方式。严格地说她的目的不在写巴黎,而是在归国之后,有感于国内的现实生活,写出一个时期个人思想上的矛盾和感怀。
也是借了国外生活的酒来解自己内心的愁吧。请看她在书前写的序诗:
我伫立楼头,
仰看飘飘的白云,
又勾起了无限的哀愁!
想当初轻轻地别,
到而今深深地忆,
梦里巴黎,
只是迷离———迷离!
梦的结果是“频年客旅我心已倦,倦心还向天涯寄”,所以在这本《忆巴黎》里,人们简直找不到法国的景物和风土人情,也没有解剖巴黎人的心理状态。看到的只是一个青年女子在异国的心声和哀乐。我相信作者在写这部《忆巴黎》时,只想着发泄自己心灵的苦闷,对于异国风光已经没有兴致多费笔墨了。作为文学作品来欣赏,这要比那些掩饰了自己的心灵而排比名胜风光的散文要有特点,也更能感染读者。
当然,作者也不是一点也没有写到巴黎的风貌,但更多的是写在巴黎对故国的怀恋。如书中的《忆江南》、《变》、《村中》、《近来》诸篇,有异国的环境,中心还是写个人的心境。看来她并不怎么喜欢巴黎。她在那儿生活得矛盾、痛苦,因此反映在这本散文集里的也是寂寞和忧伤。她回到了祖国,大革命失败后的严酷的现实,更使她心绪不宁,正如她在本书“代序”里说的,此刻仍然无法扫去她从海外带回来的寂寞感情,现实更增加了她的烦恼。她的心又开始向着刚刚离开的巴黎了。不久,她还是走向寂寞的旅程,重返巴黎。她的这种心情,鲁迅先生是理解的,记得许广平还以送学昭女士出国为题,写了一篇散文,发表在《奔流》上。文章劝慰她不要过分感伤。有趣的是在《忆巴黎》里,作者也留下了与鲁迅先生往来的痕迹,只是记得过于简略了一点。
时代巨变,物事全非,这本《忆巴黎》已经问世半个多世纪了,它留下的感情却是非常真实的。听说学昭同志到现在还挺喜欢她这本散文集,我相信最主要的也还是它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期作者的心态吧。
一九八四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