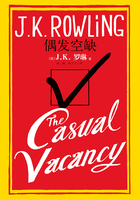醉落楼里来了新伙计。根据隔壁裁缝铺店小二的描述,那孩子长得黑黑瘦瘦的,一天也不见说半句话,只怕是个哑巴,真不知道托了谁的福才在醉落楼里谋个营生。
醉落楼名字叫的大气,不过是挂了个歪歪扭扭的招牌,老板自己搭了个摇摇晃晃的二楼,平日里倒是无事,一到刮风下雨天就吱扭作响,一副随时要散架的样子。常来的都是乡里四邻的街坊,过往的都是走南闯北的江湖客。
老板实惠,一碟摆了三片的酱牛肉,一坛兑了不少水的浑酒,不过收七文钱罢了。时间久了便得了个七文钱的诨号,不过谁也没当着他的面叫过,来吃饭的都得恭恭敬敬地叫一声七老板。
之前有个商客喝高了,踩着凳子唤道“七文钱,过来收大爷给你的赏钱”,老板也笑着过来拿钱,切酱牛肉的手背在身后。等从怀里昏昏沉沉的拿出钱来,脖子上早已架了把刀,泛着油花还有股血腥味,商客顿时酒醒了一大半,抖擞擞地倒出了钱袋子里的所有钱,腿也软了声音也颤了:“七老板大人有大量大人有大量……”等回过神来,钱也没了,人已在门外。商客低低地啐了一声晦气,迈出去的腿却动不得了,一把菜刀不知什么时候生生钉在脚后跟上,这商客才后知后觉地惨叫起来,慌忙陂着逃走了,仔细瞧那立在地上嵌入土中的菜刀竟留下酱牛肉大小的肉片来。
打那起就没人再去自找不快了。
乡野小店,薄利又客稀,靠的不过是十里八乡仅此一家酒楼,度日混口饭吃。
本来店里只有老板一个人招呼,既做厨子又做小二,为了省麻烦只卖酱牛肉和酒,客来切三片牛肉提一坛酒,客走收坛收碟记账七文钱。一到刮风下雨就闭门谢客专心修补屋子,很难有忙不过来的时候。
按理说实在没必要再找个伙计,偏偏有一日刮大风,刮跑了二楼挂的那个木头招牌,等老板追出去找到时,下面还压着一堆破布衣裳,正要揪着这堆布擦擦木牌上的泥时,竟然连带着揪出个人来,瘦瘦小小的裹在衣服里,显然是被砸晕了。
老板也没法子,总归是自家的招牌伤了人,不能不管。便把人搁在木板上拖了回去。路上磕磕碰碰不少石头,愣是没有醒,老板嘀咕道:“嘿,砸的还够结实的。”
拖回去也没地方搁,招牌还要再挂起来,老板决定先等半晌等人醒了再挂。等到日落西山,老板都腌好了明日的牛肉,烧好了水准备歇了,才想起丢在厅堂里的招牌来,准确来说是招牌上的人来。
“哎呀,糊涂!”老板忙起身去看。就着月光,那人依旧蜷缩在木板上,一动不动。“莫不是死了。死了还得明日挖坑埋了,麻烦!”老板探向那人的鼻息,“嗯,还有口气。”纠结了半天后,最终扛起那人往院里去。粗暴地撕了那人身上或许称得上衣服的碎布,一并扔到生火的灶房去,等扒干净了,老板觊了眼:“哟,男的。”摆在平日宰牛的石板上,从井里提了水,冲刷几遍后,想了想,又取了菜刀对着头发一顿砍,直到砍去了所有的死结才满意地点点头。
手碰到滚烫的额头,老板心头一跳,“呦,坏了。”忙抱起人来回里屋。屋内十分简洁,角落里支着一张床,房中间是冒着热气的木桶,里面杂七杂八地扔着桂皮、香叶、八角茴香。忙把人扔进去,又去厨房沏了热汤端进来给人灌下去。老板皱眉,眼睛转了一圈,取了一勺盐撒进去。“这就对了!唉,这桶汤算是便宜你了。”说罢便躺下睡了。
月色温柔地撒下来,氤氲着满屋的水汽。
老板盯着泡在木桶里的人,自言自语道:
“等明日你醒了便走吧。”
过了半晌又道:
“风刮了我的木板砸了你,可见是风伤的你不是我,我虽是木板的主人也不该负什么责任,但我却心善救了你,或许不该救你的。天道存亡,没人干涉得了。我没爹没娘,你也不见得有爹娘,可这世上多的是没爹没娘的人,若是我救了你,岂不是都要等着被救。我就应该把你扔在街上不管的。”
他顿了顿,思索了片刻,又说:
“你泡了我的汤,虽不见得是你乐意的,到底是欠了我,那就还我三片肉吧。不过你太瘦了,需得养一养才好,且在我这里待几日,等还了债再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