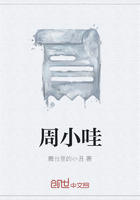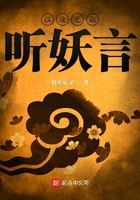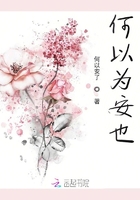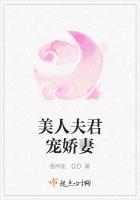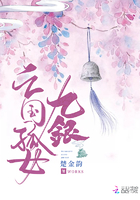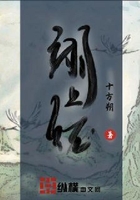今个儿来说说《草虫》。
这首应该算是国风中比较生僻的文之一了。
并且前两天跟家里大领导兼徐大医生探讨了一下,她提出了一个中肯的意见,所以,以下先附上《草虫》原文。
《草虫》
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见君子,我心伤悲。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夷。
有人(主流观念)认为,这是一首妻子思念丈夫的诗文。
但是这种观点,在我将原文读了很多遍之后,心中还是将其否了,倒不是非要特立独行的去标榜不同,而是原文的字里行间,真的没有足够有力的证据来支撑这种认知。
个人认为,从一个人发自内心的情感来说,假如真的已结连理,那么用‘君子’二字来称呼自己的夫婿,有些太显生分了。
当然,这只是其一,其二下面说,因为牵扯到了我眼里这首诗的模样吧。
对于这首《草虫》,其实在写于这里的时候,我心中也略带些犹豫,因为好像看到了两种天壤之别的场景,又觉得都很合适,不知道该怎么抉择。
所以思来想去,便两个都写出来吧。
我首先看进眼里的第一种境象,是一个女孩,可能在某天看到了一个令她念念不忘的人,其后她跟这个人产生了交集,然后这份交集又经历了极长的时间跨度,最后从相遇到相知再到或许产生了的相守。
用白文大概可以这样转述:草中的虫子叫着,蛐蛐也蹦跳合鸣,所以应该没有什么是孤独的?这是初次跟那位贵公子见面。在没有见到他的时候,心中是带着些忧虑的。但是见到了,就停止了一切担心,然后抱了抱他,便确定了自己大概已经沦陷。
(在这里,应该已经确定了恋人关系,所以接下来便是代指了两个时间跨度的约会。)
接下来的约会,是一起去南山挖蕨菜,在没有见到他的时候,内心从忧虑已经变成了忐忑(忐忑的原因可能是害怕对方开始只是心血来潮吧,恋爱一开始总会出现这样的心思。),但是见到了,拥抱了,则变得十分开心。
(接下来初恋的阶段已经过去,因为再去南边山上约会的时候,他们活动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第一次是挖蕨菜,而这次是采薇,所以这时候的感情已经相对成熟。)
然后在这次的约会中,没有见到他的时候心中是伤悲的,大概是因为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吧?然后见到他了,拥抱了,心里所有的情绪都逐渐平复,归于安宁。
很正常的恋爱中两人美好的心绪变化,不是么?所以,不能理解这样一个透着美好又带着怅惘的诗,为和会被有些人(所谓主流)弄的那么悲切哀怨,动不动还扯一下妻子和丈夫梦里相会?从哪里看到的?
(PS.对主流翻译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行查阅一下,这里就不多赘述。)
而我看进眼里的第二种境象,是在琢磨回味了很长时间后突然产生出了一种怀疑。
这首诗,当真是出自一位女孩的手笔么?
虽然说那时候的很多东西都不可考证,但我始终相信,历史记载,对于稀少的女性诗文大家还是有所宠爱的,比如蔡文姬?所以假如这首诗真的出自一个女孩之手,她的名字应该有很大可能跟随历史一起流传下来,或者至少也应该在口口相传之间传承吧?因为在那个年代,这就是一个有传说色彩的女性!
但是----完全没有。
所以这就不能不让人多想了。
其作者便指向了男性,其字里行间透出的意思那就耽美了。
这是两个男人之间的爱情。
而如果这样来理解的话,那么三种心绪变化就更能解释得通透,开始忧心忡忡担心风言风语。跟着,风言风语已经出现,所以再相见之时忐忑不安,生怕对方顶不住压力。最后,可能是生出了很大的变故,(比如有强力的外在因素干扰另一方)所以极度不安之下又深感悲伤,(几乎所有的悲伤都是因为对其事件的无力改写!),最后再见到的时候,抱着的时候,或许会觉得有这片刻的宁静,已经是极为美好,另外多余的事情,也已经不愿去想,不敢多想了。
或许有人会说,一个男人怎么能将文字写得柔软成这样子?怎么看都应该是出自女性之手。
那么我只能说,初唐时候,太子李承乾有个‘称心小郎君’,了解一下?
最后,在两者之间我就是徘徊犹豫的,所以想了又想,不下定语了,因为都是我的看法,所以,关于《草虫》,便就这样。
对了!写到这句突然灵光一闪,为什么诗文的名字要叫《草虫》?如草中之虫般不能见阳光且需小心翼翼么?啧啧----这似乎又是对我个人第二种看法的一个有力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