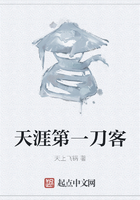覃冕池的主意是,不必执着于先问谁后问谁,两个一起问,齐头并进。
主意非常简单,但也化解了罗森岩和毕锡的难题。其实罗、毕二人之所以有这个分歧,也大半是人为制造出来的。
罗森岩虽然知道毕锡是林澹十分亲近的好友,但更清楚关大海对林澹的态度。他还不确定,关大海到底是真正追查刺客背后的主谋,还是只想给魁门弟子装出重视的样子。
林澹到底为何被刺,而且是被千里迢迢赶来的冒国血鹰所刺?
在罗森岩看来,这个问题虽然重要,但是远不如另一个问题重要。那就是,林澹如果真的死了,对魁门来说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更准确地说,对关大海来说,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如果是坏事,那当然要追查刺客背后的主使之人,为林澹报仇。
但,如果是好事呢?
这个念头在他的脑海中虽一飘而过,但留下了深深烙痕。
所以也就使得他在和毕锡讨论问题时,不由自主地,就在自己觉得应该制造一点分歧的时候,制造出一点分歧。
而毕锡之所以提出先审谁后审谁的问题,其实也有自己的考虑。
他的考虑,不是出于到底先审问谁为好。在他看来,这其实是无关紧要的。
紧要的只有一处,那就是无论审问老头或者女子,毕锡觉得自己都应在场。
林澹居然会在警备森严的魁门总部所在地被刺,对毕锡来说,这是无法想象的事。
无论从魁门的江湖超一流声望与地位,还是从林澹本人的身份与本事,这事似乎都不可能发生。
而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居然变为了现实,难道不值得深思?
也正因为此,毕锡觉得作为林澹的好友,义不容辞,必须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
他在昨夜得到林澹遇刺的消息后,坐立难安,既万分揪心,又莫名愤怒。好在关大海似乎洞察他的心情,命令接踵而至,让他与罗森岩一起审问刺客,这让他顿时热情如沸,也对关大海充满了感激。
只不过,经过大半夜的审问,两个刺客仍然闭口不言,这多少令毕锡沮丧。
但他可不是一个轻易服输的人。特别是现在,新找到了一张女刺客藏在婴儿被褥中的肖像,让他看到一丝曙光。
既然是同时开始审问,当罗森岩征求毕锡的意见,问他愿意去审问谁时,毕锡选择了那个老头。自然,年轻女子就留给罗森岩去对付。
毕锡饮了一大杯热茶,后背微微地出汗。踏着一地薄薄的白霜,前往审讯室。
这其实是一间罗森岩在自家宅院用来练功的房间,罗森岩取名“功舍”。现在,临时被改为了一间审讯室。
已近清晨,山谷里晨光点点。但是,审讯室不但门窗依然紧闭,而且所有的窗户都从头关上了厚厚的木板。这是罗森岩原来特制的设备,遮挡白天的光线,以利于他习练功夫。
毕锡来过一次,吩咐魁门弟子将木板关紧,让老头分不出现在到底是白天还是黑夜。
审讯室四周的墙壁上,安装着巨大的铜质灯托。灯托里点着熊熊的火把,将审讯室照得比太阳正午直射还要明亮。
老头被紧紧绑缚在审讯室正中的一棵大柱子上,上身光着,衣衫全被扒下。毕竟是冒国血鹰,得提防这个老杀手还有其他的招数。
因为在昨夜的审讯中已经上刑,老头上半身已经皮开肉绽,血迹斑斑。
毕锡对他可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悯,拉了一把椅子,坐在对面。
老头似乎听到声响,但是脑袋仍然耷拉着,仿佛睡着了。
或许他是真的累了。
也或许他是觉得自己已经完成了任务,抱着满足的心情,可以毫无牵挂地赴死了。
毕锡示意一个缙云堂弟子将老头弄醒。此事对他们来说易如反掌。据说他们至少有上百种法子,可以让任何人保持清醒,无法入睡。
当接连两个大铁钉被敲入老头的肩胛骨时,他微哼一声,睁开眼来。
毕锡看着鲜血从铁钉入肉的部位缓缓沁出,有意等了一会才问老头:“你愿意说点什么吗?”
老头一笑。
毕锡说:“我看你根本就不是冒国人,怎么做了冒国血鹰呢?”
老头还是微微一笑,嘶哑着说:“我当然不是冒国人。我是大全国北固郡燕南府人,是来给女婿报仇的。”
毕锡其实就是扯一个能让他开口的话线罢了。到底他是哪里人,暂时没打算细问,于是接着说:“你再硬挺也没有用的,反正你女儿已经招认了。”
老头从鼻子里往外笑了一声,“是吗?那你去问我女儿好了。”
毕锡说:“我只是告诉你,你女儿什么都招认了。”
老头说:“是吗?我女儿招认什么了?”
毕锡笑了笑,“你以为呢?”
老头摇头,“我没什么以为。”
毕锡觉得应该再敲打敲打他,说:“她藏画这么大的事瞒着你,你不气吗?”
老头一笑,“不气。再说我气有什么用呢?她是我女儿呀。”
“你真该好好想想,搞不好她还有别的事情瞒着你呢。”
“那我管不了,也不想管。”
毕锡叹口气,“你跟我们说说,你们是在哪儿碰到了齐天堂的衣衡?”
老头摇摇头,“我都忘记了。”
“你不告诉我也没关系,你女儿都告诉我们了。”
老头摇头:“我女儿能告诉你什么?她就是想说,也说不出什么来。”
毕锡见他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笑道:“你认为一个——母亲,”他有意把“母亲”两个字说得缓慢一些,“为了给自己的儿子保命,还会守口如瓶吗?”
老头的脸色非常平静,对毕锡的话毫无反应。
毕锡知道老头肯定是强装镇定。这张肖像上画着的孩子,必是年轻女子的儿子,他并未动摇判断。
他接着说:“她什么都愿意说,什么都愿意做,因为我们有她儿子的画像了。如果我们想在冒国找到她的儿子,不难。”
老头冷冷地笑了笑,“那不是她儿子的画像。再说了,她儿子也不在冒国。”
“不管她儿子在哪里,只要我们魁门想找,就一定能找到,这一点你不必怀疑。”
听了毕锡的话,老头又从鼻子里笑了一声。老头不是在嘲笑毕锡的话,而是嘲笑魁门的能力,这让毕锡有些恼火了。
不过,毕锡命令自己冷静下来。谁动怒,就意味着谁处于下风。自己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都已处于上风,为什么要动怒?动怒的应该是老头。
老头现在如此镇定,表现得十分冷淡,而且似乎不拿那女子儿子的性命当一回事,这应该正是老头愤怒的一种表现。
这也让毕锡确信,老头和女子只是一对杀手搭档。所谓父女的身份,不过是他们两人的一个掩护。
这种事在刺客行当并不新鲜,但也并不常用。因为两个没什么深厚关系的人,组成一对刺客搭档,彼此间很难建立真正的信任。
而彼此之间如果没有真正的信任,就很容易形成隐患。
刺客这个行当,不允许隐患的存在,因为隐患迟早变成明患。
那个女子私自藏了一幅小孩的肖像画,却瞒着这个老头,结果让自己找到了一个突破的方向,不正是一个明证。
但是他也意识到,没有必要再追问下去了。这个老头不会招供任何东西的。
年轻女子私藏孩子的一张肖像,这件事虽然让老头意外和震怒,但看来远没有动摇他的意志。毕锡慢慢地觉得喉咙里有些苦味。
掌握了这么大一张牌,居然打出去以后没效果,这是为什么?
毕锡很想狠狠地打这个老头一顿,毕竟是他射伤了林澹。但毕锡不是容易冲动的幼稚之人,这个念头虽然强烈,也不过只在他脑海里打了个转罢了。
毕锡从审讯室出来,心情有些沮丧,心想去罗森岩那边看看,不知他有没有进展。
罗森岩审讯女子的地方,是在缙云堂的议事室,与审讯室一院之隔。
毕锡顺着游廊大步而行,穿过一处厅堂,再过一道小门,就是议事室所在的小院了。在这处厅堂里,他看到了那个奄奄一息的病婴,被放在一个临时找来的婴儿摇篮内,身上盖着一床替换的薄被。两个魁门弟子在旁值守。
之前在病婴身上寻找线索时,是他和罗森岩、覃冕池一起,亲自细查了一遍。
他们重点检查了病婴的衣衫,以及裹着孩子的小被褥。最后,毕锡把被套上的线撕开,在被芯的一角,发现了卷成一个细筒的肖像。
病婴低低地哭泣,恐怕是饿了,或正在遭受病痛的折磨。哭声时断时续,似乎马上就要伴着他的生命一起,永远地消失了。
毕锡忍不住停下脚步,看了病婴一眼。可怜的孩子,身带疾病,却被卷入这种事,确实命苦。
毕锡也忍不住想,这个病婴的身上,应该再没有什么线索好找了吧?一念至此,他往病婴身边走近了两步。
但他很快明白,不会再有什么线索了。自己和罗森岩、覃冕池查得那么仔细,三人都是很有经验的人,绝不可能有任何遗漏。他心里一阵沮丧,停下脚步。
可能是他的脚步声引起了病婴的注意,孩子张开了眼睛。
想不到这个病婴,长了一双如此漂亮的大眼睛,黑瞳赛莫,白睛似雪,虽然眼光有些暗淡,但形状和颜色简直是太美了。
之前他在搜查线索时,可能因为是晚上的缘故,加之孩子身体太虚弱了,一直在沉沉昏睡,从没有张开过眼睛。而这时虽然由于听见了毕锡的脚步而睁开,但实在是太没有力气,很快又闭上了。
毕锡吃了一惊,却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自己为什么吃惊。
他在转身的刹那,心里微微动了一下,觉得有件事情十分奇怪。至于是何事奇怪,却并没想得十分清晰。
他一路走着,一路拼命想要拨开朦胧,把那件奇怪的事情找出来。但是越找,就越有些迷糊。当他走到缙云堂议事室门口的时候,脑袋里仍旧有些许疑惑,不敢确信自己的怀疑。
议事室门口侍立的缙云堂弟子见他走来,赶紧为他推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