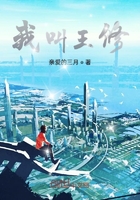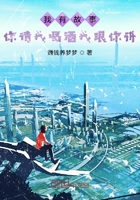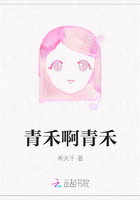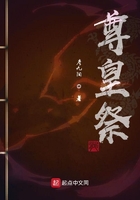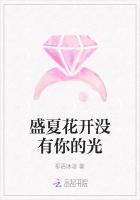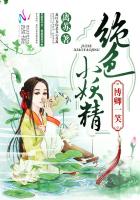一
时针刚刚指向五点,团湖冬天的早晨仍然有些朦胧。室外的房顶、角落依稀可以看到残留的白雪。晨曦相映之下楼宇上零零星星的灯光显得有些昏黄。道路上偶尔驶过的大多都是亮着空车灯的出租车。冷风吹过像梳子式的把街道上的塑料袋、纸片又向路边拢了拢。
李桂琴一个人在厨房里忙碌着。双眼煤气灶上的蒸锅冒着热气,大马勺中滋滋啦啦地响着。案板上被已经出锅装盘的和各种改刀配料的大大小小盘碗摆满了,有的甚至还叠上了几层。
“老刘,快起来吧!儿子好不容易回来一次。他睡懒觉,你也睡懒觉啊?要想睡等儿子吃完了你再睡。”
话音未落,两个卧室都传出了动静,但这动静都是从卧室到卫生间的,而不是到厨房的。李桂琴笑了笑,继续忙碌着。本来也没指望这爷俩能在一大早进入厨房,如果不是巴望着儿子在家里这几天多吃点好吃的,这爷俩爱几点起床就几点起床。
儿子不在家的时候,在周末、周日常常是李桂琴把饭菜做好,吃完了,独自出门了,都没听到除了偶尔打呼噜外身后的卧室有一点儿动静。
“妈!做了这么多好吃的!”刘昌明边穿衣服边从客厅向厨房探头道。“不赶趟了,妈!我要去接站,不吃了,走喽!”
“你说啥?你个小混球!我起了个大早,忙个底儿朝天,你还不吃了?晚上叫你早点儿睡就是不听,早晨起来就这出儿。不差这一会儿,坐下!吃!”李桂琴连珠炮似的数落着。
“吃!吃!吃!”没等妈妈把桌子摆好,刘昌明坐下匆匆忙忙地吃了几口,就走到门口忙着穿鞋。
“这个女孩漂亮吗?是不是你的女朋友啊?”
“妈你想多了,这是我的同事。”
“你都多大了,得长点心呐”
“知道了,亲妈!我走了!”
“还有这么多好吃的呢!”
“一会儿回来吃!”咣当!一声门响把话留在了门里,人却一溜烟的不见了。
“老刘!你瞅瞅你儿子,跟你一样!”李桂琴看着桌子上几乎没动的菜饭,又看了一眼厨房里还没端上来的盘子碗儿,心里和嘴里一起磨叨起来。
卫生间里明明有人,如果不是有香烟味道飘出来,整个房间似乎只有李桂琴一个人似的。自从刘昌明上大学离开家以后,这个家就像千千万万个东北家庭一样,只剩下了父母面对的冷清和对孩子的思念了。
刘昌明迎着清早的寒冷,沿着街边一边走着一边瞄着出租车。
东北冬天的早晨并非像传说和想象中那样,特别是暖冬现象的影响,即使在东北也已经难得感受到刺骨的寒冷。
出租车来了。打开车门,一股热气混杂着浓重的烟味扑面而来。刘昌明用手挥了几下,烟味逐渐淡了,露出了蓬头垢面的出租司机。
“去火车站!”两人几乎没有任何对话,出租车向火车站驶去。
“湘妹儿!”刘昌明装着几分湖南腔调拨通了索雅的手机。电话那边儿传来了咯咯的笑声。
“放心吧,帅锅,我丢不了!应该快到了!”
“下车不要看花眼了,东北帅锅可多哟。”
“你得护着点我,别把名满三湘的美铝抢走了,我可是人地两生啊!”又是一串咯咯的笑声。
刘昌明、索雅是北京一家民间咨询机构的同事。时下智库已经成为了逐渐被接受了的时髦的名字。形形色色的或所谓的智库在市场中各显神通,通过咨询、专题调研、策划等帮助企业、政府等进行科学决策。
受团湖市的邀请,刘昌明、索雅所共事的咨询机构选调人员,组成了工作小组来团湖开展双方拟定专题的工作。
刘昌明看了看车站的大钟,索雅乘坐的高铁还有四十多分钟到站,就站在出站口边上有一搭无一搭地随意看着。
在火车到站的间隙时间内,站前广场人员稀少。也许是有点冷,人们都躲进了周边的房子里和车里。在有客车进站时,伴随着广播声,人们就如同从地下冒出来般地把出站口堵得水泄不通。一个个旅店和短途客车接站的牌子高高举起几乎形成了一面墙。爆豆似的揽客声混在一起让人难以分辨谁在说着什么。旅客们闪躲着在人群中缓慢的穿行。
索雅乘坐的高铁进站了,出站口又是一片嘈杂。刘昌明一会儿低着头,一会儿踮着脚,躲开挡在眼前的牌子在人群中努力寻找着。
一个娇小的身影出现了,挥舞着两只白色长毛大手套,一眼看去活脱脱一个卡通毛绒大玩具。
刘昌明也微笑着挥着双手,分开众人迎上前去。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刘昌明张开双臂,索雅也大大方方的张开双臂,两人轻轻地拥抱在一起。
刘昌明一手拉着索雅的拉杆箱,一手拉着索雅躲开众多的牌子,在一片嘈杂声中走出了车站。
车站广场边上已经被杂乱无章停放的出租车堵得水泄不通。很多车里已经有人,但空车灯还都亮着,司机还在喊马上走马上走。刘昌明找了一台没有乘客的出租车,拉开门让索雅先坐进去。可是等了几分钟根本也不见走的意思,刘昌明就从车窗探出头问司机:“咋不走啊?”
“一个人10块,满人就走。不然你给50也行。”司机干脆的说。
“我刚过来才8块钱呐。这怎么还拼座呢?”
“现在就是这个价”司机的语气很坚定。
“这不是漫天要价吗?找管理人员去。”索雅小声说到。
刘昌明从车窗看过去,出租车管理牌子下的亭子空无一人。“算了,再找一辆吧。”两人下了车。
“饿了吧?我妈在家做了一桌子好吃的,走吧。”
“不方便吧”索雅略显矜持。“我们随便找个地方吃一口吧。”
刘昌明见索雅坚持只好作罢。
“吃点啥呢?”刘昌明问道。
“瓜子啤酒烤鱼片了!”索雅顽皮的把了字夸张地发成了劳,很明显她在调侃刘昌明。
“这应该是那些长期从事叫卖的人为了引起顾客的注意,特意提高了声调。时间长了就成了一个固有的腔调了。总的说起来东北的口音除了辽宁部分地区外,受过教育的东北人普通话还是最接近标准的。”刘昌明努力辩解着。
两人来到了一间粥铺,里面的早餐虽然算不上精致但也品种齐全。索雅简单的吃了点后,迫不及待地对刘昌明说:“快带我去看冰雪吧!”
“你最好休息一下,我们有的是时间,不着急。”
“我们不是明天才开始工作吗?反正今天没事,走嘛!走嘛!”
刘昌明非常理解一个从来都没到过北京以北的姑娘的好奇心。现在随处可见包装精美,艺术范十足的地域特色宣传资料,无论是纸质的还是电子媒体的,把各地都宣传的美轮美奂,让人心驰神往,让人忽然觉得身边几乎都是可以与世界美景相媲美的景色。东北到处都是冰清玉洁的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如同童话般的世界,让人完全忘记了在没害景色之外还有气候寒冷。再加上平时刘昌明等几位来自东北的同事对家乡的也许出自自尊的溢美之词,加上从广告中学到的什么东方滑雪胜地呀、梦中阿尔卑斯等等,让索雅这些很少见到冰雪的南方小姑娘的心里满是心驰神往。就连刘昌明这样的土生土长的东北人看到这样的宣传资料都有些恍惚了。
团湖市是刘昌明的家乡。因丘陵环抱的盆地自然形成的几个大大小小的圆形湖泊而得名,一条条河流把这些圆形湖泊链接起来,形成了不可多得的水乡景色。曾有人突发奇想把团湖改成与天池对应的名字—地池,但叫了一阵子没有流传开也就作罢了。从出生到上大学离开的那些年中,他并没有感到这个城市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在大学毕业后开始在北京闯荡打拼,每当来自其他省市的同事们谈起自己的家乡引起众人的夸赞时,刘昌明都不知道夸自己家乡什么好。后来逐渐接触了越来越多的来自东北大大小小城市的推介宣传材料,才发现这些年真是太孤陋寡闻了,自己几乎是“不识美景在眼前”。
随着人们的旅游热情越来越高时,东北好像不约而同地都开始宣传冰雪游、绿色牌了。各地冰雪游的水平互不服气,你超过瑞士,我赛过法国,北欧的童话世界更不在话下了。过分的夸张肯定是即来自文案的策划单位,也随了东北人特别是政府官员喜欢夸大的做派。
往往到了这个时候刘昌明也开始试探着,甚至夹杂了很多想象和发挥的成分来宣传团湖市的冰雪游了。这次索雅和同事们真的要到自己的家乡来了,为了让索雅们不至于失望,自己在刚下车就开始物色冰雪游的景点了。
天渐渐亮了,虽然比起南方有些晚,但亮起来也是不含糊的。路上的行人和车辆逐渐多了起来。市区里的双向六车道竟然堵起车来。长长的车流显现了这座不大城市的顽强活力。人们穿的颜色相对于春、夏和秋季是有点儿趋向于深色,灰色、黑色、蓝色、棕色居多,耀眼的红色、橘色、白色也偶尔闪过。厚实的冬装穿在身材高大有型的东北人身上是比较时尚的。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很少见到穿貂皮的了,天气逐渐变暖是一个原因,而时尚的力量是改变潮流的最大动力。
听表弟说在丰收水库的冰雪仙境是全市最高水平的冰雪游景点。
冰雪仙境距离市中心有十几公里,要坐城郊线中巴或打车去。
刘昌明和索雅来到了排在前面的中巴车前。汽车的发动机在轰鸣着,车门敞开着,车里已经坐了几位乘客。一个女子在卖力地大声揽客。索雅在车边的小贩手里买了一串糖葫芦,边吃边与刘昌明闲聊。
“这里的人蛮时尚的嘛,这个小城市穿的一点也不OUT。他们穿的好像并不比我多呀。”
“那是呀,你以为东北人像那些小品、短视频里那样穿着大红大绿,带着狗皮帽子,一边吸着大鼻涕一边讲着让人发笑的话呀?那些都是艺人编出来的笑料和创造的喜剧甚至闹剧的形象,你看到了现实中的东北人的素质还是很好的。各地人们都在改变,东北人也在改变。你看连我上学前到处可以看到的大大小小的貂皮都不多见了。穿貂的尤其是穿白貂的都成了你一样的扒蒜老妹的标配了。”
“臭美吧!你这是在唱谁不说俺家乡好啊”索雅笑着用糖葫芦指着刘昌明说道。
车开了,索雅的眼睛像不够用了似的,从车窗向外看着这新鲜的景象。车子越走,两边的白雪比市里越多了起来。
冰雪仙境到了。冰雪仙境地处群山环抱的小盆地之中,在一座自然湖泊后加人工修建的水库上构建的。从山上看过去就像一个大院套一般。入口是用从水库里取出的巨大冰块搭建的,围挡是木杆子扎起来的栅栏再积雪堆砌成的。大门上用红色装饰着冰雪仙境字样。在围挡上写着“冰天雪地就是金山银山”、“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兴市、农业富市、科技强市、外贸活市”等标语。
“两个门票”刘昌明把钱从窗口递进去。
“160元!里面都有什么呀?”索雅看着门票说。
“进去看看”刘昌明心里一点底数都没有。
一个个很难用艺术来描述的冰雕、雪雕兀自立在雪地上,或许刚制作完毕时应该比现在要好很多。可是经过了几个月的风吹日照,外形确实受到了损坏,就像风化了似的。
一座依地势搭建的轮胎滑雪道,游客们尖叫着紧随着滑了下来。用白雪堆砌的迷宫里,游客在追逐着,招呼着。
“快来看,这雪砖怎么越看越像糕点。”
“是吗?”刘昌明和索雅在白雪堆砌的迷宫墙上仔细看到。
“这你就不懂了。东北的雪不像你们南方,好不容易下了一场雪,太阳一出来就化没了。过了初冬后东北的雪就不化了,一场一场的大雪、小雪不断叠加就形成了这个样子。”
“可惜的是每层白雪之间都夹着黑灰和垃圾,看着很脏。若是没有这些该有多好啊!你看那边的白雪公主雪雕那是白雪公主啊,活脱脱是一个黑雪公主嘛!”
“冷了吧?”刘昌明关切的问道,心里也觉得无趣,巴不得早点结束。
“这里比不得城里,差不多咱们就回去吧,愿意看走之前再来。”
“有点儿,好吧,全听你的。”
两人走出了冰雪仙境大门。在大门口刘昌明用手机给索雅拍照,索雅摆出了不同的POSE.
“哎呀!”索雅用力拍了拍白色长毛大手套。刘昌明定睛一看,白色长毛大手套上一片黑色污渍。
“咋搞的?”
“好像是刚才扶着冰块弄的吧?”
两人到大门边上仔细看了看,原来远看晶莹剔透的冰块上,已经有了融化的迹象,表面上满是黑色的灰土。用手一滑,手指上便沾满黑迹。刘昌明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歉意。二人本想打一场浪漫童话般雪仗的美好想法也因为雪太脏而作罢,刘昌明尤其是索雅感到悻悻然。
“美女!帅哥!来一次飞的体验吧!”一个装扮成农村车老板的人牵着一只两条狗拉的爬犁招呼着。狗拉爬犁上铺着一铺破旧的棉被。
狗拉爬犁在这里的旅游业者戏称为“飞的”即飞行的的士。
“走喽!”狗拉爬犁跑了起来。
“哎,老板!这就是团湖最好的冰雪旅游点吗?”刘昌明问车老板,期待车老板给予否定的回答,以在索雅面前争回点儿面子。
“是啊”
“可是这和宣传相比也差的太远了”
“你还相信广告啊?别看广告看疗效!”车老板的话里透着幽默。
“你以为这是哈尔滨太阳岛还是长春净月潭呐?人家那是政府张罗了多少年才成规模的,人家那叫花多少钱?就说哈尔滨吧,哪年不花几个亿呀?咱这儿就是随帮唱影儿。政府不主导,每年交给个人来整,能整啥德行?老板想的只是赚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东北的领导要用新的角度来思考面临的形势和未来的发展,开发地方的优势。那是教他们解放思想,形成客观科学的新思维,把冰天雪地转化为优势的。可是有些领导只看前半句,把应该努力的事情扔到脑袋后去了。你啥也不干就挂个牌子,冰天雪地变成金山银山了?现在是滑雪场遍地开花,民俗村比比皆是。说句笑话你哪里要是连这些都没有,让贫困县都笑话你!再说了冰雪产业是要科学的规划和长期的投入的。你看看哈尔滨和长春吧,人家整了多少年了?下了多大功夫!想发展冰雪产业你也得有那个先天条件呐,和哈尔滨、长春的中心城市没法比,你再看看为啥北极村、雪乡、亚布力、天池、查干湖能吸引那么多游客就明白了,那不是当领导的一拍脑门就出来的。就凭这德行的领导光动嘴,想把冰天雪地变成金山银山等猴年马月的吧。”
“大哥你的见解实在是高”刘昌明竖起了大拇指。“你以前是干啥工作的?”
“别提了,早成了历史喽!”
“不如咱们建议林总请这位大哥给讲讲原生态的见解吧!”
“好主意!”
车老板一高兴吆喝一声,两条狗拉的爬犁真的有了点飞快的意思了!
索雅开心的喊着,脖子上的围巾飘了起来。
“我们回去吧?”索雅似乎余兴未尽。
“再不回去你就冻僵了,你的嘴都木了吧?。”刘昌明笑着说。
索雅咕哝了几下嘴,是有点僵硬。
“你说一句干啥”
“什么意思?”索雅不解。“嘎哈”索雅发出了嘎哈的音。
刘昌明笑了起来:“你的东北话接近标准了。这可能就是有些东北话形成的原因,你心里想说干啥,但嘴和腮帮子都冻僵了,不自觉地就说成了嘎哈。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方言习惯了。就像东北的大嗓门,东北地广人稀,说话的距离相对远不大声喊都听不到。跟着我慢慢长学问吧。”
刘昌明和索雅又回到了中巴车发车点。由于来的早返回的也早,回市内的游客很少,出租车又漫天要价,刘昌明和索雅没有事情就继续等中巴车发车。
车里人差不多满了,车主还在卖力的吆喝着。这时候忽然车前一片嘈杂。车主和一个人在车下说着什么。那个人光头,黑色夹克敞着怀,与眼前的气温和周边的人相比衣着单薄了些。
“前边的座儿给我留着!”光头命令似的。
“你谁呀?”车主问。
“不认识我呀?”光头反问到。
“跟谁说话呢?”车主话里有点火气。
“跟你说咋地?”光头的语气透着坚定的挑衅。
两人迅速进入了类似“你瞅啥?”“瞅你咋地?”的典型循环。最后车主败下阵来,嘴里一边嘟囔着,一边退让着,眼光扫向了别处。
“X!”光头在众人面前透着威风和得意。“上!”光头让自己的人上了车,好像车主根本不存在似的。
“坐你的破车是给你脸了”光头好像是说给车主的,又好像是说给自己的,更像是说给众人的。
车开了,车主的脸色一直阴沉着。
“下车!”三、四个学生喊道。
“一人4块!”车主说。
“不是2块吗?”学生们问。
“坐多远不知道啊?少一分钱也不行,**崽子!”车主提高了嗓门,夹杂了骂人的话,这话肯定是说给全车的游客听的。
学生们下去了,车主又自说自话般的说了几句自吹自擂的话,像扳回来一局似的。
“这个剧情有些看不懂啊。”索雅头顶着前排座椅的后背,侧着脸小声地向刘昌明说。
“一方水土一方人”刘昌明蔑视地说。
二人回到了宾馆。
“冷了吧?”刘昌明问。
“还好”索雅边挂外衣边说。“团湖市历史不长啊?”
“怎么见得?”
“城区不算大,在中心区很多地方都是企业名称的地名。”刘昌明暗暗佩服索雅这个小姑娘的观察力。
“名称虽然是企业,可是都变成了小区,这些企业都还存在吗?还是异地重建了?”
“这个?这个?现在不好准确回答。开始工作你就知道了。”刘昌明有些没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