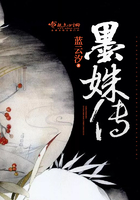“诸位,在下真气不济,不能久待,就此告辞了。”曾寿又旁听了半晌后,起身告退,然后在众人的注视下步入了雾霭中。但他却并未真的离开,而是心念一动,再次回到了千山之巅。
此时整条山脉在他的心神中并没有什么变化,但他却察觉出在重重迷雾之中还掩盖着其他一些所在,只是自己暂时还无从前去。这处逍遥谷似乎藏着许多的秘密,连冯尼、京西叟这些盘桓此地数十年的前辈们也都未曾窥其一角。
而自己似乎被授予了掌控它的权限,哪怕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已经能做到他们做不到的事情。就像现在这样,在闭着眼略微尝试了几次后,再次睁眼时,明显感到了一种踏实感,此时的他不再是飘渺无定的元灵,而是拥有肉身,一个完完全全的人。
之前元灵状态时,虽然能看能触能嗅,同样具有五感,但与此刻一比,方才的五感犹如套着一层薄纱,存在着并不真切的隔膜。而现在肉身置于逍遥谷中,却有一种如鱼得水浑然天成的错觉,让他顿时精神了起来。
进入蓄气阶段后,身体就像是一个布满空隙地纱笼,不时便有灵气从外界沁入体内,汇入经脉,融入丹田,然后又渐渐在体内消失。按照冯尼的说法,这整个过程叫做融炼,而自己所练的吐纳法会加速这一过程的循环,对灵气由被动的容纳变为主动的汲取,效率自然会更高一些。
而身处于逍遥谷中时,仅仅是站着不动,那灵气就从叶片上偶现的朝露变为山石间不绝的溪流,淌入自己的四肢百骸,比在外界修炼吐纳法时都要远远胜过。京西叟那句“这逍遥谷便是所有传闻中最佳的一处洞天”,还真是没有半点虚言,此处对修行的增益也远远超过了曾寿之前的期望。
于是他也不再作他想,直接盘腿坐下,反复修炼起了吐纳法,越练越觉得此地神妙,自己所获得的这根金手指,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粗……
曾寿专注地沉浸在逍遥谷修行中时,现实里月转星移,漫漫长夜被一束稀薄的晨光所驱赶,而午门城楼上鼓声钟声响便后,宫门开启,身着朝服的文武百官鱼贯入皇极殿,在殿堂中两班列好,而宁昌天子皇帝陛下则躺在软榻上被数名太监抬着出现在了朝堂。
前日得知幼子夭折后,原本身体就不好的皇帝昏迷了半日方才苏醒,经太医诊治后被告知并无大碍,只需静心休养便是。皇帝虽然对这些太医早就没了多少信任,但医嘱还是能听进去的,本来想罢朝半月,朝臣上下也应能体谅他,但没想到昨日又接连有事发生,让这位九五至尊不得不撑着病体来到朝会上。
耐着性子听完了朝臣们例行奏事后,宁昌帝环顾着殿下群臣,闷哼一声后方才缓缓声说道:“我听闻昨日发生了两件奇事,一是我儿朱先淳在宫内险些遭人行刺,一是宋王世子朱先泽在街巷中又被奸人暗袭。此二事,是造反,还是谋逆……”
他声音突然高了八度,带着满腔的怒意拍着御塌对群臣喊道:“有哪位卿家能为朕分说一番啊?”
朱先淳遇刺之事发生在昨日上午,有一人不知怎么混入了皇子寝宫,突然发难击伤了两名宫人,而刺客在冲往殿内的途中被数名太监拦下制伏,当时朱先淳恰好正在殿内读书。虽然此次刺杀并未能伤到朱先淳分毫,但让刺客混入宫中暴起伤人,已是多年不遇的大案了。令遇此案有关的大臣们各个如临大敌,在皇帝的怒火下瑟瑟不已。
“三法司,锦衣卫,出来!”宁昌帝伸手虚点,喊道:“这都过了大半日了,都查出了些什么,说!”
“禀圣上。”当下就有官员匍匐殿下,将他所知的案情尽皆道出,由于刺客已然自尽,且在自尽之前自毁了容貌,故他的身份仍未查明,但相助他混入宫里的几名守卫、太监已经被捕,已在狱中受审。
接着另几名有干系的大臣亦上前禀报,不过由于案情并没有太多的进展,只能像学舌一般勉强说上几句,到头来,刺客的主谋是谁,行刺的目的何在依旧是一团雾水。
这样的回答显然没办法让皇帝满意,他冷笑了两声,说道:“瞧瞧,这就是朕的大臣,查了一天就查出了这么点儿东西,真是好本事!”
在一片告罪声中,他又说道:“有谁能站能出来告诉我,为什么有人想谋害皇子,他们有什么目的,又是那些人最有嫌疑?!”
内阁次辅、工部尚书苏原听言出列上禀道:“久闻西林一党对皇子殿下素来不忿,私下多有诋毁,此事纵非其党徒亲手所为,也必有干系!”
他这一言顿时激起千层浪,诸多西林中人纷纷怒骂,“匹夫信口开河!”“无耻!”“苏贼你怎敢当廷欺君!”此起彼伏不绝入耳,直到首辅李良翰轻咳一声越众而出,方才让众人安静了下来。
对待曾经教过自己的李良翰,纵然皇帝心里不悦,,也依旧按捺住火气,轻声问询道:“先生,你如何看?”
“老臣并无断案之才,此事还须三法司竭力而为,旁人说的再多也是瞎猜。”李良翰慢条斯理地答道:“只是,老臣忽然记起万历朝一桩旧事,与昨日之事颇有相似之处,故愿陛下审思慎察,勿要轻信了奸人。”
所谓万历朝旧事,乃是史上有名的梃击案。经李良翰一提,便让众人都忆起了这桩旧案,当真与昨日朱先淳遇刺有诸多相似之处。只是当初那桩案子最后断的就稀里糊涂,万历帝不愿深究只是处死了犯人,没有找出幕后主使。过后对梃击案的看法更是众说纷纭,有说是那位宠妃意图谋害太子为自己的儿子争储,也有说是太子自导自演了一出苦肉计,目的是让自己的位置坐的更加稳固。
那么,皇子朱先淳有没有可能也是自导自演呢?不少人心里冒出了这样的念头。宁昌帝也沉吟了许久,方才说道:“三法司锦衣卫继续追查,尽快给朕一个答案。”
就在朝臣纷纷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却听他又说道:“宋王世子遇刺一事,你们又查出了什么结果?。”
朝臣们一愣,大部分人根本没有在意这件事,毕竟自宋王死难后,这位王世子就像透明人一般被大家给遗忘了。过了半晌才有人上禀道:“微臣从王府护卫口中得知,因那刺客在闹市中骤然伏击,遇阻后并未恋战飘然而去,现场除了一柄无主匕首之外并无其他线索,故实难以追查。”
“哈,这也查不到,那也查不到,我要你们何用?”宁昌帝又怒了,“是不是要等我朱姓男儿让人给杀光了,你们方才肯急一急,动一动?!”
堂下众臣又是纷纷告罪,皇帝重重地叹了口气,过了半晌,才继续说道:“吾弟迪格殁于国事,众卿对其带回的那纸合约颇有微词,但此乃战败之果,非他之过,我虽因先杰未能回来而归怨于他,但十几年过去了,也想明白了,此乃先杰命数于此,亦非他之过。”
“仔细思量,迪格他无愧于大明,亦无愧于我。而我若是连他唯一的子嗣都不能保存,他日泉下又有何面目去见他?”宁昌帝此时就像是一个追忆旧事的老人,过了许久方才继续说道:“先泽袭爵之事,我忘了,你们也没人提醒于我。这样吧,让他原等袭了宋王的爵,以酬吾弟报国之功。”
自重光变法之后两百年间降等袭爵已成惯例,原等袭爵的屈指可数的几个而已,这次也算是皇恩特许了。从回忆中走出后,皇帝正了正神色,又说道:“回到这两起遇袭的案子上,你们一个个一问三不知,但其实,我心底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无非是盯上了这个位子罢了。”他拍了拍身下的御榻,“你们一个个的都觉得我身体不行了,都在琢磨我身后之事了,对不对?”
“不用不承认,冠冕堂皇的话也莫说了,我今天跟你们讲讲真心话。”皇帝咧嘴笑了笑,“先淳和先泽遇刺看起来是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无非是觉得先清夭折之后,这储位没了悬念,不方便你们搞东搞西,所以硬要弄出点悬念来,对不对?”
“但不管你们搞出了些什么,这储位始终还是我说了算!”他铿然作响地说道:“我今天就把储位给定下,你们谁有意见,站出来!”
偌大的朝堂霎时间陷入一片寂静之中,连地位卓尔的李良翰都默然噤声,不去触这个霉头,宁昌帝眼眸肃然的扫视过群臣之后,将目光落在角落的一位苍发老道身上。
老道原本微眯着眼睛似瞑如睡,好像在神游物外一般,却陡然间越众而出,朝皇帝行了个道揖,朗然回应道:“若储位传承仅为皇家家事,道录司上下自无意见。可此事关乎苍生社稷,陛下身体尚健,切不可仓促拟定,万望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