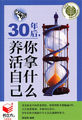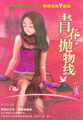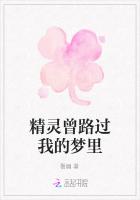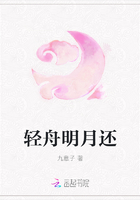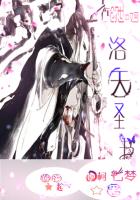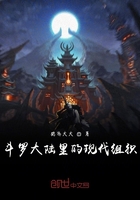谢希德(1921~1999年)物理学家,福建泉州人。留美。回国后,任复旦大学教授、校长。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书籍好比食品。有些只须浅尝,有些可以吞咽。只有少数需要仔细咀嚼,慢慢品味。”复旦大学谢希德教授是深知此理的。谢希德是中国表面物理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之一,但她读书面很宽,有专业本行的书籍,也有人文学科和文艺小说。可见要成为一个大科学家,需要非常广博的知识面。
有些书甚至要达到逐字逐句地去理解
谢希德的父亲是燕京大学物理教授,除了做实验,就是关在书房里备课、写文章。父亲的书房有许多书,在谢希德眼里好像是一座宝库。
每当父亲白天外出做实验时,谢希德便悄悄地溜进书房,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本书,随意翻阅。最初只能了解书名,或凭一些插图猜测大意。谢希德的童年,可以说主要是在父亲的书房里度过的。读书成了她生活的第一需要,书籍是她亲密的伙伴。正是在那书屋里,她接触到中国古典名著《水浒》、《儒林外史》等,书中有趣的故事,经常把她吸引住。她还喜欢读外国童话,有时看不懂,就多读几遍,不知不觉地就给迷住了。由于课外书阅读得多,智力得到早期开发,学习进步很快。读完一年级,通过考试,她的智力又超前了,于是就跳到了三年级。中学时代,她养成了预习的好习惯,自学能力很强,数理化和外语的成绩,一直名列班级前茅。
关于读书,谢希德经过长期的实践,总结出以下几条经验:
第一,读书首先要掌握正确的方法。要从各人的实际情况和学习的目的出发去读书。读书要精读和一般浏览相结合,有些书一定要精读,甚至要逐句逐字地去理解,不懂的地方务必要弄个水落石出,随后要通过深入的分析与思考去掌握必要的内容。而另外一些书,则仅需浏览即可,因为时间太宝贵,而要学习的知识太多。
第二,读书不仅在于扩大知识面,而且要与提高实际能力相结合;要带着问题学,在学习中结合实际,解决问题。文科学生要自觉利用社会调查的机会,学会分析材料,提出自己观点,为社会服务;理工科学生,必须主动适应实验室或工厂对自己的要求。高年级的学生还应提早接受科研小课题,写作小论文,搞科技小发明等活动;在校大学生应投身到科技创新活动中去,在社会大课堂里,将书本知识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
谢希德反对钻牛角尖的学习方法,认为如处处钻牛角尖,就会把本可乐在其中的读书之事弄得枯燥无味,日子过得紧张万分。她自己在读书与研究过程中,不时读一些可以放松情绪的小说、传记文学,用以陶冶情操,丰富业余生活。
学人文科学的,也要读一些自然科学
正如谢希德所说,她爱书如命,几乎天天要看书。中学时,她的右腿患股关节结核,躺在床上,还手不离英语书,记单词,背句子,正是这样的刻苦读书,为她后来英语获得优异成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文革”期间,谢希德莫名其妙遭到隔离审查,身心受到摧残,仍凭顽强的信念生活着。她淡泊宁静,不为自己处境而怨恨,但是,当不让她订阅科学期刊时,内心特别气愤。后来,她被允许回家,获得自由之后,便又投入到科学研究中去了。有一本新出版的英文版《电荷耦合器件选集》,虽然书价昂贵,她还是下决心买了。她深知,只有学习和掌握最新的科学知识,才能赶上飞跃发展的科学时代。
1976年,正当她满怀壮志,准备带研究生到四川永川县搞电荷耦合器件时,右侧胸部又发现癌症的征兆。这正是她与乳腺癌作第三回合较量的时候。
每次治疗都引起反应性呕吐,白血球大量减少,身体出现浮肿。接着医生又用中药治疗扶正,以便迎接第二轮的化疗。这样的治疗无疑是痛苦的。但是病魔愈折磨她,谢希德的意志便锤炼得愈坚强。她仍然夜以继日地阅读文献资料,把重要内容摘录下来,记在卡片上;依然对研究生进行业务指导;照样对教师的译稿作认真的校译。
一位出版社的编辑是这样描述谢希德的:
“有一次,我一进谢先生的房间,看到她面色苍白,有气无力地坐在沙发上,心里顿觉歉疚,不该在这时再给她增加负担。但是,她一看到我给她拿来几本较新的关于‘表面科学’的书籍,喜出望外,精神也抖擞起来了。她马上打开书,翻一遍,口里连连说:‘好书,好书,对我们工作很有帮助,你看,借给我几天?’
“我看到她身体如此虚弱,就说:‘看你的情况吧!’
“‘过四天准时还你吧’,她说。果然四天之后,她准时托人把书还来。我接到书,心潮翻滚,谢先生真是为了科学事业忘记了一切啊!像她这样把病痛置之度外,而对科学研究和科学事业如此专注的,这在动乱的那几个年头,我确实所见不多啊!”
谢希德之所以如此爱读书,其中的一大原因,就在于她对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一个超前的认识。她认为,随着科学的飞速发展,知识更新的周期越来越短,这就要求我们更要善于学习,掌握不断涌现的新知识,并将它运用到科学研究和开发中去。只有爱读书,才能掌握前人给予的丰富知识财富;只有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才能适应日益发展的多学科交叉、渗透的实际需要。所以她一贯鼓励学生选修一些跨系、跨专业的课程,以扩大知识面。强调学自然科学的要懂一些文史科学;学人文科学的,也要懂一些自然科学。即使是外语专业,如果没有必要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要做起码的翻译工作也是很困难的。
要用通俗语言写书
吮吸书籍提供的科学知识乳汁,经过消化吸收和创造,谢希德撰写了一部部科学著作。
50年代,她与物理学家黄昆合编的《半导体物理》一书,旁征博引,论述严谨。全国各大学半导体专业,都采用这本书作为必读教材。到了60年代,谢希德与方俊鑫合编了《固体物理》上下册。之后,她又在《固体物理学》下册中写了“非晶”一章,于1982年出版。另一本著作《群论及其在物理学中的应用》,也于1986年由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
谢希德不仅认真对待自己的著书立说,还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对待科普书新世纪版《十万个为什么》。这部书由中国科学院原院长卢嘉锡挂帅,谢希德是该书编委之一。谢希德在接受《文汇报》记者采访时说:“写科普文章有相当大的难度,主要是要用通俗的语言,把基本科学知识告诉青少年和普通老百姓,怎样在短小的篇幅里,将事情写清楚,把问题讲明白,这是很不容易的。”
谢希德举了几个生动的例子。为了这部书稿,她在病榻上修改两篇关于微电子技术和集成电路的文章,发现作者把“硅片”和“芯片”两个概念混淆了,便立即指出,还在稿纸空白处画了一个简明易懂的示意图,可见其认真的程度。还有一个地方,作者为求形象生动,用“指甲大小”四个字来描述一个微小的面积概念。谢教授说,男性的手指甲和女性的手指甲相差很大,即使是一个人,小拇指和大拇指也是不能比的,所以把它改成了“一平方厘米见方”这样较为精确的写法。有的表述方法不能确认,谢希德当即打电话回复旦大学,征求同事们的意见,有时就干脆和来访的同事、学生在病房里讨论开来。这里,我们又看到了谢希德严谨的科学态度。
吕慧芳复旦大学美国问题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