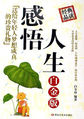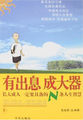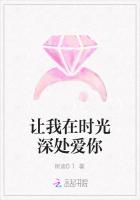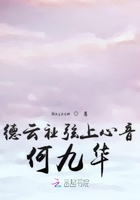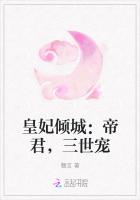陈旭麓(1918~1988年)史学家。湖南湘乡(今双峰)人。建国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近代史思辨录》等。
历史学家陈旭麓从40年代初期,就写了一大批富有情致和理趣的时论散文和学术论著,其中的一些文章被人誉为是中国当代文化中最富个性和理性神采的。取得这种成就,与他的博览群书是分不开的。
“无日不在读书”
陈旭麓常说自己“读书成癖”。80年代,他在一篇文章中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无日不在读书,晚间上床得看一阵书,半夜醒来还会扭开灯读书。”“读书是积累知识,也富有生活情趣,读到会心处你会发出笑声,读到动情处你会冒出泪花,读到邪恶处你会愤慨不已。”由此可见,读书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陈旭麓的读书爱好是从小培养的。他幼年丧母,父亲通过作些小买卖,使家境逐渐好转。1926年,陈旭麓开始入学读书,在这一时期,主要阅读私塾先生规定的《左传》、《诗经》、古文、唐诗等,对朱熹的《近思录》等书也有所涉猎。
陈旭麓家庭世代经商,他的父亲只想让他通过读些书,学会记帐、通信就行了,以后可以继承祖业经商。但是,陈旭麓没有接受父亲这种安排,而是要求继续读书。1934年,他离开湖南湘乡,来到长沙就读。
长沙是湖南的政治、文化中心,有很多新式学校。陈旭麓在私塾中所读课程,大多数无法与新式学校接轨。因此,他无心领略省城的都市风光,一头埋进书堆,补习数学和英文,为进入新式学校作准备。不过,最终却进了长沙孔道国学专科学校,在那里学习了三年,课程包括经学、史学、哲学、地理学等。
1938年,陈旭麓通过老乡介绍,进了大夏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开始了他一生中的重要转折。然而好事多磨,他在大夏读了一年后,忽然被查出没上过新式学校,也没有正式中学毕业文凭。校方通知他,已学的成绩全不作数,要求重新从一年级读起。陈旭麓没有办法,只好服从,但不愿再读中文系,于是转入历史社会系。这一改变,无形中竟为中国造就了一位历史学家。
大学毕业后,陈旭麓在教书的同时,继续多方涉猎,增长知识。1946年回到上海,他先后在大夏大学等学校教书,从此和书结下了不解之缘。读书成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无日不在读书”。
在长期教书育人、从事学术研究的过程中,陈旭麓收藏了大量的书籍。虽然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所藏之书一度被弄得残缺不全,但还是遗存了不少。1982年给友人的信中说,“搬家的事已基本就绪,几个研究生帮我把书清查了一番,因为书架少,仍是摆不开,好些书只好捆成一堆。”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说,懂得如何启发,是教育的伟大本领。这也是陈旭麓的一大特点,他很善于指导青年学生读书。他认为教育不是把人变为机器人,而是培养人去制造机器人,“教师要像恋人一样去诱导年轻人的心扉”。因此,他平等待人,经常鼓励学生在读书、学习的过程中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并因材施教,使学生发挥自己的特长。“不管人们说我有多大的过失,只要我对青年的成长有过一点热情和帮助,我就心满意足了。”
同学们给他取了一个绰号“牛克斯”
陈旭麓说:“读书历来有精选和博览两途,从而造就了专攻和通才两类人。”他认为,任何学问都必须专攻才会有所成就,然而任何学问又是和许多学问互相联系的,不广窥博览就难以豁然贯通。在他看来,读书,必须处理好精选和博览的关系。任何学科都是复杂的、丰富的,都必须广征博采,都需要“从你的视野之外获得视野之内的营养”。对此,陈旭麓谦虚地说:“我好读书,好书读两三遍,未必作到精选,读得广一些,也谈不上博览,只能说有这两个愿望。”
早在长沙孔道国学专科学校就读的时候,陈旭麓除了阅读经史子集外,还广泛阅读各种书籍,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陈独秀的《独秀文存》等。在大夏大学读书期间,除了学习哲学、历史、文学、外语等规定课程外,他还广泛涉猎《论持久战》、《资本论》、《联共(布)党史》等书籍。他被这些书深深地吸引了,接受了书中的辩证法、唯物论观点,以至在和同学交谈的时候,开口就是“生产力”、“生产关系”,闭口便是“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结果,同学们给他起了个绰号“牛克斯”。
陈旭麓读的书范围虽很广泛,但并不是漫无目的。读马列,读有关理论方面的书,是希望从中得到诱导和启示,但是“只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决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要面向实际和读马克思主义以外的书,才有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他读其他社会科学的书是为了开阔视野,读文学方面的书则是出于对社会的探索,甚至“杂七杂八的书”也读,是“因为其中有你需要而在别的书中得不到的东西”。
史书是陈旭麓的专业领域,自然属于精选的范围。然而古往今来,史籍浩如烟海,穷个人毕生精力,也不可能全部读尽,甚至读完其中的一部分。因此,读历史书籍也必须有选择,需有高明的甄别力。作为史学家,陈旭麓在这方面有自己的心得。他认为读书,特别是读历史书籍“不要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不要被评论家所捉弄”,必须具备史学家的史识、见解和辨别力。1979年,他发表了《漫谈学习中国近代史》一文,虽然其重点是谈如何读中国近代史方面,但对指导人们阅读其他方面的书,有着同样的可借鉴之处。
读书还需有个积累的过程。任何一门学科,如果要比较全面、深入地了解它,进一步掌握它,不能浅尝辄止,这决不是一次两次可以完成的,而必然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特别需要把握住重点。陈旭麓主张,在读书、学习的过程中,应当“避免那种东抓一把,西碰一下,看得虽多而只有一些杂乱无章的知识。”
“读书的真正价值和最大乐趣,是经过艰苦研究得来的东西”
陈旭麓反对为了读书而读书,为了学术而学术。他认为,“读书的真正价值和最大乐趣,是经过艰苦研究得来的东西,当你多年没有获得的知识一旦获得了,多年没有弄懂的问题一旦弄懂了,你就会大乐,没有原先的艰苦就享受不到大乐。”
陈旭麓在读书过程中,勤于思索,从而读书常有自己的观点。大学还没毕业,他就将自己多年积累的读《史记》的心得,写成了他的第一篇学术性论文《司马迁的历史观》。这原是一个很难驾驭的题目,他却洋洋洒洒地写了三万余字,文章发表后,受到各方面的好评。老师和同学们纷纷说:“你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陈旭麓在读书过程中除勤于思辨,还善于发现问题。他在《(近代史思辨录)自序》中说,“在教学准备和阅读史籍中,日积月累,熟悉的东西多了,以此及彼,就会产生疑团,就会有问题从书中跳出来,不容你不去思辨,不去搜集资料进行论证,终至一吐为快。”
陈旭麓擅长思辨、善于发现问题,其结晶是他的遗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从1978年开始,他以“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为题,给研究生和青年教师授课。他抓住在读书、授课中闪现的思想火花、思考所得,将之形成论文。1988年,陈旭麓打算把讲稿形成专著时,却不幸去世。最后,由其学生整理出版,完成了陈旭麓的遗愿。
为别人阅稿作序或撰写书评,是陈旭麓晚年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显然要占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是为他人作嫁衣的事。尤其在行文之前,要读很多有关的书籍,但他却把为人撰写序言和书评,作为激发自己思考的一次机会,很少就书论书,往往一篇书评或序言就是一篇见解独特的论文。他的一封信中,曾提到这样一件事:“春节前后的三周,审阅了一个老门生写的《道光皇帝传》三十万字。……为了写序言,倒也使我思考了道光是个怎样的皇帝。我说他既不英武,也不昏庸,是一个勤政图治而无显著政绩的皇帝,比许多瘟皇帝好。但他的两只脚随着五口开放进入近代,他的脑袋仍留在中世纪。”
陈旭麓也特别乐意为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作序,“每从他们的笔下看到年轻人特有的才思,听到年轻人大步前进的足音,那愉悦之情总久久不能自已。”他认为,“个人的生命像大海里的一滴水,如果把这滴水洒在绿荫成长的泥土上,它就会比一滴水大得多。”他甘作人梯,相信爱因斯坦所说的话,“能培养独创性和唤起对知识愉悦的,是教师的最高本领。”由此,他赢得了无数好学青年的衷心爱戴。
陈旭麓的一生可以说是和书打交道的一生,他自己说“教书、写书、学生是我的支柱,离开了这些我就不存在了。”而读书、作学问,“只有执着地‘众里寻他千百度’,才能出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境界。”
孟庆龙上海商业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