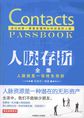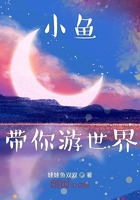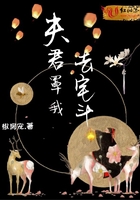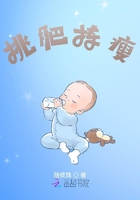茅以升(1896~1989年)桥梁工程学家。江苏镇江人。建国后任交通大学校长、铁道研究所所长。著有《钱塘江桥》、《中国的古桥与新桥》,主编《中国古桥技术史》,有《茅以升文集》。
在茅以升家的客厅里,长年累月挂有一副对联:礼乐本百圣,桥梁通八荒。那是1920年柳诒徵为年方二十五岁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茅以升所写的。在此后的几十年间,茅以升设计、主持了国内很多桥梁工程,也写了不少有关桥梁建筑的专著和通俗作品。他的文章有实践有理论,文采也好。
1963年茅以升写的《桥话》在《人民日报》发表后,毛泽东称赞他说:“你写的《桥话》我都看了,写得很好,你不但是科学家,还是文学家呢!”
他看着祖父抄完了《阿房宫赋》,竟然把它背诵出来
茅以升出生在江苏镇江的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从小就接受传统文化教育。
儿童时代的茅以升就懂得要读书的大道理。读书的道理是什么呢?很简单:一是能有做人的知识;二是有办事的能力。对茅以升儿童时代最有影响的一个人,是他的祖父茅谦。
在茅以升刚出生几个月,茅谦就举家从镇江迁居南京。他迁居的目的,是因为南京文化发达,可以为未来的孙辈开阔眼界,增长学识,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茅谦创办了《南洋官报》,并出任总编纂。他将在戊戌时期写的《变通小学议》重新刊载。这篇文章曾在戊戌变法时期印成小册子风行江南城乡。它提出“教习儿童生气勃勃的白话文,废止八股文”、“读书要先理解再背诵”,“不贵多而贵精,读一句书,皆能讲解明了,便得一句之用”等观念,在当时确是创见,茅以升启蒙伊始就奉此为座右铭。
茅以升爱读书。他十岁就考进了全国知名度极高的江南中等商业学堂,学习新知识,接受新道理。他的求知欲极为旺盛。由于老师柳诒徵的影响和鼓励,引起了学习古文的兴趣。他常到祖父藏书的小阁楼去找古书读。小阁楼上挂有一块横匾:一家终日在书楼。茅以升每当见到它,就会升起要把阁楼里藏书读完的愿望。
有一天吃晚饭时候,茅以升失踪了。后来还是祖父从小阁楼闪闪发亮的灯光中,找到了正在聚精会神读书的孙儿。祖父没有责备,反而称赞了他。
祖父教他读书,所选的第一篇范文是唐王勃《滕王阁序》,授教方法也很别致,即用毛笔抄录一句,讲解一句,待全篇讲授之后,要他回去背诵。
茅以升只用了半天,就背熟了。
祖父还对他说:“读书务求其通,仅会背诵还不行,还要会讲会写。”又说:“相传王勃幼年读书时间久了,嘴角生了口疮;写文章时间久了,手指磨出了老茧。因而能一气呵成《滕王阁序》。其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还成为千古绝唱的佳句。”
茅以升牢记在心。
他以勤学苦练强化了记忆力。一个人能强记,过目不忘,乃是靠少年儿童时期的艰苦磨练,这里所谓的天赋,只能是微乎其微。茅以升苦读的一大收获,就是记下了很多佳文佳作。有次祖父抄写唐杜牧的《阿房宫赋》,他站在旁边看,祖父抄一句,他念一句;抄完了,他竟然能全文背诵,不错一字。
凡是中华大地的名桥,他都能引上古诗
1989年茅以升逝世后,先后出版有关他事迹的三本传记:一本是公盾《茅以升:中国桥梁专家》;一本是茅玉麟、孙士庆《中国桥魂茅以升》,还有一本是镇江政协主编的纪念文集《桥梁专家茅以升》。
三本书的书名都离不开“桥”。
茅以升一生确实与桥结下了不解之缘。
20世纪30年代,他主持设计和建造了中国第一座铁路公路两用双层现代化大桥,被称为“中国近代桥梁史划时代的里程碑”;50年代,他出任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为建设共和国第一座大桥做出了卓越贡献。
茅以升与桥结下不解之缘,和他早年生活经历有关。
1905年,茅以升九岁,这年的端午节南京发生了一件大惨案,秦淮河上文德桥因为年久失修倒塌了,不少人就在这座石横桥上落水身亡。茅以升目睹倒塌的文德桥惨状,他情绪十分激动,表示将来长大了要造桥,要造好桥,让千千万万的人们平安通过。
从此他对有关桥的书本和文字产生了浓厚兴趣。凡读书,遇到有桥的记录,就随手抄写在本子上,看到有桥的图画就描绘起来。
他数十年如一日从中国古书中搜集有关桥的文字,从小做到了老。这对他日后写古桥很有帮助。比如在谈成都万里桥时,就用了杜甫诗“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张籍诗“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宋苏轼诗“我欲旧寻万里桥,水花风叶暮萧萧”,陆游诗“雕鞍送客双流驿,银烛看花万里桥”;在谈河北赵州安济桥时,他用了唐人笔记《朝野佥闻》所称“如初月出云,长虹饮涧”,以及宋杜德源《安济桥》“坦平简直千人过,驿使驰驱万国通”,元杨鱼《安济桥》“五丁凿石极坚顽,陌上行人得佳还”,等等。凡是中华大地的名桥,他都能引用古诗古文说明。
中国古书里有无数关于桥的文字。文革期间,百事俱废,茅以升为了不虚度岁月,与老友夏承栋、陆师善同心合力,以三年时间,翻阅《全唐诗》、《全宋词》和元曲名家选本,凡是有关桥梁的文字,以及与桥梁有关的悲欢离合故事,如蓝桥相誓、断桥相会,均作搜集、抄录,并作考证与注释,尔后用工整小楷抄录在稿纸上。茅以升自己装订,设计封面,取名《桥话》。这部厚达一米的九册《桥话》,堪称是古中国桥梁诗词考证和注释之大成,它所收集桥梁文字数量之最,是可以写上吉尼斯世界记录的。
从地方志里寻找桥的文字
茅以升长期以来从书本中汲取有关桥文化,搜集桥梁文字。他读过《永乐大典》(残本)和《四库全书》;也翻过魏晋以来笔记野史,如从王嘉《拾遗记》中发现古代曾用鼍背为梁等等。
他积累古桥梁资料,其中一个来源是地方志。茅以升读过许多地方志,仅从他所写的中国桥梁史大小著作中所引用的,估计就不下一千种。比如:从《福建通志》引用洛阳桥建造故事;《山东通志》引用北宋真宗(赵恒)赴泰山封禅,途中所铺的“席桥”和青州月样桥;《浙江通志》所说的东汉孙钟的富阳“瓜桥”、余杭葫芦桥、绍兴相传的晋王羲之兰亭桥;《江南通志》安徽建平(朗溪)“暗桥”;《山西通志》太原“赤桥”、赵城国士桥;《湖广通志》孝感绩麻桥、黄州海棠桥、石首照影桥、蕲水绿杨桥;《贵州通志》平越(福泉)葛德桥;《四川通志》成都万里桥、升仙桥、广安至喜桥、康定泸定桥、灌县珠浦桥;《河南通志》汝州洗耳桥;《江苏通志》邳县圯桥;《江西通志》饶州(波阳)胭脂桥,王公桥,安福白鹤桥等。
百尺之楼,非一朝而建。茅以升就是从书中大量汲取有关桥的文化,这样一步又一步地走上一座座的大桥、小桥、木桥、石桥和铁桥,然后又走下桥,读书、思索、再读书、再思索,从而成为世界级的桥梁专家。
朱守芬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