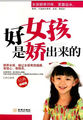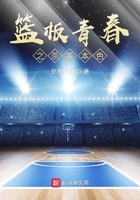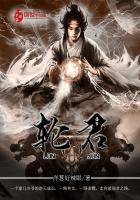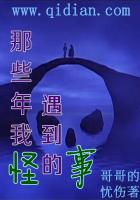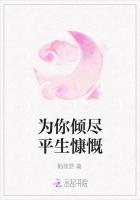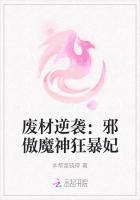齐白石(1863~1957年)美术家。湖南湘潭人。建国后,任中央美术学院名誉教授、中国画院名誉院长。有《齐白石作品集》。
齐白石为什么能在艺术道路上不断进取,最终成为艺术大师呢?勤奋好学,是齐白石成功的秘诀。俗话说:“三分天资,七分努力”,齐白石的读书求艺,正是经过了千辛万苦的艰难跋涉,才到达了胜利的彼岸。
打柴时把书挂在牛角上
齐白石出身在贫苦农民家庭,从小聪明好学。四岁时,祖父教他认字,不多久就掌握了三百多个汉字。祖父教不了他了,就送到外祖父的私塾去上学。尽管外祖父不收他学费,但是家里还供不起书簿纸张等必需的文具,不到一年,就不得不辍学。
但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学会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书读得非常好,常得到外祖父的夸奖。学习之余,画画的天分开始显露。他经常画雷公神像送给小朋友,画得次数多了,越画越好,平时看见过的东西,如牛、马、猪、羊、鸡、鱼、虾等,皆能栩栩如生地画出,因此描红纸用得很快,惹得外祖父也生了气。
辍学回家后,他每天上山砍柴,又帮着家里做事。上山砍柴常带着书本,忙中偷闲,读学堂里未学完的《论语》。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去问外祖父,隔不多久,一部《论语》居然都读完了。回到家里,仍旧是写写画画,搞得祖母非常不高兴,说:“三日风,四日雨,哪见文章锅里煮?可惜你生错了人家!”他明白祖母的意思,后来打柴时总是把书挂在牛犄角上,先打够了柴,再读书,没耽误正事。齐白石老年有《忆儿时事》诗:
桃花灼灼草青青,乐事如今忆佩铃。
牛角挂书牛背睡,八哥不顾唤侬醒。
还刻了一方印章:“吾幼挂书牛角”,都是纪念儿时的事。
家里的活计很需要人手,齐白石跟着父亲下田,终因身单力薄,干不下去了。父亲鼓励他学一门手艺,将来好养家糊口。他拜了木匠为师,学起了大器作。大器作又称“粗木作”,活儿比较简单。他羡慕那些做小器作的,能做精致小巧的东西,还能雕刻花。于是放弃了大器作,拜一个雕花木匠为师,学作雕花手艺。齐白石学得津津有味,十分刻苦,满师以后,他的手艺已比得上师傅了。
二十岁时,齐白石无意中得到一本《芥子园画谱》,这是一本清人所编的画谱,山水人物,翎毛花卉,应有尽有,形色俱全。他爱不释手,用透明竹纸描绘,从头到尾,共描绘了三遍,足足用了半年的时间,将整本《芥子园画谱》勾影完毕。以后不再看谱,就能绘出各种花鸟、树石。有了这本画谱,他做起雕花活,更是推陈出新,变化无穷,手艺远远超过了师傅。
字不必多写,而是要多看帖
齐白石白天做雕花活,晚上就着松油柴火画画。当地有个叫胡沁园的画师对他很赏识,鼓励他读书学画,并愿意收他为学生。齐白石因囊中羞涩不敢答应,胡沁园说:“那怕什么?只要有志气,一面读书学画,一面卖画养家,也能对付得过去。”齐白石不仅担心穷,还担心自己年龄大了,怕来不及。胡沁园又说:“你是读过《三字经》的,‘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你今年二十七岁,何不学学苏老泉呢?”他又向齐白石介绍了名士陈少蕃。从此,齐白石学画跟胡沁园,读书随陈少蕃,有了这两位老师,他的人生道路如同点亮了两盏明灯,指导着他探寻艺术的奥秘。
齐白石勤奋好学,买了一本蘅塘退士孙洙的《唐诗三百首》,下决心要把它全部背诵出来。开始遇到不少生字,在请教别人后,就用图画绘意,比如张九龄《感遇》“江南有丹桔”,就在“丹桔”字旁绘一只红桔子;《古柏行》“苦心岂免容蝼蚁”,就在旁绘一只小虫,如此等等。这样,仅用了两个月就将《唐诗三百首》一字不漏地背出,直到晚年,仍能背诵如流。有些诗,当时虽然不理解,但因为能背诵,久而久之,也就懂了。接着,又读了《孟子》、《聊斋志异》,在陈少蕃的教导下,他发奋用功,诗文写作也有了不少成就。跟胡沁园学画,学的是工笔花鸟草虫,胡沁园把收藏的许多名人字画指点给他临摹。如此读书学画,有吃有住,心境安适,眼界也广阔多了。七十岁时,回忆往事,他做过一首《往事示儿辈》的诗:
村书无角宿缘迟,廿七年华始有师。
灯盏无油何害事,自烧松火读唐诗。
齐白石常说:“没有读书的环境,偏有读书的嗜好,穷人读一点书真不容易。”语出肺腑,发人深省。
三十岁时,乡里人奔走相告说他画的画,比雕的花还要好,一传十,十传百,前来求画的人越来越多。家里靠了他这门手艺,光景有了转机,祖母说:“阿芝!你倒没有亏负了这支笔,以前我说过,哪见文章锅里煮?现在我看你的画,却在锅里煮了!”
齐白石在读书学画的同时,还学会了裱画,其技艺不在画画之下。后来他参加了“龙山诗社”,任社长。牡丹花盛开的时候,胡沁园约了诗会同人,一起赏花赋诗。齐白石作了一首七绝:“盛名之下岂无惭,国色天香细品香。莫羡牡丹称富贵,却输梨橘有余甘。”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诗友们报以热烈的掌声。胡沁园说,这首诗不仅意思好,韵也押得很稳。
齐白石的字学馆阁体,临历科翰林的殿试策,讲究圆润腴满,一笔不苟,没有一点碑帖气息。到了胡家以后,看了胡沁园与陈少蕃两人写的何绍基的字,腴润中有笔力,他又跟着二人学何绍基,后再学金冬心,最后专心学李北海。他非常喜欢云摩碑的字,有一段时间,他天天看云摩帖,休息时就把字帖带在身上,走路时看,坐车时看,久而久之,以至闭了眼也能看到帖。他把碑帖的字体记得烂熟,提笔往往一挥而就,浑然天成。因此他后来很有体会地对学生说,字不必多写,而是要多看帖。
齐白石曾拿着自己的诗文字画及刻的印章,拜见湘潭大名士王湘绮,请他评阅。王湘绮说:“你画的画,刻的印章,又是一个寄禅黄先生哪!”寄禅是湘潭有名的和尚,也是少年寒苦,自己发愤成名,王湘绮如此相比,是很看重他的,随后欣然收他为徒。在王湘绮门下,有铜匠出身的曾招吉,有铁匠出身的张仲和木匠出身的齐白石,人称“王门三匠”。这“王门三匠”的名声,远近皆知。有一次,他们同游滕王阁,王湘绮提议联句,首先出了两句:“地灵胜江汇,星聚及秋期。”他们三人想了半天,谁都没有联上,彼此面面相觑。齐白石是一个有志气的人,凡事落在人后,就不得心安,想到作诗不是容易的事,应该多读点书,打好根基,因此,他把书室“借山吟馆”中间的“吟”字删掉了,只名为“借山馆”,表示他不敢称作诗人。其实,因为他读书多,也能写出有自己风格的诗。晚年他自评己作,还说是:诗第一,篆刻第二,字第三,画第四。
行万里路得江山之助
齐白石四十岁以前从未出过远门。1903年,即四十岁那年,朋友来信邀他去西安。信里说:“无论作诗作文,或作画刻印,均需于游历中进境。作画尤应多游历,实地观察,方能得其中之真谛。古人云,得江山之助,即此意也。”在朋友的督促下,齐白石动身北上。一路上,奇妙景物尽收眼底。经此游历,他才明白前人画谱,造意布局和山的皴法,都不是向壁而造没有根据的。他在途中画了很多画,最得意的有两幅,一幅是《洞庭看日图》,另一幅是《灞桥风雪图》。
在西安住了三个月,又随朋友到了北京城。在京城,他一面教朋友学画,一面卖画刻印章,闲暇时,又去逛琉璃厂,看古玩字画。在西安、京城期间,不少人仰慕他的才华,推荐他去做官,人有了官名,吃穿都不用愁,何乐而不为?可是齐白石不为俸禄所诱,拿定主意不做官,他说自己平生不会做官,要到官场里去混,实在是受罪,坚决不去。
此后几年,齐白石五出五归,走遍了半个中国,游览了陕西、北京、江西、广西、广东、江苏等著名山水。八年的游历,齐白石结交了许多好朋友,书画篆刻,艺术造诣突飞猛进,他心境舒展了,作品的境界比以前开阔了,绘画与印章的风格,也有了很大改进。比如,他早年作画,是用《芥子园画谱》作蓝本,照了书本上的样子,随笔勾摹,只求形似,无笔法可言,拜了胡沁园为师后,一心跟着胡沁园学工笔画。自从远游归来,沿途饱览风景,深得江山之助,又见到不少古今名人的手迹,渐渐地他就改用大写意笔法,并把游历得来的山水画稿,重画了一遍,编成了《借山图卷》;又如他以前写字,专学何绍基的,在北京,认识了李筠庵,李筠庵叫他临《龙颜碑》,他就一直临到老;刻印章,原是取法丁龙泓、黄小松两家的,出游归来邂逅黎微荪,在黎家见到赵之谦的《二金蝶堂印谱》,就改摹赵体了。
胡沁园常引用司马迁的话与他相勉:“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些年路走了不少,书却读得不多。五出五归之后,他感觉知识底子还差得很,知道做诗做文章的难处,就天天读古文,从根基上下苦功。
去俗气之法,就是多读书
1918年兵荒马乱,乡下无法呆下去了,齐白石悄悄离开了家乡,第三次来到北京,定居下来以卖画为生。刚到北京,他所作的画,是近于八大山人冷逸的一路,北京人不喜欢,生涯落寞得很。好朋友陈师曾劝他自出新意,变通画法,他听后,琢磨了很久,自创红花墨叶一派。他为友人作画记云:“余作画数十年,未称己意,从此决定大变,不欲人知,既饿死京城,公等勿怜,乃余或可自问快心时也。”这就是有名的“衰年变法”。
齐白石论画,既不赞成“只弄笔墨,不求形似”,又极反对“只起形似,不求神韵”。他主张“形神兼备”。他所画的,无论是鸟兽虫鱼,花卉果蔬,甚至于山水、人物,都是经实地观察得来,决不向壁虚构。他题“画蟹”说:“余寄萍堂后,石侧有井,井上余地,平铺秋苔,苍绿错杂,尝有蟹横行其上,余细视之,蟹行其足一举一践,其足虽多,不乱规矩,世之画此者不能知”。又云:“余之画虾,已经数变,初只略似,一变逼真,再变色分深淡,此三变也。”齐白石有一句至理名言:“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古。”
读书,使齐白石画艺大进。若干年后,当齐白石已是国画大师时,他就读书和绘画关系开导女弟子熊仲光说,“初学画者,不怕有稚气,就怕有俗气,稚气随年龄增长,不断用功就可除去;俗气则难除,去俗气之法就是多读书,书卷之气上升,则市井之气下降,故古人云画家须读万卷书,走万里路方可脱俗。汝今初学,即有高雅之气,实属难得,望勤学不怠,期于有成”。
齐白石活到老,学到老,一生都在孜孜以求,向着艺术的高峰不断攀援,生命不息,创新不止,终成一代艺术宗师。
胡怡之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