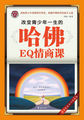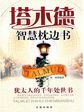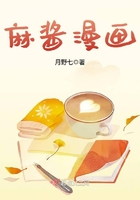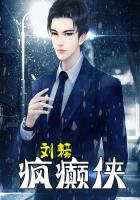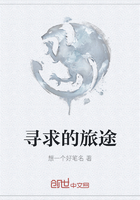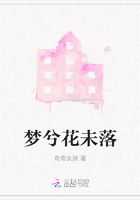黄宾虹(1865~1955年)国画家、美术教育家。安徽歙县人。早年在神州国光社等处工作。主编《艺观》。建国后,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教授。有《黄宾虹集》。
近代山水画家黄宾虹,被誉为中国山水画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国画界常把他与齐白石相提并论,誉之为“北齐南黄”。黄宾虹成为一代画宗,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读书多,阅历深,从而具有深厚的学养。
“不就是‘红于二月花’的枫叶吗!”
黄宾虹读书作画,八十余年几无一日间断。八十九岁时,双目患白内障,严重得几乎失明,还在纸上摸索挥写。1953年,他为京剧表演艺术家张英杰(盖叫天)祝寿,题了“学到老”三字,同时也以之自勉。他本人确实具有“笔无暂暇,非病不休,非老不息”的“学到老”精神。
黄宾虹五岁起读书,从小就养成了勤学的习惯。平日好学好问,七岁就识字千余。他父亲有个挚友能诗善画,黄宾虹便去请教。该友嫌黄宾虹年纪太轻,总不爱回答。黄宾虹求知心切,一再请教,终于得到这位前辈的指点。他学写字,这前辈要求他力透纸背。有一次,他写了个“大”字,这前辈将纸翻转来看,摇头说不行,指出从纸背后看,在起笔处有三个点,是使力未平的缘故。从此,黄宾虹就更加注意如何握笔,如何使笔,终于练得一手好字。“三更灯火五更鸡”,黄宾虹每每早起在家里写字学画,然后去家塾读经史、诗词歌赋类文章,他比较喜欢诗词和六朝的辞赋,傍晚休息时,便背诵诗词。他求知欲强烈,八岁那年的秋天,黄宾虹奉父命陪同一位同族的翰林老爷观看当地的名胜古迹,到了家乡金华的八咏楼,楼外满山遍野,枫叶经霜,一片火红。翰林老爷指着红叶问黄宾虹是什么,黄宾虹不费思索地答道:“不就是‘红于二月花’的枫叶吗!”他的回答令翰林老爷十分欣喜,又指打草丛里面跳出来的一只蚱蜢,问道:“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是蚱蜢”。翰林老爷又问:“那你可知道有一种小船叫舴艋舟的,又是什么缘故?”黄宾虹记得李清照的词中有一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就说:“小舟叫舴艋,是‘六书’象形的意思。”这位翰林老爷更为赞赏年幼的黄宾虹,并将自己的著作《劝学赘言》《凤山笔记》以及重刊《潭滨杂记》等送给黄宾虹阅读,由此他获得更多的知识。十三岁时,黄宾虹遵父命应试科举,但榜上无名。黄宾虹本无心于科举,便埋头于书画堆中。十九岁时,黄宾虹游览了黄山、九华山,特别兴奋。有一天,他与诸亲友游鸣弦泉归来,入夜,同行者都睡了,可是他还在旅舍的灯光下起劲地默写着黄山的景色。夜半,月光射进窗户,更激发了他的画兴,于是就带着画具悄悄地步出户外,蹲在旅舍旁边的大岩石上画夜景,直到拂晓才离去。
黄宾虹在学画期间,经常奔波于金华、杭州、歙县、南京、扬州间,不论在旅舍或舟车中,他总是手不释卷。他生活非常有规律,天不亮起床,在院子里舞剑、锻炼身体。东方发白后读书,晚上写字或抄书。中年,他更加勤学勤画。白天工作,晚上埋头学术研究。画兴到来、灯下挥毫。有时静对壁上的名作,聚精会神地看,直到心有所悟。晚年,他还自以为“八十学无成、秉烛方未已”,手订“学画日课节目”,内容包括学习的范围与进程,并要求自己按“日课”进行学习与工作。1955年3月初,他病势严重到不能起床饮食,床头却放着纸笔。距逝世前二十九天,强撑着起来画山水小品,留下了绝笔墨宝。
借来文字学典籍认真阅读
黄宾虹博学多才,而文学上的修养,对他的绘画帮助很大。其作品中期多题诗,晚期多题画,“诗文书画、汇诸其美而为一。”
黄宾虹深知,书不可不尽读。不经寒窗苦读,不会有所创新。少年时在家乡,他曾一个人躲在楼上,读书作画。画倦了就读书,读倦了便作画,甚至废寝忘食。一盏孤灯,一卷在手,往往读到深更半夜。为研究文字的变迁发展,他借来《说文解字》、《尔雅》、《仓颉篇》,认真阅读,并与其他著作相互印证、比较。对书法,他为了解前代名家的实践和经验,分析他们的艺术作品的优缺点,取长舍短。他一边临摹古画,一边又读画家的著作,加深理解画论,用以指导实践。他研究传统,吸收传统,采取浏览、细读和临写三种方法。对于浏览和细读,他重于比较,把不同时代的作品相比较,把名家作品相比较,对于同一画家作品,又以前后变化作比较。好画过目,都认真吸取其长。“取古人之长皆为己有,而自存面貌之真不与人同。”
带着古人名画走在万水千山间
黄宾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一生九上黄山,五上九华,四上岱岳;西湖、富春、太湖、天目等名胜古迹,更是饱游饫看。去江西,游匡庐;入福建,游武夷;到广东,登罗浮、游越秀;远至广西,畅游桂林、阳朔;自湘西入湖南,登衡山、游岳麓,放舟于洞庭。遍游峨嵋,探长江三峡之险、攀登巫山十二峰;在香港、九龙等处,也都留有他漫游的踪迹。南南北北,走遍了中华神州的大小河山。环视二十世纪中华画家,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注重游历作画的。
黄宾虹沿途写生作诗,有铅笔速写、墨笔默记,画稿积累多至万余帧。黄宾虹游山川,与众不同,他带着古人名画,在山水间寻求画法的来源与奥妙。游黄山、青城时,他“常于霄深入静中,启户独立领其趣”,面对自然山川,深刻领悟。
人谓“百闻不如一见”,黄宾虹既重视“耳闻”的间接知识,更注重直接的感受“一见”,身带书卷,遍游名山大山大川。他认为的“见”,也就是“读”。中华山山水水都可当作立体的形象的活文字来读。没有早年的“读万卷书”和中年的“行万里路”,他不可能成为画界的精英;也不可能创造出他山水画的鲜明风格。
黄宾虹认为,山水画家一要“游览山水”;二要“坐望苦不足”;三要“山川我所有”;四要“三思而后行”。即要尽情、全面看山川,深入细致观山川,与山川为友,拜山川为师,心占天地,方能懂“万类性情”,笔笔有所思,对山川“身到、心至”。他游览山水,“师法造化,正是十里拜一师,行万里路,拜了千个老师”。他的画,立意奇、丘壑多。“形理意妙合自然”,奇的不使人感到怪,平的却又使人感到奇,在绘画艺术上,别有造诣。
黄宾虹书读得多,画看得也多,很早对于书画具有高明的鉴定能力。早在1886年,即他二十一岁的那年,他就鉴定了一幅冒名董其昌的赝画,由此声名大振。1936年,故宫博物院聘他鉴定旧藏书画。鉴定名画,也就是审读名画乃是得天独厚的艺术欣赏,是他行走、观察千山万水的继续,它也是一种读书模式。几年间,他过目历代名作数以万计。因此正如傅雷所说,那是黄宾虹“读万卷书的最有益的补充。”
钱朝阳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