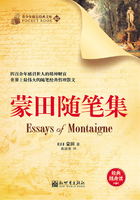走。它应该是个动词吧,有时候也不一定是,即使它不是动词,它也可以带动很多的词语,能够牵来很多的物事。走路。行走。走来。走去。走过。走到。走向。走入……
齐步——走!一、二、一,一、二、一。哦,多么矫健的军人步伐,这可是我最喜欢的步伐之一啊。很羡慕我的两个弟弟,他们都曾经是军人,一个是炮兵,一个是武警,不过我最想当的是与大海打交道的水兵,或者是飞翔在蓝天上的空军。我最终也未能成为一个军人,这是我此生难以弥补的遗憾之一。但是,现在想起来也就无所谓了。军人那种高度的纪律性,那种整齐划一的生活,也许是我所受不了的。再说啦,如今再也没有了烽火连天,没有了硝烟弥漫,没有了金戈铁马,没有了出生入死,当兵还有多大意思呢?
走神儿。走神儿有时候就是发呆、发怔、发傻,有时候就是联想,就是梦想,就是奇思妙想,我喜欢走神儿,很多时候都在走神儿,我就是喜欢走神儿,说不出走神儿是好,还是不好。小时候,在课堂上走神儿,考试时走神儿,长大了开各种各样的会议时走神儿,散步时走神儿,上班时走神儿,骑车时走神儿,坐车时走神儿,坐船乘飞机时走神儿,逛大街、逛商场、逛书店时走神儿,听音乐时走神儿,看戏、看电影、看电视时走神儿,宴席上走神儿,葬礼上走神儿,婚礼上走神儿,恋爱时走神儿,做爱时也可能走神儿,读书时走神儿,即使是在写小说时也往往会走神儿。不,不仅仅如此,就是在小说里面我也走神儿,比如写着写着就可能会分岔,岔到按规矩说不该去的地方了,其实也就是跑题了,一走神儿就跑题,跑题了就是走神儿了,当我发现了这种走神儿的问题之后,不是悬崖勒马,不是痛改前非,不是矫枉过正,而是信马由缰,破罐破摔,听之任之,走神儿就走神儿吧,走到哪儿算哪儿,只要不是走投无路就行。反正我就是喜欢走神儿,我也知道自己这个毛病,我觉得有必要在自己专用的语言仓库里,建立这么一个歇后语:汪淏走神儿——常有的事。甚至打算将来要为自己写一篇小说,名字就叫做《走神儿的汪淏》,而此时此刻,我分明就在走神儿。
走婚。一种神秘而有趣的婚姻形式,男女双方只有感情的联络,只是性爱的伴侣,而不用家庭这种固定形态把他们拴在一处。听起来有些像天方夜谭,但它就发生在并不是特别遥远的云南泸沽湖那边,摩梭族人民的情感、性爱、婚姻生活,就是那么过的。多年以前,我曾经去过那个遥远的地方,当时真想留在美丽而神秘的泸沽湖,也尝试着走一回婚,可惜是和新婚的妻子一起去的,我这个隐秘的愿望就不太好实现了。
走往。交际的另外一种说法吧。你一点不喜欢走往,就像你从小就不喜欢走亲戚一样,你不喜欢跟那些喜欢走往的人走往,更不愿跟那些有钱的人、有权的人、有名的人走往,这些年来,你几乎从不跟这类人走往,不是对这些人有偏见,而只是不见,只是不想见,或者觉得没有必要见,如此而已。在走往——交际上头,我的确是个懒人,也宁愿做这么一个懒人。
走门路。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门,有许多的路,你会钻进哪扇门,会走上哪条路呢?我知道的,我几乎是没有别的门路的,除了写作和读书,我不愿意进别的门,不愿意走别的路。
走资派。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革命派要战斗。呵呵,这些词语和句子,都是些早就掉光了牙齿的老太婆,它们太老啦,或者说早就死掉了。就像有些词语在诞生,有些词语在消亡,比如,走后门。多年以前,走后门这个词儿,就像家常便饭一样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里,很多事情都用得上它——走后门。如今,谁还能想到它呢?是啊,现在不必走什么后门啦,现在的门太多啦,正门,歪门,邪门,到处都是门,已经不必走什么后门,于是,走后门就死了。
走红。所谓一炮打响,所谓走红的人与事太多了,可你一点也不喜欢,一点也不稀罕,当然你也不可能走红什么的,你只愿意是本色的自己。你喜欢蓝颜色,或者是黑颜色,要不就是白颜色,却不怎么喜欢红颜色,所以对走红这个词语就不感兴趣。
走光。某些有裸露欲的女歌星、女影星,故意露出那么一点点皮肉,当然是那些脸以下、大腿以上的部位,说白了,或者肚脐,或是胸脯,或者屁股,这就是所谓的走光了,她越是会走光,越是善于走光、敢于走光,就越是能招来眼球和嘴巴,于是就越能走红。人们喜欢看到她们的走光,要是走光走得再多一些,就更妙了,如果不能是全光了的话。而今适逢一个走光的好时代。正如有买的就有卖的,有愿意“露点”的,就有喜欢窥视的,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走火。走火入魔。走火,就是枪走火了,走火入魔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不认为后一个是贬义词。其实走火入魔应该是说一种难得的境界呢,那得看是在什么事情上。我走火入魔过吗?什么事情值得我走火入魔呢?
走过场。走形式。这两个词语,更多的时候属于组织,属于单位,属于政党,比如开会,比如领导讲话,比如发放文件、学习文件,比如考察,比如参观访问,比如各类大检查,比如所谓的专项行动,等等,对此,我不太感兴趣,就懒得再想这玩意儿啦。
走市场。市场是早就有的,但走市场却是个新词儿,至少对于我来说如此。本来,市场就在那儿,可现在人们却叫着喊着要走市场,像是农民起个大早去赶集,要走市场了。集,就是市场嘛。想起了一个故事,哦,是想起了一个女性。她先前是一位苗条而纯真的女孩儿,现在是个成熟的女人了。那时候,她是个文学爱好者,喜欢写点纯美而忧伤的抒情散文,还在晚报上发表过,而且读过些好书,一搭话,你就能感觉到她是个素质不错的女孩儿,当然这跟她有着那种得天独厚的条件相关,她舅舅开了一家书店,她作为店员帮舅舅卖书,自然就读过不少好书,顺便也就知道了许多关于书的学问。我是那家书店的常客,一来二去的,就跟她相熟了。当她知道我也写小说,对我就更多了些热情和尊重,少了些客套,当然也少了些价钱,在我买书的时候,她一见到我,就很有些深度地跟我谈论作家,谈论图书,主要是谈论那些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对于店里那些又是海报、又是炒作的畅销书,她总是嗤之以鼻的,特别看不上,说那是走市场的,没意思,没价值。我就会意地笑了笑,然后便问她这些走市场的书,走得怎么样呢,她苦笑着说卖得还是不错的,接下来就是摇头感叹,说如今大多数读者的素质太低,分不出真正的优劣,说现在不少作家堕落成了文字商人,只想畅销,只顾走市场,而缺乏精神和灵魂,忘记了艺术品位,等等,一套一套的。她这么说的时候,我只是微笑,而不想发表什么意见,她已经说了那么多,我还能再说些什么呢?一晃,许多年过去了。她早就在舅舅的那个书店里学艺出师,自己也开了一家很像样的书店,又做批发,又搞零售的,小店员成了女老板,越做越会做,越做越大,越做越好,她发财啦,人也发福啦,苗条的姑娘就成了个丰满的少妇,赚钱买下了房子,还有汽车,小日子过得很滋润了,我去逛她的书店时,她总是告诉我近来哪些书畅销,哪些书卖不动,对我又表扬,又批评,又指导的,汪老师,你的作品写得很有品位的,可惜你太不考虑当今读者的胃口啦,你的写作也要走一走市场啊。我就笑了笑说,我当然是要走市场的,每天我都到菜市场上走一走的,另外,我还喜欢到鸟市场和花市场上走一走呢。开过如此的小玩笑之后,我一脸诚恳而又茫然地说,我不知道如何走市场,真的不知道。再者,我也不太愿想市场不市场这档子事。于是,她就一一列举目前走市场走得很俏的那些作家,有些还是她先前很尊敬的名家呢,随后就历数那些能够走市场的题材和写法,就像当初她拿那些抒情散文恳请我指导一样,如今她很有耐心地指导起我应该写些什么以及如何写作来了。我恭听完毕,苦笑着摇头,谁爱走市场谁就走去吧,我走不了市场的,也不想走什么市场。她还想继续开导下去,我只好婉言谢绝道,我们还是说点别的吧,或者这样说,你先忙吧,我看一看书。本来,我想说几句不太客气的话,比如想说,我只是在为自己写作,而且永远只为自己而写作,只为自己的内心世界而写作,我的作品来自我的灵魂,也许它能走进读者,哪怕只是几个读者的心灵呢,至于能不能走入市场,一点也不重要,甚至最好是别走入市场。可想了想,还是没有说,这些心里话不必说出口的。
走运。人走时运马走膘。你走运吗?是啊,你走过运吗?不好说,想不起来了。走运,不走运,运气这种东西,无所谓有,无所谓无,有时候有,有时候无,不是你想走运就能走运的,那就不想走运不走运这种事情了吧。
走账。走账就是记账。这个你当然知道,岂止是知道,简直是太熟悉了。想起来,那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啦,你从商业学校会计班毕业之后,就被分配到一座小城的肉联厂“走账”去了,走账这种枯燥的活计,一下子就耗走了你整整八年的青春好时光。后来,你就走了。因为你一点也不喜欢那些阿拉伯数字,那些大写了的数字你也一样不喜欢,说到底,是你不喜欢“走账”,你喜欢的是语言,是汉字,是词语,是由汉字组成的文章和小说,于是,你就走了,一走就是好几百里,从小城走到了省会,从杀猪宰羊的肉联厂走向了大学中文系,一个天天得走账的小会计,成了一名文艺学硕士研究生,研究起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来了,其间走过了多么遥远而艰辛的路,只有你自己最清楚。比如,因为考研而停薪留职,因为停薪而无以生计,你只好跟一位开了家结婚用品商店的朋友,一次次乘夜车到江南去贩货,中途上车,当然无座,只得钻进座位下面去睡觉,因为想省下点钱,不敢住旅店,睡过一个个南方车站的广场,更多的时候是马不停蹄,去了就回,回来了再去,这种苦不堪言的日子熬过了半年多,你才开始面对那么多更困难的考研问题。往事如烟啊,你就不必多想这些如烟的往事了。在这种事情上,你宁愿好了伤疤忘了疼,不搞那种忆苦思甜的勾当。反正你早就不再是那个每日都要走账,跟数字纠缠在一起的小会计了,你已是个与语言打了多年交道的写作者了。当年走账的时候,你还算个挺本分的会计,那是来不得半点马虎和模糊的,现在你行走在语言的道路上,就不必那么安分守己了,倒是可以出格些,有时候甚至不妨走走神儿什么的。
边走边唱,我刚才不是在边走边唱吗?《边走边唱》,一部电影的名字,一个盲艺人的故事,由一部叫做《命若琴弦》的小说改编,两者我都看过,感觉是这样的:小说很好,电影就那么回事。很多电影都是由小说改编的,很多由小说改编的电影都不如小说。是不是这样呢?或许只因为你喜欢的是小说,而不怎么喜欢那些由小说改编成的电影。很有意思的一种文艺现象吧,那个说过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但其实很喜欢思考的小说家米兰·昆德拉曾经咬牙切齿地发过誓,本人的小说谁他妈的也休想改编成电影。操!想强奸我吗,想强奸我的小说艺术吗,没门儿!于是,这老兄就在其小说里尽量很哲学地叙述那些深刻而微妙的人生故事。很讽刺呢,他那部小说名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还是生生被人改编成电影《布拉格之恋》了,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后者(电影)要比前者(小说)的接受者多得多。不知米兰·昆德拉先生是感到悲哀,还是觉得庆幸?这是一个外国人的故事,你不必关心它的。想想当今我们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事情吧。由于偶然被改编成电影的小说而轰动一时的那些作家,其名字后头无疑是加了砝码的,他是否有某种被强奸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否很快活,只有当事人自己最清楚了。很好玩、很可玩味的是,而今有那么一些(小说)作家,渴望着、期待着被影视(导演)强奸,甚至时刻准备着、盼望着后者强奸,要是能被(影视)轮奸那才叫真棒,才更过瘾呢。当然最好是那些干劲很大的猛男名导来做,而有些所谓的小说,就是专门为影视而量身定做的,身高、体重、三围,都尽可能符合影视(导演)的眼光和胃口,或者,影视之后,或者同期,再鼓捣出所谓的小说,所谓的影视小说。某些影视(导演)与小说(作家)之关系,令你想到如下的词语,暧昧,恶心,野合,暗送秋波,眉来眼去,投怀送抱,明铺暗盖,打情骂俏,勾搭成奸,有钱大家赚,你有情我有意,互惠互利,利益均沾,相得益彰,皆大欢喜,等等,靠!这样的小说,这样的电影,我连看也不会看的。你这是怎么啦?跟电影有仇,有过节儿吗?不,我也很喜欢看电影啊。但我喜欢看的是另外的电影,是某些外国好电影,是那种与小说无关的艺术片。如上的事情,与你有关吗?没有,似乎没有,真的没有,你犯不着为此发牢骚吧?唉,我只不过是忽然想到了这些而已。算了吧,还是想点别的事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