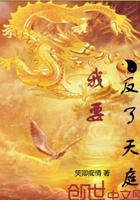站在医院的门口,麻木的看着那些人来人往的病者。
一辆活动病床被几个急救员风风火火的推过来,病床上正蜷缩着捂着胸口的人。殷未济赶紧闪在一旁。他的内心百感交集,这世界上还是有那么多受苦受难的人。
未济手臂已经包上了厚厚的绷带,如行尸走肉的迈下了急诊室的门口的台阶。
跟手臂的烧伤相比,其他部位都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
给他包扎的大夫说这已经够幸运的了,如此近距离的爆炸居然只是受到了皮肉伤害。只是急诊医生有点百思不得其解,说他的伤口很奇怪,按说电子产品爆炸是不会造成烧伤,未济的手臂伤口分明是被近距离的高温烧了就会是这样的。甚至开始怀疑,这个沉默寡言的病人是不是有精神上的问题了。
从主治医生的意思看来,近距离的爆炸伤害只对他造成皮肉烧伤,破坏力实在太过于轻微了。不过它确实很庆幸,及时的用手保护住了眼睛,但是他并不明白,自己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医院离他租住的房子并不太远,心情木然的他毅然选择徒步走回家,他不想去跟一堆人去挤公交,也不想在街道上尴尬的扫描公租自行车了。
打车……还是算了吧,掏空了口袋才勉强交够了医药费,他的囊中就已经蹦子儿皆无了。
这么胡思乱想的神游,脚下依然麻木的朝向家的方向前行,速度也并不快,他现在蒙蒙的,一团雾水。
殷未济怎么也想不明白。
当时完全在走神的状态中,又倒霉的从神游进入了白日噩梦。
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会做一些身临其境的噩梦,有如在地狱中,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噩梦做的也越来越多。大部分的噩梦都是黑暗与痛苦格调的,就像是在地狱中煎熬着,忍受着。
这种状况越来越严重,最近几年,甚至在大白天恶梦偶尔也会突然混进现实中来。
今天是最严重的一次了,他没想到噩梦会与他神游完美的融为一体。而且让他悲催的分不清什么是现实,什么是噩梦了。
还有一个疑问挥之不去。
那就是连传真机炸掉都不知道的自己,又怎么会有足够的反应,迅速去做像保护自己如此重要的事情呢?
越想越不明白。
头还是昏昏沉沉的,也不知道怎么了,自从神游被突然惊醒之后,自己就迷迷糊糊缓不过劲儿,老感觉半睡半醒,连走路都深一脚浅一脚。
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患了精神分裂症,但是他已经不在乎了。因为从没有人在乎他,自己干嘛要在乎自己。
他暗恨,都没有人来看看自己,哪怕现在有人能扶一扶他,他也好受些。
活了25年,别说女票,连真正的有价值的朋友也没交到。
从学校毕业到工作挣钱。那些同学同事对自己都爱答不理的,也许是自己平时的行为太过神经兮兮的,经常是动不动就发呆发愣。
如果说帅哥(他自认为还是有几分姿色的)卖萌能讨好女生的话,自己偏偏又长了一张棱角分明的脸。弄得怎么看都像是高冷而不是卖萌。
也确实有几个女孩主动套近乎,但是一个个风骚的不行,他最讨厌那种女人。
而交的朋友都是酒肉朋友,平时借钱的多,真正能靠得住的少。而有几个看似人品还不错的,自己又老是和他们说不到一块去,完全没有共同语言,每次交流都是尬聊。
到最后,也懒得搭理他们了,过自己的世界就好。
街道两旁依然是不温不火的场景,破破烂烂的商户门脸。有些明明是刚刚才装饰好开始营业,但是目前看起来模模糊糊的笼上了一层灰色。
可以是因为生意不好,经常成看见戳在门口偶尔吆喝一下的小贩。
走进步,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出现捡瓶子的老大爷老大妈,
行走着的人全都互不交流,这是机械的来去匆匆的朝自己的目的地前行。
在他看来一条街道与另一条街道没有区别,麻木的两条腿只是一步一步自动的在朝前移动。
再过一个街口就是自己住的单元楼了。
天色渐渐随着他的心情也暗淡下来,他看了看表,下午一点四十三分。
手表的滴答声清晰可辨,每一分每一秒都与他自己的心跳声交错着响起。
街道尤其安静。
好安静。
安静?
……
不对!!
整条街道什么时候?这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了!!
他稍微回过神来,四下张望,突然意识到现在的景象十分怪异。
什么时候,周围稀稀落落来往人群——不见了。
困倦到打蔫的小贩没有了,匆忙赶路的行人没有了,疯狂跑闹的小孩没有了,收家具的——也没有了……
未济现在处在一个无声的空间,一个无人的世界。
诡异至极,不管怎么说,这大白天的一个平时店铺林立的热闹街道,咋就瞬时间半点人影都没有了呢?
甭说的人影,就是连个活物的影子没有一只。
他开始意识到有些不对头,但又搞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
慌乱之下,他带着个伤残的胳膊四处观看,巷口、店铺、路旁空空荡荡。甚至连个溜狗的也见不着。
就是所谓的那种死寂的感觉,那种只有在墓地里和空无一人的剧院里才有的感受,可……这明明是在大街上啊。
他好奇的四处观望,希望能够找到一点活物的气息,原本狗屎满地、枯叶子满天飞的街道这一刻却出奇的干净,连平日往脸上扑的小虫子也没有。
然后……这种寻觅……也渐渐变得困难起来,视线越来越模糊了,他揉了揉眼,发觉越来越看不清事物,奇怪之下,不自觉的看向了天空。
哇……天!
不看还好,这一看之下,顿时惊的浑身僵硬,遍体发出阵阵的寒意。
血色翻滚的没有尽头的天际,阴影寒气正在迅速的吞噬着所能接触到的每一块土地。衬托在它下面的所有代表生命的色彩被统统夺取,放眼望去尽是铅灰色的死气沉沉。
一直无限的四面延长直到那一条血色的地平线。
一切……怎么有些变的和梦中的场景越来越相似了呢?
自己这是又睡着了么?未济惊愕的用那只健康的手捏了一下脸,发现痛感还在,不是做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