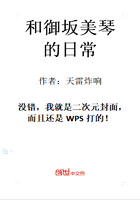女孩终于拿到了她的工钱,四十两,一个月,林小宋倒是出手阔绰。
“为什么像良姨这样的大好人却总是为钱苦恼呢?”自言自语。
小女孩再次撑起那把油纸伞,尽管今天并没有雨。
她叫羌凡,羌笛的羌,平凡的凡。父母远在异乡,这两年是良姨带着她。她常想起往前种种美好生活的画面,他们的脸庞总是浮现在眼前。她跟着良姨搬了很多次家,她觉得父母回来会很难找到她们,所以她已经为此筹备很久——她要去找他的父母。千里之外,那个繁华无比的帝都,是怎样的景象呢?他们有变老了吗?
她坚信很快就会有答案。
小跑回到家,木门洞开着。羌凡暗暗责怪。
良姨没有在家。平常可是很少出去的呀。厨房的大箱子里,食材还有的是呢。
桌上留了碗面,里面意外地放了不少肉,还腾腾冒着热气。羌凡感觉有什么事发生了,但是她不想再被打扰,尽管或许只是出于无奈。
碗下面压着一张信纸,折了很多次,小小的,完全在碗底下。羌凡自认自己对找东西有特别准的感觉。舒开信纸,一些灰尘却散了出来,羌凡努力挡住碗,不让灰尘玷污了高贵的肉。
“小凡,你马叔叔给我寄来了钱,我有一些急事,先去子午了。桌下的地板里有四百两银子,衣服你可以自己收拾。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
羌凡从未听说在遥远的城还有什么马叔叔,也没见过良姨的言语这么仓促直接。但是语气还算平静,应该没有大事。
四百两银子,在这,哎,对,找到了。
地板下面格外干净,良姨应该是打理过了。那都不重要。
这就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嘛!
吃碗面,睡过了一中午,醒来时候突然想到什么事情。飞一样跑到了林小宋家。
“林小宋!”
“哪里来的野人直呼大小姐名讳?”不远处有个丫鬟怒斥道,装腔作势的样子还很逼真。
“诶?羌凡,你怎么来了?来要书的吗?”
羌凡强忍心中的不爽。
“林小宋,你爸是不是想要我们家那片院子?”
“这......”
“现在,这个院子卖给你们,更好的是,整套房子也卖给你们。不是风水好吗,这样你们家就福禄双收是不是?我不多要,只要六百四十两。”羌凡回忆了一下当年买时价格,给拉上去整整一倍。
这一套捆绑销售很让人无语,但林小宋还是以最快的速度跑到了她父亲那里。
“爹,良瑜辰卖了!”
“卖了?”
林老爷子腾地一下从太师椅上站起来,惊喜交加。
“无需多说,叫人去商量价钱。”
“那小丫头说了,要六百四十两。”
“嗯?说好了?这不是问题。快,苏管事,拿钱,换房契!”
回家时,夕阳欲颓,羌凡攥着一大把银票,租了还算可观的马车,顺便去雅安阁吃了顿饭,启程。
“姑娘,子午可远得很呢......”
“少不了你的!”羌凡努力装出平时林府丫鬟的架势,自己以后也算半个富人了。
不知怎地,建嗣惨剧,自从张北翎来到子午,竟然从未听人议论起。问过吴罗二人,那三个整天不知去向的奇葩,甚至马老师,都是不知道。在子午人的印象里,建嗣还是那个离得不远的平凡的城。前两天还遇到一个家乡是建嗣的农民,他却说已经离开了那四十年了,连城门什么样都记不清了。
两城相隔如此之近,这件事情可能是被刻意压下去了。
算了,本来也没指望官府衙门能够解决这种没来头却死人多的案子。只不过,倒是有些日子没听到宁箴的消息了,雅安阁也好几天没去了。
马老师毫不迟疑批准了以后张北翎每天下山去上工。吴冬至和罗桀这几天经济已经紧张,时不时买些消耗品却不知不觉已经只能吃张北翎的老底。二人各回各家取钱去了。张北翎也算是明白了一点,修炼,真烧钱。时不时马老师指点着去采购什么珍稀药材,山上结界里还没有,下山时总共七个人能凑就凑,那三个怪胎明白就是穷光蛋,马老师也是一副云淡风轻的姿态,可是把张北翎坑苦了。
再来上工时,却发现老陆把这些天没上工的日子还照样算的工钱都存着呢,一下又吹鼓了钱囊,而他本人却一如既往的不见影。
人们还是没变,还是有不少人认得他,一个小青年还鼓起了掌。
重拾了先前的生活,张北翎感觉不错,至少感觉心里踏实了。这几天好像也有那些药材的原因,他明显能感受到自己的身体在改变,魂域变得精练了几分。山上书楼里三等境界要求的水平,也在不断练习,时不时搭个结界计划什么恶作剧,只是搭的时间有点长。然而,吴冬至却比自己快得多,罗桀早就不屑与他们比了。自己还是那样。不过唯一有优越感的是,吴冬至就是打不过他,好像是某种天生的克制。吴冬至好几次不服气跑到马老师那,张北翎就在隔壁画鱼长老的房间里偷听,马老师只是鼓励鼓励他,告诉他克制是不存在的,一定是某些方面针对性太强,压制自然产生。
确实如车夫所说,车程用了整整五天,看着马跑的也不慢的。终于到了目的地时,车夫越发忐忑的心也放下了——羌凡的行李,几乎都是钱。车夫好像从未见过那么多似的,咽了咽口水,赶着车走了,还不住偷笑,让羌凡记起来总觉得被坑了一样。
子午的城门一看就知道不一般,那种感觉说不出来,只有时间可以积淀,可以看透。
雅安阁也是那么显眼,虽然其他大大小小的食宿地方的牌子也没有什么两样,但雅安阁就好像子午的城门一样,独树一帜。这似乎是每个初访者必有的印象。肩上背着这几天看不出缩小的钱袋,看起来里面只是装的衣服。走进去才发现,小管事简直就是不地道,总店种种还没有那边好的,不过确实是大,还有二层,人也极多。下午有段时候人海才平复一些,渐渐空出些座位,羌凡才得以排上号。
可能是出于前几年持之以恒的渴望和习惯,一看到木牌上的肉片面就脱口而出,旁边伙计差点没反应过来。仔细一看,价格却是比那边便宜些。
端面来的的是个青衣少年,看上去和其他伙计不一样,羌凡仔细端详了一下,什么都没看出来,长得还不错?
陌生小姑娘不知含义的目光总是让人心里发毛,张北翎不知为何有种不好的设想,却面未改色,快步走了。跟同事们打个招呼,确实到了跟那两个人约好上山的日子,这两天没回去,还有点想呢。
结界已经熟悉的很,张北翎甚至能够早早就让自己进入非呼吸换气的状态。山上依旧是那般,最早的吴冬至坐等在那棵巨树之下。二人早早吃过晚饭,守在门口,却迟迟没有等到罗桀。张北翎心说这死胖子是不是忘了,明明才没过几天,难道智商和体重是成反比的吗。
前边日落了,后边渐织的漆黑弥漫起来。张北翎闲着,抬头数着星星。数着数着,却发现今夜有一些诡异,那里诡异?一时却说不上来。只是心中有种难受的感觉,好像少了什么东西。眯上眼睛仔细看看,嗯?月亮呢?北斗呢?
乱星摆布的模糊不清。
张北翎把整片天空来来回回看了好几遍,这两个日常极其显眼重要的参照物却怎么也找不到。腾地一下坐起来,伸手去拉旁边正打哈欠的吴冬至,他回过头,询问的目光顺着张北翎的视线往上移,突然僵在那里。
“今天是什么鬼日子......”吴冬至的声音有些含糊不清,但是没有恐惧。
“今天什么日子也不是,黄历上最平凡的几天就有今天,什么也不宜,什么也不忌。”
张北翎突然想到马老师上次喝多了的时候说的话,什么都没有啊,杀人的好时候。不禁联想到罗桀,但瞬间打消了这个想法。
起风了,风也是贼风,阴森森的,吹出一身冷汗。
“要不咱们别等了。”张北翎突然有了什么不好的预感,但就是说不清楚。不对,是说不出来。
嗯?为什么说不出来?
旁边吴冬至好像静止了一般,面对着他,脸上却是很复杂的表情。张北翎看到半截玉黎已经握在他手中,但没有完全化出来。
张北翎第一个想到的是自己身后有什么,瞬间青渊出鞘附魂疾斩,却什么也没有。只是风被卷成了几股乱流,久久无法恢复本来。一回头,发现自己正站在那边。我的天,这是灵魂出窍了吗?青渊还跟着一起出了?
张北翎戳了戳“自己”,又硬又凉,好像一大块高山上的冰。他想说话,随便瞎叫了几句,但是发现自己什么也没听到,不知是说成没说成。想到一些鬼怪的唬人书,张北翎一咬舌尖,却根本咬不动。好像自己也是又硬又凉。略用些力,青渊在小臂上划过,只留下了一道不很清晰的白痕。
张北翎并不很害怕,因为马老师曾说过在这棵树下曾发生过不少很奇怪的事,就好像一个人突然吃了自己的剑却什么事也没有事后还不记得的种种。他猜测自己现在也处于某些怪事之中。
张北翎向来对变化很敏感。现在吴冬至的玉黎,又多化出了几分。张北翎看到空气中有一些细小的白色颗粒极其缓慢地凝着,汇向吴冬至右手处。“自己”却毫未动。
张北翎突发奇想,又走过去戳了戳吴冬至,还有温度。轻推一下,吴冬至的身躯很不自然地弯曲,向后退去再次静止。玉黎划过的空间有无数光影交杂着闪烁。张北翎感觉有点过了,恐怕这一推要让吴冬至受什么内伤,但他不知道怎么停止这种状态。低下头,张北翎在无声地大喊。
喊完了,安静极了。张北翎却发现自己的魂气有些枯竭,不仅仅,好像是超额支出。这有什么联系吗,自己好像什么都没干。难道推一下这么费的吗。
眼前一黑,生命的感觉突然再次涌入脑海。张北翎感觉喉咙有点甜。终于听到一声响,很沉闷,想来可能是吴冬至落地了?张北翎没有感觉了,但在黑暗中他猜他差不多已经倒着了。
再见光明时,张北翎发现自己躺在一张不太舒服的床上,眼前是有些模糊的橡木天花板。哦,还有两个熟悉的脸。
“你用什么法子偷袭的我?我怎么没见你练过?”吴冬至的声音有点哑,听起来好像几天没喝水的那种声音。应该还没养好呢。
“不知道。”张北翎不知道这三个字声音能有多大,或者说没说出来,反正他是尽力了。
“不管是什么,好像很费魂气的啊。至少你这个月是别想从床上下来了。”罗桀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张北翎想着你要是不拖拖拉拉也不会有这些个屁事,虽然他自己也没明白究竟是什么屁事。
“马老师,您见过吗。”吴冬至看起来好像回头了,。
“你说我听。”马老师这句话说得不知怎么语气特别顺耳,一点先前的架子也没有了。
“啊,就是我看到张北翎突然变成好几个,然后我就飞了,他也吐血晕那了。”
张北翎现在知道自己完全是只能听不能说的状态了,也没法描述那奇怪的经历,躺着干着急。
“没见过。”马老师的声音又来了架子。张北翎猜想之后又应该有什么很重要的指点,就如可以去哪或在哪类书上查一下之类,却无奈黑暗再次袭来,只好睡去。
张北翎在深渊中,坠着,身旁什么都没有,但就是深渊。红褐色越来越狰狞,好像融了血的岩浆,一点点狭窄。张北翎要停住。
右手一提却提了个空,我怎么会不带着青渊呢?
张北翎努力回忆着刚刚发生了什么。
好像一个穿绿衣服的把我推下来了,他还说了什么?
张北翎用剩余不多的魂气凝了魂锁,却丝毫没有减缓下落,张北翎突然发现下坠速度加快得不正常,好像是最深处在不停地吸着他。张北翎艰难地回过头去,发现最低处什么也没有,只是一个亮白的小点。
四边越来越窄,张北翎什么也记不起来。左右看看发现手掌已经消失了,没入了那些红褐。痛感却没有传来。张北翎喊了几声,他猜只有他自己听到了。
自己好像不很愿意的样子......
吴冬至和罗桀呢,他们好像早就下去了。
都不重要了。如果这是个噩梦,还是快点醒吧。
“呼。”张北翎如愿醒来。感知到自己的魂域还是冰冰凉,但好歹有了一丝生气,不再像上次那样感觉都没有。
正在冥想的吴冬至睁开了眼睛。张北翎从来不在乎梦到了什么,只是那个梦很难忘记,好像已经经历过一般。他忽然想到什么,算了算年龄,吴冬至与他是同岁的。都是及冠之年,吴冬至好像与自己有些不同。
“冬至,你为什么要杀了那些在我之前的人呢?”
“因为我觉得你挺有意思。”
这个理由不充分,但张北翎并不想反驳,因为他没想问这个。
“我说的是,为什么非要要了他们的命。”
“你想听吗,这个故事不短,希望你不要中途再睡过去。”
张北翎翻了个身,没说什么。
“我的父亲,原来只是一个农夫。当年永阳隆威帝因为那个红颜祸水的小妃子一晚上不知道耳鬓厮磨了什么,转天起来突然要发动侵略。”
“没有人赞成,除了当时正想谋反的剠王徐辅仁,在暗地里经常‘帮忙’,还没有经过任何人同意赐死了当时的允皇后。然而烨帝却什么也没说,转年把那个妃子扶上后位,那段日子,人们都说,皇后是个控人心的妖精,现在控了皇上,就相当于控制了整个帝国。”
“隆威帝当时三权稳握,并不在乎许多忠臣的看法,却也没有杀他们。侵略还是开始了,矛头首先指向的是最富庶的岳彦,然后是西北联盟国,炀冢......永阳铁骑横扫边境,还粉碎了北靖草原部落的许多大势力。永阳没有盟友,原因就是,隆威帝命令军队只杀尽,不招降,每攻下一城都是血流成河,八百里只剩下横尸遍地。也因此国力消耗得非常快。但隆威帝不以为然,还将许多王府甚至皇宫的禁卫军也编入侵略的队伍。他终于收手的时候,中北原只剩下了两个国家,永阳,还有龟息——那蛊惑人心的皇后的家乡。而龟息国,因为有皇后在那边,没有反抗,乖乖称了臣,隆威帝也没有屠城。”
“家园被占领的人们心有不甘,曾经一度多地连续爆发多次起义和讨伐,但都被或永阳或龟息的军队镇压。而且因为屠杀已经让丧国之民所剩无几,最终幸存的人决定,不再明面起义,而是隐忍等待,刺杀隆威帝。我的父亲就在那些人中,当时他才二十几岁。”
“文武百官对于统一天下的结局意见不一,最终导致朝廷分裂成了两派:一派认为应该积极发展军备,一鼓作气继续征服南蛮诸国,另一派则认为要适可而止,休养生息,百年之内不要再发动任何大小战争。对此,隆威帝却不置可否,只是每天听着大臣们要打在一起的口气,连奏折都不批。”
“矛盾愈演愈烈,甚至有不少人也公报私仇,以此为借口发生过不少高官之间的刺杀。而我的父亲,这时算是真正看明白了,把握住了机会。在我爷爷的祭日那天,装扮成了野心日益膨胀的徐辅仁的刺客,进宫,结果行动败露,一大批人都死了。我的父亲觉得时机已过不宜久留,便诈死偷袭了一名禁军,换上他的衣服,在潜逃途中却正好遇到了皇后。父亲威胁她不成,用了他们远西的奇药,让她重现她的记忆,一路领到寝宫。因为本来禁军大都参战了,余下不少也在查刺客,父亲刺杀成功了,让隆威帝和皇后死在了一块。”
“随后,龟息国自然分裂出去了。徐辅仁发动政变,四个月后登基,曾重赏我父亲。但父亲本来不是为了帮助篡位,并没有做官,只是托人上表恢复了族人的自由,当时已成为邯帝的徐辅仁也同意了。父亲遇见了母亲,觉得终于可以过上平静安定幸福的生活。本来事情可以到此为止,但邯帝偏偏昏庸无能荒淫无道,没怎么休养生息倒把剩下的家底也压榨的所剩无几,四品以下的官员,当时连正常菜都吃不上几口,更别提平民了。没几年自然又是民怨沸腾,然而父亲其实已经爱上了这个国家和他的人民,看透了当年的血只在隆威帝一人手上,决定再次为民除暴君。这时候,父亲认识了,皇室偏系血缘的十七代玄孙,就是当今圣上。觉得他很有治国的秉性和韬略,学习能力也很强。时不时便与他长谈。当时父亲认识的他是个家道贫困的书生,却真的对他很有期待。”
“父亲知道他的志向,他就是看不下去了。”
张北翎仿佛看到,弯月下面,一个三十几岁的壮年男人和一个注定不凡的书生躺在草地上,听见了他们的谈话。
“吴朔,你觉得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嘿,那得要这皇帝老儿见了阎王才好。”
“别瞎说。”
“你年纪轻轻,就没想过要做什么大事业?”
“书没读完,卷没看透......”
“有些东西,需要自己去磨练。或许你还要经历一些。”
“去做什么?”
“你的血,决定你此生,注定不凡。”
吴冬至说到这时语气有一些激动,但很快又平复下来。
“他有一阵子没有理我父亲,但最后好像是想明白了。徐辅仁怎么死的对所有国人来说都是个秘密,包括我。后来,睦和帝,就是圣上,把残族放回境内,再让他们拥有自己的地盘,但永阳依旧有很多土地。圣上平了内乱,最后两派都退了,一朝天子一朝臣,这就是最好的结果。父亲把握着禁军,十七年了,从未再拿起那把刀。”
“总之,父亲教我的是,如果要让一个风险永远消失,只能以死亡代替死亡;而当世间不再需要死亡,那就不能再有一丝留恋。如果那天你没有带着你的剑,或许谁来陪我都一样。”
张北翎觉得精神了一些,听故事的感觉总是不错的嘛。哈......这么困啊,那就睡会吧。